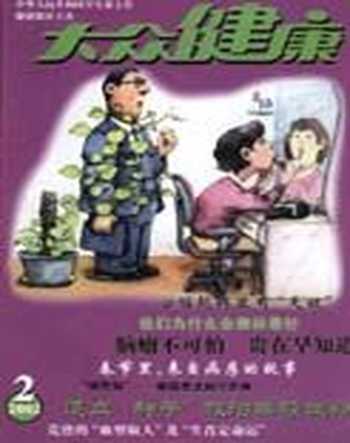巧施中藥,郭沫若逢生
章小兵
光緒34年秋(即1908年),17歲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嘉定城讀初中。不料,他卻生了一場大病,要不是醫(yī)家辨證施治,也許就少了這樣一位享譽(yù)世界的大文豪。
那年中秋過后沒幾天,郭沫若總感到非常疲倦,頭痛、下痢、咳嗽,不時流鼻血,不思飲食,對葷腥非常厭惡,吃素菜也沒有胃口。郭沫若勉強(qiáng)支撐了一個星期,再也挺不住了,便決心回家。當(dāng)時的交通極為不便,來往只好坐轎子。他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便暈厥過去。
郭沫若的父親文化不高,卻聰穎而略知醫(yī)道,在當(dāng)?shù)匾菜闶且粋€“土郎中”了。看著兒子病成這樣,他不敢怠慢,開了一劑溫和的湯藥,但病情太重了,吃下去毫不見效。家人又找來附近惟一的儒醫(yī)宋相臣來診治。
宋相臣說郭沫若的瀉肚子是陰癥,發(fā)燒流鼻血等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他給郭沫若開了藥量很大的附片、干姜。這一劑藥吃下去,不得了!郭沫若的黏膜都變黑了,口舌眼鼻沒有一處不是純黑的……宋相臣和郭沫若的父親都束手無策。無奈,家里人只好請來了巫師。在郭沫若昏睡的床前,巫師殺了一只公雞,把雞心挖出來,敷在郭沫若的心口上;又讓他吃了許多雄黃丸和六神丸等雜藥。所有的方法差不多用盡了,依然毫不見效。
第四天上午,郭沫若的一位堂叔推薦來一位住在隔河30里外的姓趙的醫(yī)生。他看了郭沫若的病狀之后,提出新的治療方案。病是陽癥,完全要用涼藥,并開了劑量很大的芒硝、大黃。不消說宋相臣是反對此治療方案的,稍通醫(yī)理的郭沫若的父親也不敢贊同。他們從上午一直討論到下午四五點鐘,還沒把藥方定下來。
趙醫(yī)生很有主見,他堅持說藥方雖然是瀉藥,但吃下去瀉的次數(shù)會一天天減少。郭沫若的父親折衷地提出要求稍微減輕藥的分量,趙醫(yī)生卻不容商量地拒絕了。這時,已處昏迷狀態(tài)的郭沫若卻在冥冥之中說了一句:“我要吃姓趙的藥!我要吃姓趙的藥!”于是,由郭沫若的母親作主,讓郭沫若把趙醫(yī)生開的藥吃了下去。他吃了這藥后,瀉的次數(shù)果然減少。趙醫(yī)生主張還要吃,一連吃了六劑,兩天一劑。郭沫若那時瀉下的只是一兩個很小的黑糞球,惡臭無比。他開始蘇醒過來,自己已能聞到糞臭。病愈時,他已是骨瘦如柴,又經(jīng)過了三四個星期的調(diào)治,才能夠坐著不搖晃,但卻落下了耳聾和腰痛的毛病。
從郭沫若的病危轉(zhuǎn)安,可以看出中醫(yī)的辨證施治是多么的重要。本來他的病是要攻積滯的,可宋相臣卻用了溫里藥,無疑使病人雪上加霜。不出名的趙醫(yī)生透過下瀉的表象看到了病情的實質(zhì),用芒硝、大黃攻積滯實在是出手不凡。大黃性寒,味苦,入胃、大腸、脾、肝、心包經(jīng),主要作用為攻下通便、瀉火解毒、活血祛瘀、清熱燥濕;而芒硝性寒味咸、苦,入胃、大腸、三焦經(jīng),主要作用為軟堅通便,清熱消腫。由于癥對藥準(zhǔn),不出名的趙醫(yī)生終于把郭沫若從死亡線上救了過來。
這件事情反映了中醫(yī)辨證施治的神奇。學(xué)中醫(yī)要學(xué)到真正的精髓,不能囿于中醫(yī)的皮毛,這樣才能抓住要害、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