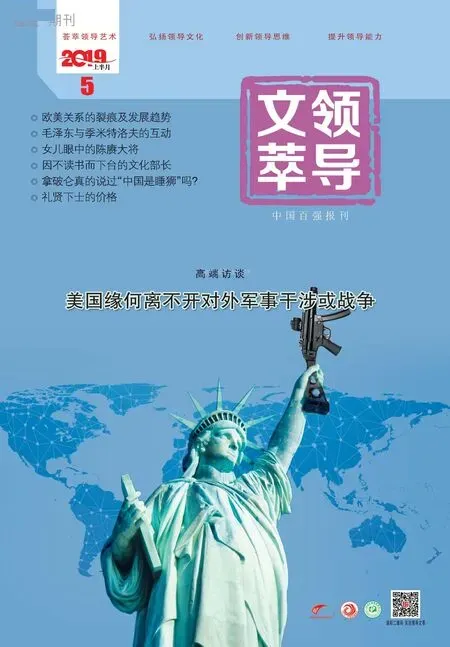彭德懷的笑與怒
郭云夢
不該把我的幸福奪去
在我們住的那幢小樓的前面有一大片草地。
我們住進什房院后,排長組織大家把樓前的那片草地翻了翻,開成了一個小菜園。
小菜園兒位于前后院東門的西側,從東門到小樓那條彎彎的小路以東,仍是一片荒涼的草地。
彭老總似乎也比較注意這片草地。
有一天,我帶他到廁所解手,回來的路上,他突然站了下來,目光盯著那片草地,歪著頭,長長的眉毛一揚,說:“這里可以開園子,可以種包菜,包菜產量高,又好吃。”
望著他那嚴肅認真的樣子,我的心就像這片草地一樣,多少有點凄涼。
在我們新開辟的小菜園前,他又站住了,望著那一棵棵瘦弱的番茄苗兒,他自言自語地說:“多好的苗苗哇!可惜沒有管理好。”說著蹲下來,拔起一棵小草兒,在手里捻轉了一下,說:“這么多的小草,不和苗苗兒爭食吃?”
我聽老兵說,這也是他的一個生活習慣。在他當國防部長期間,每次外出活動回來,他都要到自己的小菜園里看一看,如果菜地里有草,他就會不顧疲勞,下地薅草,他是不允許野草和蔬菜爭營養的。
那天有點兒不大湊巧,正趕上上級有關部門到什房院來檢查工作,他們正在連部里聽連長匯報有關情況。
我當時沒有急著讓彭德懷回去,是有心讓他多曬一會兒太陽,并無意讓他去薅草。
連部就在小樓的二層樓上,不知是誰最先發現的,排長從樓上匆匆忙忙地跑下來,讓我趕緊送他回去。
他站起來,拍了拍手,說:“我能種田,會種園子,讓我來管理這個園子吧!我可以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他勞動的權力已經被剝奪了,一個小小的警衛戰士,有什么權力再賦予他?
接著發生的一件事是因為他們的廁所。
他們的廁所是臨時搭建的,供他們十個人專用,平時又無專人負責清理,里面的不衛生程度是不難想象的。
有一次,他從廁所里出來,走到我的身邊,淡淡瞟我一眼,說:“我閑著無事,悶得慌,請你幫我找把鍬,讓我把廁所清理一下。”
他見我有幾分遲疑,就說:“我能成,干什么都成的。你看……”他伸伸胳臂,握緊拳頭,表示身體還很結實。
我的心里有點兒酸楚,就含含糊糊地答應了他。
下哨之后,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排長。
排長就派人把廁所清理了。
事后的第二天,他從廁所出來后,就帶著一臉的不高興。
當他走到我的面前時,瞪了我一眼,口氣很生硬地說:“你不該把我的幸福奪去。一個人應該是誠實的,撒謊不好。”說罷,氣哼哼地走了。
一個多月后,我終于在排長的默許下,給他找了一把鐵鍬,讓他“幸福”一次。
他把廁所清理后,頭一次看著我笑了,并夸我是個好伢子。
這是我在什房院值勤的一年多的時間里,見過他的惟一的一次比較開心的笑臉。
說實話,他笑的時候遠沒有他嚴肅的時候好看。
誰吃你的臭蘋果
他的大拇指指甲有點兒毛病,比一般的指甲長得厚,疙疙瘩瘩的。據說這種病狀就是灰指甲病,治療起來很容易,只用勤剪指甲,吃點兒灰黃霉素、維生素B1、B6什么的,再經常用碘酒消消毒就行了。但在什房院,他連這些最基本的條件也沒有。
平時,每當他刮臉的時候,總是用刮臉刀的刀片把指甲上隆起的部分削去,或許,這樣會好受一些。
那幾天,接連下了幾場雨,天上陰云密布。
在陰霾的天氣里,他的灰指甲很容易作祟。他站在桌子前,用大拇指在桌面上蹭,以緩解癢的煎熬。
好不容易盼來個晴天,“放風”開始照常進行。
那天,我帶著譚政大將在他們的房后活動。一個從山西入伍的新兵帶著他在西邊的操場活動。
當他們的“放風”活動結束后,我把譚政大將送進住房,山西兵就帶著他回來了。
他平時走路一般是昂首闊步的,而這一次卻低著頭,一邊走一邊用另外一個拇指摳著病拇指的指甲。
突然,他瞧見地上有一片破碗碴,破碗碴也算是對付灰指甲的利器,他禁不住想伏下身揀一塊兒。
山西兵見他要揀破碗碴,不知他要干什么,立時慌了神,一邊拿眼偷偷看我,一邊大聲喝止他:“不準揀!”
山西兵見他不管不顧,眼看就要得手,想和他爭搶已經來不及了,就趕緊用腳去踢。
他發現哨兵要踢破碗碴,忙用身子護住了。
哨兵用腳踢,他挲著雙手,左擋右攔,哨兵踢了幾次,也沒踢著。
我心里有點兒酸楚,想出面阻止哨兵,剛邁出兩步,就見各個哨位的哨兵都轉過身來,在觀看這一老一少爭奪破碗碴。我的勇氣沒有了,只好癡呆呆地站著。
他終于把那片破碗碴揀到了手里,一邊刮著指甲,一邊對哨兵說:“我用它刮下指甲,這又不是什么政治問題。”
哨兵的臉都有些發白了。
當他把彭德懷元帥送進住房后,紅著臉,吭吭哧哧地對我說:“班長,我……我沒看見,他……他就……”
看著山西兵誠惶誠恐的樣子,我輕輕地嘆了口氣,說:“沒關系,他這個人是不會想不開的。”
我沒有批評哨兵,因為,雖說一個破碗碴微不足道,但對一個死志已決的人來說,也是足以致命的。按照當時的規定,這樣的利器,是絕對不能讓他們擁有的,這不能怪哨兵。
另一件事是因為吃蘋果。
他們雖然成了這里的“囚犯”,但他們的原工資待遇沒變,每個人都有一筆錢放在連部里,由連隊代管,以保障他們的日常所需。
彭德懷不抽煙,生活也比較簡樸,并不經常購物,這天,不知為什么高興了,他突然向哨兵報告,想買幾斤蘋果。
通信員把蘋果買回來的時候,正是我值班的時間,我掂著蘋果來到了他的房間。
他的嘴角抹了幾絲淡淡的笑意,滿懷喜悅地接過蘋果后,順手抓出兩個,伸到我的面前來,說:“吃吧!這么多,我一個人是吃不完的。”
我知道他是實心實意的,但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有勇氣去吃這個蘋果的,我自然也不會例外。我婉言謝絕說:“對不起,我不喜歡吃蘋果。”
他見我這樣說,就把蘋果遞給了哨兵,說:“你吃一個吧?”
哨兵是個新戰士,大概是從陜西來的,人很聰明,也很聽上級領導的話,是連隊重點培養的干部苗子,階級斗爭的弦自然繃得比較緊。見彭德懷要給他蘋果吃,當時就拉下臉來,說:“誰吃你的臭蘋果!”
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手中的蘋果袋“咚”地一聲掉在了地上,幾個蘋果滾出了袋子,散落在地面上。
他的臉色在這一瞬間變得黃不黃白不白的,兩只手就那么扎煞著,就像觸了電一樣,站在那里一動不動,許久沒有言語。
我想把屋門關起來,以免他和哨兵發生沖突。
就在我關門的時候,他卻伸手抓住了門板。
他的兩眼瞪著哨兵,感情似乎很沖動,說:“你這是標準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吃個蘋果有什么了不起?這又不是什么政治問題。”
一連數日,他都是愁眉苦臉的。
他愛兵,更愛生活,然而,他卻失去了愛的權力。
(河洋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