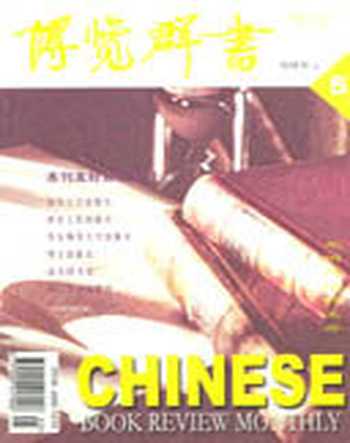地圖的隱喻和可信的科學
齊曼(J·Ziman)教授的《真科學》并不是一本容易把握的書,不僅因為其較長的篇幅,更在其思想的綜合性。他既承認科學的社會建構一面,同時仍試圖表現科學家們為了達致“客觀”所進行的種種努力。于是他借用了“地圖”(map)這一喻體來對應科學。這正是齊曼教授在這本新著中的關鍵所在。
李義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作為對地形的模仿,地圖并不能等同于實際地理的客觀狀況。如果說地形是客觀實存的感性世界,那么地圖就只是以之為基礎的形式描述。后者雖然不能算作感性的世界本身,但也絕不是純粹主觀的臆斷或胡謅。但是,既然作者認為科學理論像地圖這樣不能完全同經驗世界本身畫等號,而只是模仿性的敘述,那么從這種社會學角度來考察科學知識,就有很明顯的建構主義傾向。
與建構主義一樣,作者也認為我們所采用的工具,都是既有的某種理論的具象化。工具所遵循的度量衡、它對于對象的作用層面,以及通過它反饋出來的量化結果,都負載了已接受的理論框架。采用這樣的工具,將同時限定了我們如何切入待研究的對象,我們會用怎樣理論視角觀察那些“能被觀察到”的因素,而同時忽視那些“不能被觀察到”的因素。同時,得到的實驗報告總會使用既定語詞來描述,并且首先將接受既有的理論框架的解釋。這就好比規制地圖時,.由于測量技術的限制和測量者的選擇,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會被刻畫出來,我們得到的地圖總是有所取舍的。
通過解釋之后,一條新命題(或理論)才能是“說得通的”。猶如我們開辟的一條新路,它必須是同原有的路網有所關聯的,而不能是獨立的兩端緊塞的“死路”。當然我們發現不可能出現兩段皆處于封閉狀態的“路”——我們不稱其為“路”。而這正是因為,我們所用以拓展路徑的理論出發點和工具,如上文所述,本來就是從既有的理論路網中衍生出來的。但另一方面,僅僅被發現者(或提出者)解釋是不夠的,無論是“說得通”還是“走得通”,都在暗示著“交流”這個概念。一條新理論必須參與到理論共同體的交流之中,由此完成它的意義生成和功能界定,即在交流中獲得其含義能被接受的共同基礎,并定義出它的作用范圍和主導方向。這就好比必須將一條新拓展的路涵蓋至整個路網中,必須允許人車通過,才可以考察其在交通流動全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與周遭融洽并對現有路網有所促進。
每個人進入科學認知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閱讀地圖和實地行走同時發生的過程。當我們初始面對世界的時候,除了目之所及的有限信息,我們手中還擁有前人傳承下來的地圖,它使我們明白身處何方,以及能夠如何行走。而閱讀地圖就是接受教育的環節。在地圖的幫助下,我們通過實地行走來體驗和檢驗前人的對錯。由于每個人的行走方式并不一樣,因此每個人形成了自己的個體認知模型,即形成了個人地圖,換言之,每個人擁有了自己關于世界的認知圖式。但是這種個體地圖并非兩兩之間格格不入,因為我們的行走都是基于前人的地圖的指導之下,這就具備了主體間做進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就其反面而言,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文化共同體的人們如此難以深層、便利地交流——因為從一開始他們接受的就是不同前人的不同地圖。但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內,這個問題不太明顯,因為雖然自然語言對普遍主義提出了挑戰,然而科學共同體內部卻擁有一套更為優越的數學語言或邏輯語言。于是我們的個體地圖雖會逐漸趨于分散,但一旦展開交流,便能夠迅速地發現可共通之處——從個人的意見中過濾,得到可重復的、可操作的、可檢驗的共識,這便是科學理論。作為一份共同的地圖,它是對個體地圖的,也是對原來的共同地圖的繼承和修正。然而這只說明了我們從舊的共識走向了新的共識,并不意味著除此之外,我們就放棄了個體地圖。每個人仍是在共同地圖下以主體身份獨自行走,仍不斷形成新的個體地圖。這些個體地圖中尚沒有進入共同地圖的部分,有待共同體通過交流來加以判定。如果一條線路被證實,那么就被添加到現有路網中來,成為“公有的”,參與新的共同地圖的建構,反之則被拋棄。所以。共同地圖是個體地圖的形成基礎,而個體地圖是共同地圖得以擴展的必要條件。
整個自然科學體系如同一套“三維地圖”,不同的學科(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則是這套三維地圖的不同層面的呈現。進入一定學科的人,總以一定的視角考察作為整體的自然。于是物理學家看到的是物理地圖,生物學家看到的是生物地圖。它們只是同一張地圖的不同維度的描述,就像一座城市的供水網圖、輸電網圖、商業網圖的關系。于是,對于一個特定學科的研究者而言,與他的個體地圖相作用的共同地圖,主要是在這個學科維度上形成的共同地圖。但是這并不代表不同維度的地圖就不可通約,因為它們面對的對象——自然界——是相同的,并且它們都處于數學邏輯語言地圖之上。
地圖雖然并不是地形本身,作為人類社會的產物,科學知識也不能被證明是同世界完全貼切。但是否如此,就以之為虛妄的神話而置于信任抄1)呢?就如同撕毀所有的地圖,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1:1的反映實際地貌呢?其實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存在1:1的地圖是否可能?很明顯,作為地圖,1: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就科學知識而言,它既然是“知識”那就不是“世界本身”——如果它就是“世界本身”,那么“知識”這個概念就是多余的。同時,經驗的人的有限性,也導致了科學知識無法同世界本身完全匹配。然而關鍵在于,不能完全匹配并不意味著另一個極端——知識的建構是主觀的臆斷。齊曼通過對默頓的四個規范的逐一修正,試圖表明現代科學仍是試圖貼近“世界本身”的一種可信的活動,自然科學家依然是一個努力使科學知識摒棄偏見、達成共識的群體。
正如前文所述,自然語言對普遍主義構成了挑戰,但科學家的活動卻是以數學語言和邏輯語言為基礎,通過量化的方式來盡量地減少個體的主觀因素。無論是數學還是邏輯,他們一方面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語言,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客觀世界的語言。前者使科學共同體中的共同交流平臺得以存在,科學家們能夠共同遵循著邏輯的推理方式和量化的操作方式;后者則體現了知識世界的經驗性基礎。
科學家雖然無法從根本上擺脫來自個人的和社會的“前有”負載,但他們的行動仍然是在盡力地排除這些非客觀的因素。起碼是在具體的操作和規范層面,依然要保證科學理論的可證實(偽)性、可重復性,依然要進入共同體的交流之中接受懷疑,而這些懷疑同樣必須遵循已有的科學規范和科學思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自然科學的理論都不能是純粹主觀臆造的,共同體中存在著一套不依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約束”。
當然從哲學上來講,任何研究規范或約束都無法保證我們完全確鑿地認知世界,但這種“客觀約束”畢竟是目前能夠貼近世界的最佳策略。在人可以作用的領域內,我們應把主觀因素降至最低,測量更精確、計算更嚴密、描述更中性。當然,即使這樣,也不能消除人的種種局限性,因為這些“局限”并不是別的,僅僅由于我們是作為一個經驗的、有限的“人”而存在。
(《真科學》,[英]約翰·齊曼著,曾國屏等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