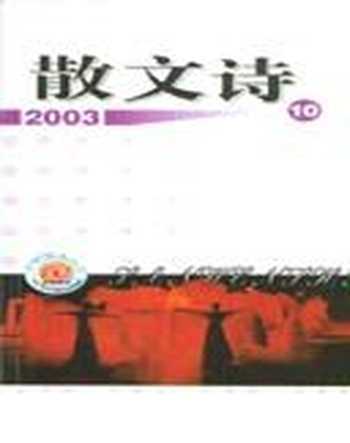西部
島 影
關于滄桑
滄桑是一種感覺,一種厚重、深冷的感覺。
如果用眼光去撫摸滄桑,我們會誤認為枯黃的落葉和凋謝的花瓣就是滄桑。其實滄桑是活著的景觀,是一個收藏歲月不需要抖落時間殘片又能超越時空的古玩;它接納生命過程中的一切細節包括風去雨來又不失真;它堆砌苦難又不掩飾陽光的潑灑。滄桑的觀賞性在于心靈而非視覺,因而,我們說心與滄桑的距離遠比視覺要近得多。
在新疆的羅布泊,你會覺得自然中的一切存在也有走樣的時候,甚至連最美麗的傳說和那個水汪汪的字眼上的誘惑都會徹底地給你洗腦。羅布泊,那應該是有水草有舟楫連片碧藍的水澤吧,然而,地圖上那彎淺藍色的眉眼連一滴淚水都沒有的羅布泊,讓人在大自然的真容面前顯得如此不可思議。盡管羅布泊在土灰色的尼雅地貌上風化成如浪的土堆,但凡是走進羅布?白的人都成了英雄,他們不是被淹死,而是被干死,甚至在迷途中走失成了英雄,因為明知用生的代價去兌換自然的秘密,羅布泊無疑成了靈魂的棲居地。羅布泊,一處神秘變幻的空間,曾經的湖泊雖然消失,曾經的擁有和至今仍然托載著一批批尋夢者的希望之舟。
滄桑是一種存在,一種刪除表象誘惑的存在,滄桑的地盤永遠生長著萬木蕭蕭的肅穆,它是燃燒的冷色調,它不需要張揚,因為人類與自然的對視也就是心與心的對白,他們從來不需要第三只耳朵。朝圣西藏
在一幅酷似牦牛的地圖上,我看到了西藏。
看到兩支堅硬的犄角倔強在抵頂著昆侖山系的危巖,西藏的陽剛和野性深埋進那片赭黃的版圖。西藏,一座望也望不到頂尖的山峰,有多少雙攀援的目光在世界屋脊的高度下望而卻步。
朝圣西藏,你或許旋動轉經筒的偈語,聽雪域之風干百次地呼喚五顏六色的經幡,破譯一個民族心底最真誠的祈愿。
紅山腳下的八瓣蓮花為圣城拉薩造型。到拉薩去,到最接近太陽的城市去,有誰不崇拜太陽呢。
漂流在雅魯藏布江的波心,那條從雪域高原飄然而至的河流,其實是藏民心中延伸出的哈達。
藏北,世界屋脊最后一級臺階,空氣稀薄,連草木都因缺氧而銷聲匿跡,我們見到寺廟,聽到了朝圣路上手屐的匍匐聲,我想任何一個人,要執著一念,對心目中的彼岸首先準備用生命橫渡。
在藏北,山比人多,一座座連草木都長不出的高度卻能繁衍雄性的傳說,每一泓水光都泛動著動人的神話。神山圣水,這就是西藏自然中的人文景觀;千山萬水,既是站成高度的傳說,又流淌著深度的神話。在念青唐古拉,我們想象萬河之母源頭撼人心魄的壯觀,事實上,真正的源頭不屬于某一座山,因為如林的雪峰在同一枚太陽的照徹下化解而成為圣母,顯然,江河之源是一切河流的開始而非高潮,因而,江河的源頭在起步中拉長的是它的身影并非壯勢。黃河與花兒
那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逼真的花型在西部的陽光下投映成了寧夏的版圖。寧夏是一朵花啊,一朵以黃河為枝頭的花。于是塞外江南的山山水水開放成了花的造型。
黃河第一次掉頭回眸,我們才發現寧夏的魅力,也只有寧夏才能讓桀驁不馴的黃河漪漪地繞道延伸到了花兒的故鄉。
黃河只要不泛濫,每片干涸的土地都愿等待她的覆蓋,黃河將那些散落的炊煙擁入懷抱,黃河放慢了步履,拉長了長度,黃河流出的“幾”字謎一樣的婉轉成了花兒的高腔。黃河在寧夏養育的不僅僅是村落和牛羊,她把一個民族的心浯和花兒澆灌成了風情。
黃河有時就像一棵掛滿滄桑的榕樹,既古老又年年枝繁葉茂。望著那些此長彼消的漩渦就像撫摸著樹的年輪,不是用手而是用眼光在那一枚枚渾圓的圖案中解讀黃河的野性和天然中的母性原真,因而,我們說黃河遠不是自然之河。
在寧夏的土地上,我們聽到花兒的綻放,寧夏人把花兒的種子播進他們的聲帶和情感之中。黃河是花兒源頭,黃河的真正河床是寧夏子民的胸腔。寧夏人走到哪里,黃河就流到哪里;黃河即便斷流的時候,花兒一樣的黃河動感依然在花兒的土地上流淌。天山:一列由西向東的駝峰
絲綢之路上惟一存活的是駱駝。
駱駝似乎遠離了我們,它們總是浮出晨昏的沙海,成為沙漠風光中惟一能走動的風景。
天山啊,這匹酷似駱駝的脊梁和駱峰,由西向東站成蒼莽和神奇的浮雕,駱駝的浮雕。
新疆的神秘可以收藏,隨手撿一顆石子,你撿起的無疑是一件遺物,或一枚凝固的傳說,那么厚重、本真、滄桑,并有一絲觸痛靈魂的溫熱。
新疆的綠洲是流出來的,是雪山的精血,雪水停留的地方就會長出白樺林、左公柳,于是城市在這片林子里節節攀長,因而城市是綠洲的作物。
依奇克里克,塔里木盆地的一片沖溝,如果譯成漢語,那就是“野山羊出沒的地方”。新疆的牛羊多得就像我們內地打谷場上的谷粒,它們成群結隊、密密麻麻,如一群會走路的莊稼,惟一不同的是這些“莊稼”不是長在土地上,而是像云片一樣在放生中成熟。新疆人在享用香噴噴的奶茶和烤全羊時,我自然回味江南包谷酒和新米上桌時一樣的喜悅。
新疆又是一個用舌尖一嘗都能甜到心底的瓜果之鄉。哈密瓜、馬奶子葡萄、香梨,它既是藤枝上長出來的,又是上蒼對那方水土的垂青。風情在嗩吶和羊皮鼓的吹打聲中牽掛了多少匆匆的行影。新疆從此成了我的記憶,一朵游移的云淡出那片天空,成風成雨飄灑成一串牽情的懷念。馬頭琴:草原上能說話的圖騰
世界上惟一能被音樂感化的是馬。
走進草原的人,真正能夠在馬頭琴的訴說中流淚的還是馬。
一匹馬駒活在了馬頭琴的兩根弦上,活成了傳說,活成了草原上凈化性靈的經典。
奔放、剽悍,它們蹄下生風但從未走出過草原,不是草原有多大,也不是格桑花搖曳出油津津的誘惑,也不是韁繩拴住了它們的漂泊,只是草原不能沒有馬,草原為馬而豐饒,它們就像一朵朵繡在藍天上的云絮,雖然它們時時游離,但僅僅是在動態中拼構圖案。
馬頭琴,草原上惟一能說話的圖騰,一把一撞就能牽情的器樂,一匹不能奔跑但永遠唱歌的馬,它以馬頭的造型成為草原傳承的圖騰,但你無須朝拜,它早已人格化了,你只要聽一聽馬頭琴的訴說,聽低緩沉婉的琴聲,你就知道傳說中關于一頭母馬丟下小馬駒后牧人用馬尾拉響馬骨招魂。母馬最終泣淚回頭。一個民族博愛和善良的心音從此成了馬頭琴的靈魂,因而我們可以說馬頭琴是牧歌的真正源頭,也是馬們惟一能夠聽懂的人類語匯。
題圖/張天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