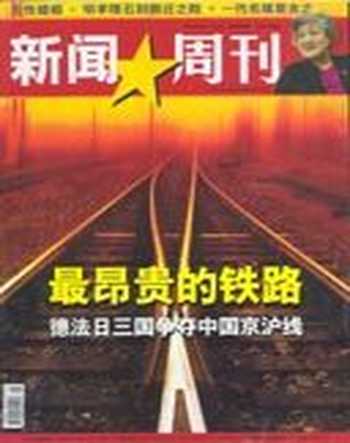總統先生誠實嗎?
2003年1月,弗魯姆的《天降大任:驚世總統布什》(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由蘭登書屋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弗氏盛贊布什誠實的品質,但是近來發生的錯誤情報事件,卻令堅持民主原則的部分美國人懷疑總統的這種誠實
戴維·弗魯姆是小布什的前任總統演講稿撰寫人,此公對小布什的總統生涯進行了滿懷深情的描述,大談自己的老板如何地“蔑視政客們的說謊行徑”。譬如,在準備錄制第二天即將播出的廣播錄音時,總統開始讀稿:“今天,我在加州……”然后,他會突然中斷,頗帶惱怒地說:“可我不在加州啊!”在弗魯姆看來,這種做法的確有點書生氣,但也不失為總統品質的體現,因此“國民盡可相信布什政府不會撒謊,不會欺騙公眾”。
現在看來,弗魯姆先生實在是荒謬至極!
在華盛頓錄制廣播,卻說自己身在加利福尼亞,小布什或許天真爛漫地認為這是在說謊,而說謊是不對的。然而,在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總統先生卻未能發現誤導了本國和世界的嚴重錯誤。正如我們所見,白宮把自己發動戰爭的理由建立在一批經過高度選擇的“證據”基礎之上。布什雖然發表聲明,指控伊拉克試圖從非洲購買鈾,但總統及其參謀班子明明知道,這種指控即使不是無中生有,也是高度可疑的。
在被問及上述指控為何能被寫進總統的國情咨文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都堅持認為這一指控并非謊言。兩位官員的論說顯示出,他們正如總統一樣,對于何謂說謊只有一種幼稚的字面上的理解。
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是這樣講的:“英國政府了解到,薩達姆·侯賽因最近試圖從非洲獲得大批量的鈾。”而其原始版本只是蒼白無力地指出薩達姆曾試圖從非洲買鈾,這一版本遭到了中央情報局的反對。白宮官員與中情局會商之后,建議把這句話改為“據英國政府報導,薩達姆·侯賽因曾試圖從非洲買鈾。”
從字面意思上看,這事兒說得不錯,因為英國政府的確報導過此事。但這無疑又具有誤導性,因為中情局曾經告知英國政府他們的情報可能有問題。布什只援引英國政府未加證明的指控,卻使賴斯和拉姆斯菲爾德都深信不疑。賴斯說“(總統的)聲明準確無誤,英國政府的確報導了此事。”拉姆斯菲爾德則認為布什的說法“在技術上是準確的”。
事實上,即使完全從字面上去理解,布什的聲明也不夠準確。布什不是單純地說英國政府“報導”伊拉克曾試圖從非洲買鈾,而是說英國政府“了解”到此事。說某人“了解”到某事,就默認了他們所了解之事乃是真實的。試想,倘若英國政府說薩達姆是個愛好和平、準備給伊拉克帶去民主的人,布什先生還會說英國政府“了解”到了這一點嗎?
拋開所謂“技術上準確”這種無力的辯護不提,退一步講,即使總統的說法真的在技術上準確,它仍會有計劃地誤導各國,使他們認為伊拉克一直試圖從非洲購買鈾。而這才是嚴重得多的問題。因為布什及其政府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罪名是莫須有的。
在錯誤情報事件成為公眾話題之后,布什的表現再次給人以在道德上舍本逐末、避重就輕之感。一個有道德敏感性的人,認識到發動一場基于錯誤情報之上戰爭的嚴重后果,必將采取適當的措施。他應當確保美國公眾得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確保肇事者按照慣例受到應有的懲處,確保對事件做出可能的最好解釋——承認這是高層的嚴重判斷失誤。
但布什并未做出努力。問題公開化后,布什的反應只是譴責其批評者是一群“修正主義史家”,同時規避情報的可信性問題——正是借助了這些情報,布什發動了戰爭以達到驅除薩達姆的目的。后來,他又說中情局已經澄清了他的言論,好像這樣就可免去自己所有的責任。在中情局局長特內特表示對錯誤情報事件承擔責任之后,布什又說自己“完全”信任特內特和中情局,他認為事情會就此結束了。
2000年總統大選中,出于對其誠實品格的信任,許多選民更為偏愛布什而不是阿爾·戈爾。在那些把“誠實”列為影響自己選擇總統重要因素之一的選民中,有80%自稱把票投給了布什。這些選民對克林頓深感厭惡,這不是因為他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之間的緋聞,而是因為克林頓在此事件中做偽證。
無疑,克林頓的確撒謊了,他犯了錯誤。然而克林頓的謊言并沒有把自己的國家帶入一場奪取了數以千計國民生命的戰爭。可布什雖然口口聲聲地強調誠實的重要,卻隱瞞了一個彌天大謊,而這一謊言后果的嚴重恐怕已遠遠超出簡單的道德范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