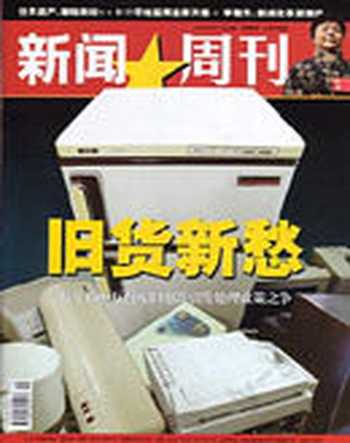地方政府何所為
保護還是開發:一些地方政府力圖在兩者間找出一個權宜之計。
2002年夏天,湖北十堰市旅游局在鄂港經濟合作洽談會上發布了招商引資的信息:將以合資、合作、拍賣、參股、轉讓、租賃、承包等方式轉讓武當山部分景點旅游項目的經營權,允許投資商控股51%至55%,經營年限可達50至70年。
不光是武當山在這樣做。據媒體報道,深圳華僑城買下曲阜孔廟、孔府、孔林及其它的旅游景點的51%的股份,成為“三孔”新主人;四川旅游局也表示要出讓包括三星堆遺址在內的10個景區的經營權……
拋開涉及文物保護一部分,單就經營來講,業內人士分析,適當出讓經營權,可以促進旅游市場由低層次的一般旅游產品經營向高層次的景區租賃經營發展。但是,轉讓世界遺產經營權的做法還是遭到了空前的質疑,人們認為,世界遺產正在陷入難以擺脫的尷尬境地。尤其是,前段時間武當山遇真宮失火事件,更加劇了人們對于世界遺產命運的擔憂。
面對世界遺產,保護和開發成了博弈雙方。申遺就必須先整治,整治就要花錢,一動錢就要有成本核算,結果最終遺產保護成了遺產開發。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對峙中,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計企圖在兩者之間找出一個權宜之計,以應對日益增加的旅游壓力和日益嚴重的遺產破壞。這里也不排除一些地方官員將“申遺”當作政績工程來抓。
大量的事實表明,許多地方在套用國家建設部1987年6月10日下達的《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實施辦法》,或者干脆用開發區的相關法規來管理和保護世界遺產。專門法規的缺位,加大了世界遺產保護工作的隨意性。而因為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統一管理,各地政府一方面考慮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專業知識,致使世界遺產被失控開發。
要從根本上讓世界遺產走出怪圈,謝凝高認為必須做好六方面的工作:第一,為保護世界遺產專門立法;第二,設立類似“世界遺產管理局”這樣的機構,直接負責各地遺產的管理;第三,成立專家委員會,參與保護世界遺產的科學決策;第四,立即整改各地對世界遺產的違規行為;第五,國家撥付相應的專項資金;第六,管理部門要經常進行培訓。
謝凝高認為,國家撥款的嚴重不足給當前世界遺產的保護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有幾個數字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韓國每年給風景名勝區撥款相當于6億人民幣,美國則高達43億美元。而目前,我國每年給119處風景名勝區的撥款是1000萬元,平均分下來,大部分的風景區連職工的工資都不夠支付。正因為如此,才使得許多地方只得“靠景吃景”。
除了要加大這六方面的工作力度外,此間有一種意見說,從我國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之日起,我們就應該樹立起保護遺產的觀念,既要有做出犧牲眼前利益換取長遠利益的心理準備,也要有由被動接受到自覺遵守世界規則的觀念轉變,從而將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深入人心。
有人舉了美國的一個例子。上個世紀90年代末,美國黃石公園全體職員罷工,要求政府將此公園報請加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原因是:1.公園4公里以外的私人土地里發現了金屬礦,土地的主人計劃開采;2.公園里的野牛染上了普魯氏病菌,恐怕傳染給家牛;3.有人給園內的湖里放進了外面帶進來的桂魚,導致水里的生態失衡;4.游人壓力越來越大。為此,當時的克林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面花6500萬美元將4公里以外的那塊私人土地收購,并疏散了公園里的床位,盡量讓游客去外邊住。
另外,一個例子經常被人提及:法國雪鐵龍公司曾在長城東段起點的“老龍頭”拍了一個汽車廣告,然而該廣告在法國某電視臺播出僅十幾秒,即招致無數電話怒斥:“我們法蘭西民族是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民族,怎能為了拍一個商業廣告,竟讓汽車爬上人類文化遺產!”
一位搞環保的中國人,曾經向中國《新聞周刊》談起過他的經歷:他去參加朋友搞的一個旅游項目評估。他們坐在小船上,向湖心的一個“鳥島”進發。這位環保工作者建議道:如果游客要觀光,一定不能上島,以免打擾鳥兒們的產卵。但是這建議馬上遭到地方官員們的反駁:如果不上島,且不說在水上視線太低看不到多少鳥會影響游客的興趣,而且不上島,還會影響一系列的收入:如島上的食品銷售、望遠鏡的收費、甚至在島上建旅社的收入,就都沒有了。這位環保工作者只得閉嘴。
若想真正保護我們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中國怕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