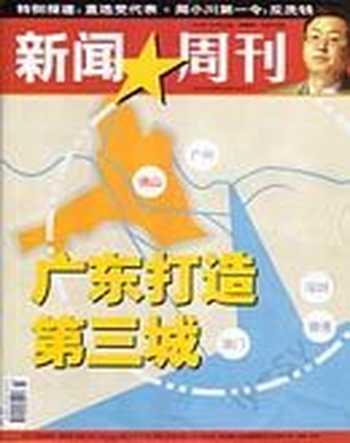再干50年:從小康走向現代化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已走了頭兩步,現在開始走第三步。走前兩步是用20年,第三步要用大約50年
主講:王夢奎
時間:2002年12月23日晚7:00
地點:北京大學圖書館北配樓報告廳
主辦:北京大學校友會·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北大講壇
中國進入小康社會的判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確立,是根據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進程做出的。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可以做出以下四點基本判斷:
(一)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市場供求格局發生根本變化。按可比價格計算,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過原定20年翻兩番的目標。這引起宏觀經濟政策的根本性變化,即由過去的限制消費的政策,轉變為擴大消費與改善供給相結合的政策。
(二)經濟結構實現重大調整,工業化進程加快,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第一產業比重由28%下降為15%;在人口總量增加3億的情況下,農業勞動者占總就業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以下;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出口量迅速增加,但在出口商品構成中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10%,工業制成品比重由50%提高到90%。從工業方面看,已經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制造業能力比較強大,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運輸等“瓶頸”問題得到基本緩解,現代服務業正在興起。
(三)改革開放取得突破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這是理論創新,也是制度創新,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都具有深遠意義。綜合評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超過50%。而任何國家的經濟市場化程度都不可能達到100%。
(四)人民生活實現兩大歷史性的跨越: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90年代由溫飽達到小康。城鄉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群眾消費由追求基本生活資料數量的滿足,發展到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結構從以農產品消費為特點的溫飽型,進入以工業品消費為特點的小康型。
上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走了頭兩步,現在開始走第三步。
“三步走”走了兩步,不等于走完了現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前兩步是用20年,第三步要用大約50年。這里講的是實現現代化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考察中國經濟,要注意總量和人均兩個方面。我國經濟總量已經居于世界第六位,按近些年的發展態勢,2010年前后會超過法國(2005年)、英國(2007年)和德國(2013年),達到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位。但中國現在人均還不到1000美元,剛剛進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行列,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也還是中下收入國家,在世界上的排名變化不大。我們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在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以及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和生活水平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人均GDP上海在4000美元以上,貴州不到400美元。至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有更大差距,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之間的矛盾還很突出。
從2001年起,要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用50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就是考慮了全國發展不平衡的情況。
“小康”這個詞,最早是《詩經》上說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勞苦,應該讓他們稍得安寧。白居易的詩,也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過小康的說法(《老病相仍以詩自嘲》:“昨因風發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后世人們把家庭稍有余財,可以安然度日,稱為小康。而把小康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則出自儒家的《禮記·禮運》,這是西漢時代的書。這部書里講的“小康”,是和“大同”相對應的社會發展階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話,人們都不陌生。在那里,“大同”是儒家的烏托邦,只存在于遠古的堯舜時代,那是一種向后看的理論。康有為的《大同書》是向前看的,他對未來大同社會做了一個想象力豐富的空想設計。毛澤東在建國前夕所寫的一篇著名論文里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路,共產黨人要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這里所說的大同,是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即共產主義。這是繼承和發揚傳統思想而賦予其全新意義的一個典范。鄧小平關于小康的論述,也是繼承和發揚傳統思想(同時也是吸收民間語言)而賦予其全新意義的一個典范。
毛澤東所說的“大同”是未來的理想;鄧小平所說的“小康”是現實的目標,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溫飽有余、但還不富裕,這么一個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
有人問:實現了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否還是小康社會?我認為,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前,都是小康社會;那個時候的小康社會,是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也許,在那以后,會把實現現代化提上實際議事日程,逐漸淡化小康的色彩,更多地強調實現現代化這一面。這也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個問題今天可以不討論,由后人來解決更好。
王夢奎,1938年生,經濟學家。196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先后供職于《紅旗》雜志編輯部和第一機械工業部、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務院,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和十五大、十六大報告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提問與回答
問:前一段時間社科院對縣地級領導做了一個統計調查,其中有78%的市長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不穩定時期。在這里我想向您請教的是,中國社會的內在脆弱性體現在什么地方,以及針對這些脆弱性您能不能給我們大家提供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和看法。
答:我剛才講了,保持社會穩定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發展本來就含有不穩定的因素,因為要改變原來的狀態。按照國際上的說法,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是社會處于不穩定的時期,我國現在正處于這個時期。我國的不穩定因素主要是工業化、城市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失業人口,社會收入的差距,地區的差距,由這些因素產生的,所以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前進過程中的問題。從收入差別來說,我們主要應該采取法治的辦法,保證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對高收入者的稅收。你說的那個調查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它提到的穩定、不穩定的標準是什么,是完全不可控的動亂?還是雖然意見比較多,但還在可控范圍以內?如果從后面這個根本標準來判斷,應該說,中國現在的不穩定,還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還在可控的范圍內,還處于改善的時期,不是已經沒有辦法了,應該說基本上是穩定的。
問:您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存在一種不均衡性,這種不均衡體現在城市、農村、地域以及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小康建設的過程中,如果像您剛才說的目的不是讓大家的收入差距縮小,那么按照這個模式發展下去,差距會不會越來越大呢?中國的社會公平怎么實現,中國的性質又會朝什么方向發展呢?
答:我講的意思不是不要縮小差距,我的意見是不能用平均主義的辦法來縮小差距,因為那樣會影響發展。縮小差距是一個過程,現在國家實行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國家對落后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強、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是為了縮小差距。但根據我們的研究,地區差距在近期內不會縮小,因為各地的基礎不同,發展的客觀條件也不同。絕對差距在一定時期內會繼續拉大,相對差距則取決于各地的發展速度。比如說,上海的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而貴州不到400美元。上海增長10%就是400;貴州增長10%只有40。絕對差距拉大了。這種絕對差距的擴大也存在于美國、日本和我們之間。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要求我們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