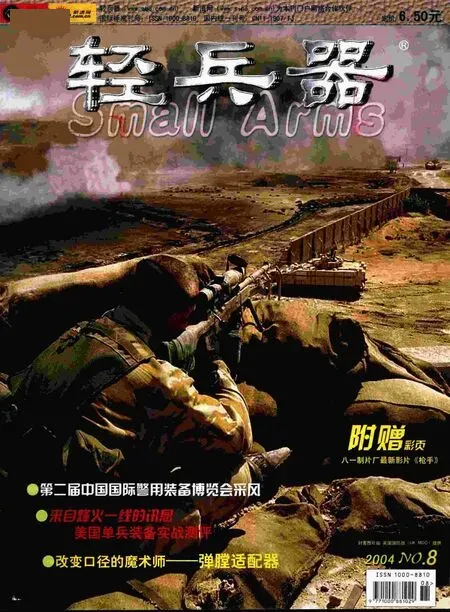日本軍國主義的利爪(下篇)

30年式刺刀的生產廠家及標記
30年式刺刀的生產從189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45年,前后近半個世紀,并且是由分布在日本、朝鮮和中國的不同兵工廠生產的。起初,日軍使用的包括30 年式刺刀在內的各種自產兵器都是由國營各大兵工廠生產的,但隨著對外擴張規模不斷加大,民間企業也逐步加入到軍需品生產行列。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后,受日本政府戰時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大部分工業企業都直接或間接地轉向了軍需生產。從1937年10月起,日本連續實行了兩次“中國事變”軍需動員計劃。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國民總動員法》,稱:“今逢戰爭時期,為達國防之目的,冀發揮國家全體之力,擬對人力、物力資源等,加以統制運用……” 此后,政府根據需要不斷安排民間企業轉向軍工生產,絕大多數日本企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綁到了戰爭的車輪上。像30年式刺刀這樣的冷兵器,也同樣被安排到了許多不同的民間企業進行生產。為了相互區分,刀身上多打有相應的廠徽或其他標記,這些標記是鑒別30年式刺刀出處或品評其價值的最直接的依據。為了保證產品質量,這些民間企業往往都歸屬數個國營大兵工廠領導和監管,大兵工廠在民間企業內設有監督班,負責監管軍需品的生產,其產品上除帶有本企業的標記外,在經監督班驗收合格后,再打上對應的大兵工廠的廠徽,所以這一時期的許多30年式刺刀上都打有對應制造廠和監制廠的兩個標記。
一般來說,30年式刺刀的廠徽都打在刀身右側靠近護手處,由一些簡單的圖案組成,代表不同的制造廠和監制廠,有的在其下方還打有漢字,常見的有“石”、“菅”、“尚”、“和”、“高”等(圖1 (b))。此外,在刀柄尾端頂部,也常打有長度為5~7位阿拉伯數字的號碼,有的數字前還有1至2個假名,有的早期生產型在數字的上方或下方還打有漢字標志,以“名”、“阪”、“和”為多,也有打有“昭”、“仁”等字的(圖1(a)),這些假名和漢字應該是對應著某個驗收者或生產廠。
最初生產的30年式刺刀,有的像18年式刺刀那樣,在刀身右側靠近護手處打有“東京炮兵工廠 明治××年造”的漢字標志,有的在刀柄上打有西門子公司的標志,有的像大多數日制步槍一樣刻有象征天皇的16瓣菊花的徽記。但這些只是極少數,后來生產的30年式刺刀,則統一改為打制造廠和監制廠的標記,目前所能見到的都是后者,主要有以下幾種。
東京炮兵工廠(Tokyo Hohei Kosho)或小倉兵工廠(Kokura Rikugun Zoheisho)
從建廠到二戰結束,日本陸軍的絕大多數武器都是由東京炮兵工廠及后來的小倉兵工廠供應的,其中也包括刺刀。東京炮兵工廠前身是幕府于1861年(文久2 年)2月興建的關口制作所,它是日本第二家近代兵工廠,1863年5月投產,主要制造火炮。1868年4月,該所被明治新政權接管,專門生產步槍等武器。1870年起稱為東京炮兵工廠,因位于小石川(Koishikawa),又稱小石川炮兵工廠, 1923年起改稱東京陸軍兵工廠(Tokyo Rikugun Zoheisho)。1935年,該廠遷至小倉并改稱小倉兵工廠。從東京炮兵工廠到小倉兵工廠,廠徽始終都是一個圓圈外圍繞三個半圓(圖2),表示從上方俯視時的四枚疊放在一起的球形炮彈,以紀念該廠從生產火炮起家的歷史,該廠徽從1898年一直沿用到1945年。

光精機制作株式會社(Hikari Seiki或Hourglass)
該廠是小倉兵工廠監管的下屬生產廠家。關于廠徽的含義,以前曾有人釋為沙漏,實際上為一透鏡(圖3),表示該廠的主要產品是軍用光學精密機械。該廠位于臺灣高雄,其他情況不詳。

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Matsushita National)
該公司是日本著名的民營企業之一,于1918年(大正7年)3月在大阪大開町設立。從1937年開始,該公司積極投身于收發報機、電話等軍用通信設備的生產。1938年初,其下屬的松下金屬公司(Matsushita Kinzoku)開始接受陸軍省訂單,生產機槍彈彈殼,后來逐漸擴展到大多數常規兵器。其間生產的30年式刺刀上僅打有一個標記(圖4(a)),與小倉廠徽相類似。稍后松下金屬公司成為小倉廠的監管企業,廠徽改為中間有字母 “M”(松下的縮寫)的箭(圖4(b)),同時在左側打有小倉廠徽,但也有單獨打有松下標記(圖4(c))的刺刀。到1944年初,日本全國572家指定軍需品生產企業中,松下公司下屬企業就有7家之多。松下公司對戰時軍需生產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甚至是傾盡全力的,對侵略戰爭的“貢獻”也十分突出,但戰后這一點并未受到追究,目前該公司仍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器生產和經銷商之一。


名古屋兵工廠(Nagoya Arsenal)
該廠于1923年設立,是規模僅次于小倉兵工廠的日本第二大陸軍兵器制造廠。其廠徽為大圓中包含上大下小的兩個外切圓(圖5)。名古屋兵工廠除自身參與生產外,還負責監管若干下屬企業。與小倉廠不同的是,名古屋廠的廠徽打在生產廠家的右側。不過單獨打有該廠徽的30年式刺刀并不全都是在名古屋生產的,同樣使用該廠徽的還有位于愛知縣春日井市的分廠,即1939年7月設立的鳥居松(Toriimatsu)制作所,該廠占地約100公頃,有工人12000人,主要生產99式步槍、狙擊步槍及30年式刺刀。1945年日本投降后該廠被撤銷。
田自動織機株式會社(Toyoda Au to mat ic Loom或Toyoda Jidou Shokki)
該廠是名古屋兵工廠監管的下屬生產廠家。廠徽為4條相互交叉成菱形的線條,代表織布時交叉的經緯線,中間為自動的“自”字(圖6),根據“自”字末筆寫法不同,又分為兩種。該廠除生產30年式刺刀外,還生產過“二式短劍”,實際上就是縮短的30年式刺刀,配用于1942年(神武紀2602年)定型生產的二式傘兵步槍。與30年式刺刀不同的是,二式刺刀的廠徽標記打在刀柄背部的金屬部分上。該企業在戰后仍然存在并繼續發展,目前是我國紡織業所用自動噴氣織機的最大供應商。
理研鋼材公司(Riken Kouzai)
該廠是名古屋兵工廠監管的下屬生產廠家。廠徽為一個菱形中間有兩條平行的豎線(圖7)。該廠的前身是1927年在東京成立的理化學振興事業株式會社(理化學研究所),制造汽車用活塞環。1941年,發展為理研重工業株式會社和包括理研鋼材公司在內的理研康采恩,戰時生產飛機、汽車用活塞環和鋼鐵等。現今理研株式會社仍然存在,主要生產汽車零部件。
金城鑿巖機制造公司(Kanashiyo Sakugan-ki)
該廠是名古屋兵工廠監管的下屬生產廠家。廠徽為五角星內有一“K” 字(圖8),五角星為日本陸軍的象征,“K”應為神奈川縣(Kanashiyo)的縮寫。該廠具體情況不詳。

仁川兵工廠(Jinsen Arsenal)
其廠徽為五角星內有一類似樹葉狀的圖案(圖9),有人認為是象征著榮譽的桐葉。根據中間圖案的大小,廠徽可分為兩種。日本在侵占朝鮮后,于1923年在該地設廠,主要生產38式、99式步槍及刺刀等輕武器,是朝鮮半島上最大的日軍兵工廠,并在平壤、元山等地設有多個分廠和監督班。1946年后大部分被朝鮮人民軍接管。
奉天兵工廠(Mukden Arsenal)
Mukden即奉天,為沈陽的舊稱,也有稱其為滿洲(Manchuria)兵工廠的。該廠前身是1916年軍閥張作霖設立的奉天軍械廠。“九·一八”事變后,該廠被日軍占據,1932年在其基礎上組建了奉天造兵所株式會社,1937年擴建后改名為奉天兵工廠。該廠是日本在中國境內設立的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兵工廠,主要為日軍和偽滿軍隊生產各種輕重武器。日據時期,該廠廠徽為一個被三等分各種30年式刺刀廠徽的實物照片的同心圓(圖10(a))。日本投降后,奉天兵工廠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并于1946年11月改為兵工署第90廠,其間繼續改造和生產部分日式武器,不過廠徽有所變化(圖10(b)),但打有后一種廠徽的30年式刺刀大多較為單薄和簡陋,有的比日本二戰末期的產品還要粗糙。1948年底沈陽解放后,90廠被人民解放軍接管,并成為626廠等諸多國內現代軍工企業的前身。
圖11中所示的4種廠徽對應的生產廠家尚不明了。圖11(a)為向下的等腰三角形,可能是三愛工業公司;圖11(b)為疊壓在錨上的五角星,外文資料中稱這個標記為Rocking Star,估計生產廠家與海軍有關,或者是為海軍生產的某種武器上的刺刀;圖11(c)中單獨的五角星既可以代表日本陸軍,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隊的標志,所以認為這些刺刀是日本生產和國內八路軍、新四軍兵工廠生產的兩種看法都有。但從實物來看,打有五角星的刺刀一般都是早期型號,且工藝較為精細,特別是血槽加工較為規整,與根據地兵工廠手工生產刺刀的情況明顯不符,個人認為日本生產的可能性更大;圖11(d)所示的廠徽為菱形內帶“60”字樣,風格與日本兵工廠截然不同,應為國內廠家仿制產品。國內稱為60廠的有兩家,一是1945年11月成立的京滬地區兵工廠接收處,1946年9 月改稱兵工署第60廠,但主要生產美式武器。二是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由西北制造廠等與晉興機械廠合并成立的第60兵工廠。由于打有該標記的30年式刺刀現多在山西、河南發現,且皆為早期型號,做工較為精細,故是后者生產的可能性極大。
圖12(a)與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徽記近乎相同,估計代表海軍兵工廠或橫須賀海軍工廠,打有該標記的30年式刺刀和95式士官刀在國內均存有實物。圖12(b) 對應廠家是東崎株式會社,該廠也是小倉兵工廠的監管廠之一,此廠徽主要見于95式士官刀上;圖12(c)對應的廠家主要生產輕武器彈藥,產品上多有打“ム” 標記,其他情況不詳;圖12(d)為大阪炮兵工廠,廠徽為兩門交叉的舊式野炮,該廠亦是日本近代兩大陸軍兵工廠之一。1870年2月,明治政府接管幕府的長崎制鐵所,將部分機器設備和工人遷至大阪,創建大阪制造所,后改稱大阪炮兵工廠,主要生產山野炮、海岸炮和攻城炮等重武器和配用彈藥。
除此之外,現存實物中還有大量的無標記30年式刺刀,其中一些加工精細,另一些則較為粗糙。這里面多數是國內各兵工廠所仿制的刺刀,可能也有一些是日本原產的。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各抗日根據地兵工廠制造了大量刺刀,僅1942年晉察冀軍區就生產了4.7萬余把,原材料多是鋼軌及炮彈彈體,但其中仿30年式刺刀并不多,除極少數是為仿造的部分日式6.5mm步槍配套制造外,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彌補戰斗中的損耗。抗戰結束后至1950年前后各解放區仍在仿制30年式刺刀,不過數量依然不多。總的說來,國內仿制的30年式刺刀大多較為粗糙:一是刀身鋼材中雜質多、易銹蝕,有的還有“夾灰”現象;二是鋼火差,易彎折、易斷裂;三是刀身較薄較窄,護手、卡筍部分單薄;四是血槽部分多數為手工制造,有的系用鋼棒在燒紅的刀坯上砸成,有的是用鏨子在刀身上直接鑿出,邊緣較不規整,槽內也不平滑。
30年式刺刀在戰爭中的使用
30年式刺刀是日軍中使用最為廣泛的冷兵器之一,到二戰結束為止,有據可查的生產數字約為680萬把,比1906至1945年的40年間日本各種步槍的總產量還要多40萬,實際生產數字肯定更大。30年式刺刀除可配用于38式、99式及一式等各型步槍外,還可以配用于96式、99式等輕機槍,這在其他國家也是相當少見的。在日本陸軍中,除曹長(上士)以上佩帶手槍和軍刀以外,包括部分軍曹(中士)在內的大多數士兵都是人手一把30年式刺刀,海軍等其他兵種的警衛部隊和憲兵也有配發。此外,并不廣泛使用步槍的炮兵部隊的炮手、馭手等也多有佩帶,主要作為個人自衛武器和日常工具使用。38式步槍全槍較長,裝上30年式刺刀后,更是長達近168cm,彌補了日軍士兵身材普遍較為矮小的缺點,加上刀身較長、厚重結實,殺傷力很強,在拼刺時占有相當優勢;同時日軍非常重視白刃格斗技能,入伍的新兵要經過嚴酷的長時間拼刺訓練及體能鍛煉,因此刺刀肉搏近戰成為日軍在作戰中經常使用并且占有一定優勢的戰術。
30年式刺刀在日軍中受到重視由來以久,它的第一次大規模使用是在日俄戰爭中。1905年1月25日到28日,在沈陽會戰前夕的黑溝臺戰斗中,立見尚文將所率第八師團殘余部隊組成“立見軍”,并自命為臨時司令官,在第五師團的援助下,全體以刺刀進行突擊,成功解除了俄軍對自身和秋山好古率領的騎兵第一旅一部的包圍,并反敗為勝。這一次的勝利作為以師團為單位執行“白兵突擊”(白兵突擊(はくへいとつげき)是日軍在進行白刃戰時所喊的口令)的成功戰例,助長了日軍作戰指導思想中濃厚的唯意志論傾向,以至于把“刺刀突擊、白刃決勝”稱為是“攻擊精神”的結晶,過分夸大白刃格斗和精神力量在戰爭中的作用,到后來30年式刺刀甚至成為日本陸軍的主要象征。1909年,“決定戰斗最終勝負的方式是刺刀突擊”被寫入《步兵操典》。一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投降為止,“利用刺刀進行短兵夜襲攻擊”始終是日軍的基本作戰信條。

實際上,30年式刺刀的神話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騙局。同樣是在日俄戰爭中,1904年11月26日,為奪取旅順口東線松樹山堡壘,日軍組織起以中村覺少將為首的3 000人敢死隊。出發前中村覺要求“我們將以刺刀打擊敵人,不管敵人火力多猛,在敵陣地上立足未穩之時,誰也不準開槍”。當日18時許,日軍敢死隊破壞鐵絲網后向堡壘發起沖擊,被俄軍2個缺編的水兵連以白刃格斗阻止在胸墻一帶。戰至次日凌晨2 時,敢死隊傷亡過半,中村覺亦中彈負傷,被迫撤退,這一次以刺刀對抗機槍和鐵絲網的大規模“白兵突擊”便以日軍告負而草草收場。30年之后,在南洋的熱帶叢林中,當日軍面對火力占絕對優勢的美軍時,任何依靠30年式刺刀進行的“白兵突擊”往往都是以尸橫遍野的慘敗而告終。在中國戰場上,大規模刺刀戰的情況也很少出現,白刃戰多是以排、班為單位來進行。但面對裝備處于劣勢的中國軍隊,白刃格斗一如既往地成為日軍的強項。抗戰期間犧牲在日軍刺刀下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是國民黨第79軍軍長王甲本中將,他于1944年9月7日在湖南省東安縣山口鋪附近與日軍的遭遇戰中,被敵刺中腹部壯烈殉國。到抗戰后期,敵我力量及戰術能力發生了彼消此長的變化,同時日軍中有經驗的老兵也逐步損失殆盡,拼刺刀逐漸成為一種得不償失的“精神戰法”。到戰敗投降前夕,日本在“全民玉碎”的口號下,在本土及各殖民地的日本僑民中組織了各種“肉攻隊” 和“特攻隊”,而其中的多數人連步槍也沒有,只有綁著30年式刺刀的木棍和竹扎槍,試圖進行自殺性的“本土決戰”,以刺刀來對抗盟軍的飛機和坦克,30年式刺刀因此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后瘋狂的歷史見證物。
30年式刺刀之所以在中國人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像,并不是因其在戰場上的表現,而在于它是屠戮中國人民的最主要兇器之一。日軍始終認為,用刺刀來“處理”戰俘和平民,既節約彈藥、又不會發出多大聲響,而且可以有效地震懾民眾,使其打消任何反抗的念頭。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這種“處理”辦法更是殘酷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原日軍士兵外賀關次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殘兵敗卒,便槍殺或刺殺了他們……在南京南門車站,工兵隊的膽大妄為者刺殺或綁成十字地刺殺了中國兵70名左右。城外,尚有許多人躺在敵人的尸體堆里,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最后通過我們的手送他們上西天者,不知其數。……”《東京昭日新聞》隨軍記者鈴木二郎在回憶錄中也談到了在中山門城墻上對俘虜的集體屠殺:“……俘虜在25米寬的城墻上排成一行,一個個被刺落到城外。許多日本兵舉起刺刀,使勁地吆喝著,再向俘虜的胸膛和腰間刺去,只見鮮血飛濺,陰森森的氣氛使人毛骨悚然。在那里,我又看到了前一天在中山路勵志社,日本兵把我錯當成是中國人而企圖刺殺我的一副兇相。……”對平民的虐殺行為更是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當時的安全區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在信中寫道:“12月18 日……有個5歲的男孩被送到醫院來,他被刺刀戳了5刀,1刀戳穿了腹部;有個男子,身上被刺刀戳傷了18處;有個婦女,臉部有17處被戳傷,腿部也給戳了好幾刀……”在其后的各次作戰和“掃蕩”中,30年式刺刀成為屠殺中國人民的 “效率”最高的武器,將戰俘和平民作為活靶練習刺殺的慘劇更是一再發生。在整個抗戰期間,倒在30年式刺刀下的中國民眾要以百萬來計數。從這個意義上說,30年式刺刀可謂是臭名昭著,如今存世的每一把該型刺刀都可能見證過這一段浸透中國人鮮血的屈辱歷史,都可以說是日本侵華和大屠殺的鐵證。
二戰期間,30年式刺刀除了裝備日軍外,還廣泛地裝備偽滿洲國和汪偽軍隊,受到日本支持的泰國、緬甸等國的仆從軍隊也有使用。雖然日本在二戰后不再生產30年式刺刀,但實際上戰后日本陸上自衛隊、警察預備隊和保安隊仍裝備該型刺刀和99式步槍,直至被自產的64式步槍所替代。在中國,30年式刺刀的生產一直持續到1950年以后。在抗戰中繳獲的大量日制步槍和30年式刺刀在解放戰爭中被繼續使用,并且其中大部分最終成為人民解放軍的裝備,為人民解放事業立下汗馬功勞,那一時期的許多紀念碑甚至是徽章上都有該型刺刀的身影出現。抗美援朝開始后,入朝作戰的志愿軍中仍裝備有部分38式步槍和30年式刺刀,而先期從朝鮮半島撤出的蘇聯紅軍也將繳獲的包括30年式刺刀在內的大量日制武器交給朝鮮人民軍使用。在國內,30年式刺刀和38式步槍一直使用到1970年代末,才最終從民兵裝備序列中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