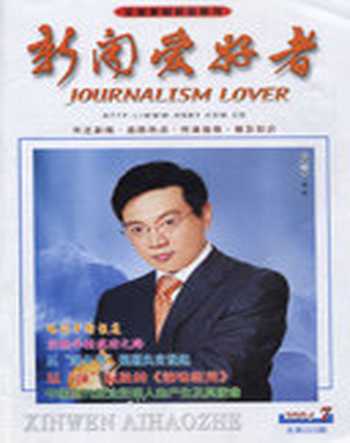維護黨的利益反映人民呼聲
聶廣鵬
按照報社的安排,我在3月24日至4月1日的9天里,對新鄉市一重點工程毀壞古漢墓事件作連續報道,前后共發了三篇消息。同時,編輯部配發了出版部副主任任鵬同志撰寫的三篇評論。這一組極具戰斗力的批評報道,充分體現了黨報對漠視法律、違反政策事件的高度關注,樹立了河南日報的權威,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反響。
3月29日,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河南新聞聯播先后播發了新鄉“毀寶”的電視消息;香港鳳凰衛視的記者也向我詢問情況,索要有關資料;3月30日中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新鄉市“毀寶”工程仍在繼續》一文和點評,新華網、人民網、雅虎網、新浪網、河南報業網等全國主要網站均對30日的消息和點評予以全文轉載;3月31日,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桂娟和朱祥到施工現場采訪,4月2日新華社向全國各主流媒體發了《新鄉一重點工程為趕工期毀掉漢墓23座》通稿和一組三張照片,上述幾大網站又予以分別轉載;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中國青年報等媒體也先后發了該事件的消息。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祥批示河南省文物局認真調查。4月5日上午,省文物局在已經多次電話過問的情況下,又指派兩位處長到新鄉“毀寶”現場調查處理。
迫于輿論監督的巨大壓力,該市不得不于3月29日下午全面停工,按照文物保護法精神,先勘探挖掘再進行工程施工。3月31日下午,我到工地現場采訪后,根據新鄉市領導的先后表態,又及時采寫了《變“毀寶”工程為“護寶”工地》一文,至此該組報道畫上了句號。這組報道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保護了新鄉市王門村這一古漢墓群文物,更在于這一組系列報道產生的社會意義:使之成為一次范圍廣泛、聲勢浩大的普及文物保護法教育。
這組文章廣泛傳播之后,各級文物部門、領導干部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好評;施工單位認為,這組報道給他們上了很生動的一次文物保護法律知識教育課;文物部門表示,輿論監督起到了他們百般努力難以奏效的作用;普通讀者認為,毀壞文物實在不應該。僅以新鄉地區為例,文章刊發后,施工單位到新鄉市各級文物部門申報文物勘探的就絡繹不絕,成為新鄉文物保護史上的空前奇觀。
4月份,考察中原城市群的院士提出,河南在發展中要注意文物保護;4月22日,國務院參事一行20多人在結束了在河南為期9天的考察后,向省政府領導反饋意見。其間國務院參事沈夢培在向河南省政府的建議中,專門將河南文物保護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用了5分鐘的時間、從3個方面詳細講述了河南在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中保護文物的重要性。他說,“河南地處中原,是華夏民族的孕育之地,保護好文物,就是保護好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尤其要求“要特別加強對施工單位的教育”。
采寫這組報道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報社的高度重視是這組稿件能夠發出、發好的重要保證。3月24日我采寫好第一篇稿件后,就向市地記者部和朱夏炎總編輯匯報。朱總指示有關同志將該稿件送省文物局領導征求意見。省文物局領導當即給予“可發”的批復意見。總編輯助理、編委委員熊志波、值班主任劉翔明、趙克中、任鵬和夜班編輯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在省委黨校學習的記者部主任陳貞權聽到匯報后,也多次過問和指導這組輿論監督稿件的采寫。尤其是新聞出版部值班主任任鵬同志,對我發過去的每一篇消息均寫出了很有分量、力透紙背、畫龍點睛的點評,為這一組稿件更好地發揮戰斗作用、體現黨報的權威增添了色彩。
其次,文章的客觀性是輿論監督的“生命”。這組報道“火藥”味很濃、傾向性很強,但新鄉市沒有任何人對報道的客觀性有任何懷疑。盡管存在“地方保護”問題,新鄉市的個別領導同志暫時也有些不理解,但面對言之鑿鑿、毀壞文物的事實,也是拍案而起,要求盡快落實文物保護法精神。
這組報道在表現手法上,我堅持既不當“審判員”,也不當“宣判員”,而是當好事件的忠實記錄者。在26日見報的消息中,記者通篇采用的語言都是事件當事人、漢風博物館館長老張的敘述。這樣既提高了消息的可信度,又為避免輿論監督中的“新聞官司”留下“后手”。
批評報道如果不傾注記者本人的真情實感,就不可能有震撼力,在打動受眾上就會大打折扣。因此,26日見報的消息一開頭便是“10多輛挖掘機揮動著巨鏟,40多輛運輸車來往穿梭,一座座古墓慘遭毀壞,面對這種狀況,文物保護專家痛心疾首地吶喊——‘快來救救這個漢代古墓群!”用這些話作引題和標題,編輯部用的版面語言——對標題加黑框,增強了文章的沖擊力。
由于新鄉市對這篇報道置之不理,3月30日見報的標題就更具震撼力:《無視國家法律拒絕輿論監督新鄉市“毀寶”工程仍在繼續》,編輯部又對標題作了加黑框的特殊處理,更加吸引讀者的眼球。對第三篇消息稿件,值班領導改定的標題是《新鄉市領導明確表示誠懇接受批評歡迎輿論監督變“毀寶”工程為“護寶”工地》,使受眾對新鄉市“毀寶”事件的態度一目了然。
再次,輿論監督只是鞭撻假、惡、丑的手段,旨在促進黨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我作為駐地記者站站長,很了解這一工程在當地的位置,也清楚它的竣工和投入使用是新鄉市“五城創建”、申報國家級衛生城市的必要條件。但對此背景并未提及,完全是顧及新鄉市領導的“面子”。而在幾篇文章中先后表述了“新鄉市重點工程”、“這個項目我們和市里簽訂了責任書”、“建設項目再重要,也要遵守文物保護法規”等關鍵語句,相信細心的讀者能夠讀懂字里行間的含義。這組報道合理地處理了情與法的關系。同時,記者在進行報道期間,就建議有關各方迅速組織人力、物力對文物進行勘探、挖掘和保護,并在第三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表明,希望“這一環保工程盡快開工”,這都為以后和緩地解決問題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這組報道的前兩篇消息被評為3月份河南日報的好稿,4月份又被授予“精品獎”。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由此使我進一步確信,黨報記者只要把黨的利益、人民的呼聲放在第一位,他就會在關鍵時刻沖向前,而不會顧及苦和累、得與失。也只有這樣,他才會一心一意為黨的新聞事業盡心盡力,才會多抓到一些“活魚”,最終得到讀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