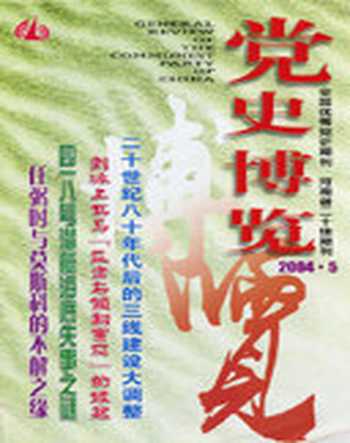任弼時與莫斯科的不解之緣
姚 勇
17歲的任弼時和劉少奇、羅亦農,肖勁光等同船赴蘇。在俄羅斯檔案館里,至今仍保留著任弼時當年填寫的調查表
1921年5月,上海外灘碼頭一艘蘇聯郵輪起錨了。船上有一批中國五四時代的新青年,他們是任弼時、肖勁光、任岳、劉少奇、羅亦農、蔣光慈等。這些年輕人將奔赴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尋找救國之路。
注目漸漸遠離的祖國,遙望水天一色的遠方,憧憬著光明的未來,任弼時心潮起伏。
還是去年夏天在湖南長沙聯立中學讀書的時候,一日,任弼時外出,路遇在船山中學讀書的同鄉任岳,得知長沙正在籌組“俄羅斯研究會”,以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從事實際調查、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為會務內容。這個學會由毛澤東、彭璜等人負責。任岳就讀的船山學校校長賀民范也是學會一員。任岳說,可以通過他介紹加入俄羅斯研究會,爭取去蘇俄留學。那天中午,任弼時和同學肖勁光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著,商量的結果,兩人決定加入俄羅斯研究會。肖勁光后來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
有一天,弼時同志從街上回來,看到我高興地說:“有辦法了,有辦法了!”我忙問他有什么辦法,他說:“我們到俄國去。”那天中午,天氣很熱,我們躺在宿舍的床上,輾轉反側,興奮得睡不著。去不去?還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文憑還要不要?商量來商量去,兩人都橫下一條心:去。
1920年8月,作為長沙俄羅斯研究會派出的第一批學生,任弼時和肖勁光等一行6人從長沙乘小船至岳陽,換乘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做赴蘇準備。8個月后,他們踏上了赴蘇俄的旅程。郵輪在日本長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直奔海參崴。在海參崴,他們與共產國際機關秘密接上了頭,換好介紹信,作了職業化裝后,改乘火車繼續前進。對這段歷史,肖勁光后來曾回憶說:
我們倆人為一組,分別化裝成理發和裁縫學徒工人,一路來到西伯利亞。開始還算順利,在通過最后紅白交界的關卡時,弼時同志不幸被白匪以“鼠疫患者”為由給扣留了。我們心急如焚,但也無能為力,這對只有17歲的弼時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但他表現出驚人的沉著、鎮靜和隨機應變的能力,終于擺脫了白匪的盤查,過了關卡,只身一人趕到伯力與我們會合了……從伯力經赤塔去莫斯科,我們乘的是悶罐火車,沒有開水,沒有暖氣,上車前每人領到一個像枕頭一樣的黑面包,餓了就啃幾口,但誰也不敢多吃,因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悶罐車載著我們,直到1921年7月9日才爬過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亞鐵路抵達莫斯科。
到達時,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在莫斯科召開。任弼時一行當即被安排在共產國際招待所,會議組織者讓他們以東方民族代表身份輪流列席大會。會后,任弼時等人于8月3日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10月21日,正式開學。任弼時和劉少奇、羅亦農、肖勁光、任岳等成為中國班第一批學員。為了以后回國從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進中國班,每個人即獲得一個俄文名字,任弼時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時,他將原名“任培國”,改為后來人們所熟悉的“任弼時”。
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國班設有政治經濟學、西方革命運動史和歷史唯物主義等課程。他們最初的學習很吃力,教師全部用俄語授課。課堂上,要靠翻譯一句一句地譯,斷斷續續,很影響聽課效果。任弼時不甘于只聽翻譯“譯課”,下決心利用一切機會學俄語。1922年3月5日,“東大”下發旅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調查表,以了解留俄學生近半年來的學習和對革命的認識情況。現在的俄羅斯檔案館里,仍保留著當年任弼時填寫的調查表。筆者挑選幾條,我們從中不難看出當時一代青年志士的愛國深情和政治素養。那時,任弼時才18歲。
1.來俄的目的:實際考察勞農俄國,觀念明確,回國做革命運動。
2.政治經濟和俄文學得怎樣以及有何心得:政治經濟以前是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一個大概,算是有進步,俄文也算有進步。
3.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及旅俄青年共產黨的意見:對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我覺成分太復雜,辦事欠人才,共產黨應有?眼負?演責任整頓才對。對于旅俄青年共產黨,也是要養成個人能信主義。
4.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意見:中國農民,無產業者少,這是很難宣傳的地方。要到鄉村組織一種農會,向農會去宣傳,以這種農會做宣傳的動機,用經濟眼光去解釋他們將來的危險地位,使他感覺到將來的危險,或者也可使他為自己的地位,加入無產階級斗爭。
5.現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現在是想求點革命的工具,使自己的觀念明白,將來也要做點革命工作。
6.打算什么時候回國,回國后,干什么事情:回國問題,只是工作之緩急,不過自己的工具,還覺不足供用。若是回國,沒有相當可以運動的機會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廠做點工人運動的工作。若是有機會,我很愿意多求點應用的工具。
那時的任弼時雖然青春年少,但我們從上述字里行間能體會到他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追求進步的強烈信念。一年以后,原來擔任西方革命運動史課堂翻譯的瞿秋白奉調回國。由于任弼時出色的俄文水平,他接替了瞿秋白的課堂翻譯工作,一直到1924年結束在“東大”的學習生活。
旅俄學生初到“東大”時,物質生活條件極差,標準很低。學生們享受供給制,吃飯、穿衣、住房子都是學校供給。剪發、沐浴、洗衣也是學校負責。每月有1元5角新盧布的零用錢,吸煙的人可以領到一些煙草。和任弼時一起學習的肖勁光曾回憶道:
食品供應,“東大”的學生們享受著紅軍的待遇:每日兩塊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幾個土豆。午飯,有時每人有一勺湯,是海草和土豆煮的,偶爾放一點咸魚。他們穿的衣服,都是歐洲工人捐獻的。任弼時個子沒有歐洲人那么高大,也分得一雙很重的大皮靴、一件黃色麻布上衣、一件軍大衣、一條皮帶、一頂尖尖的上面綴著紅五星的帽子。晚間,房間里燒一些木柴烤火。睡覺時大家都是一個挨一個,擠在一起取暖。沒有被子,只蓋一件軍大衣和一條毯子。
1922年冬,陳獨秀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共產國際特意慰勞了一次中國班的學員們,發給每人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豬肉,這在當時都是稀有的珍品。任弼時和好朋友肖勁光、任岳、周昭秋等幾個老鄉湊在一起,找到一個盛開水的罐子,在四樓的教室里,把所發的全部吃食都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大吃了一頓!這種匱乏的物質生活狀況,直到1924年隨著全蘇經濟的好轉才逐漸得到改善。
在中國班,無產階級政黨嚴格的組織訓練與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是同時進行的。1922年12月,任弼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后來,分散在法國、德國等歐洲各國的青年共產黨人請求轉到“東大”學習,得到陳獨秀的同意,由趙世炎率領第一批12人于1923年4月來到莫斯科。旅歐同志的到來,壯大了旅莫支部的隊伍,黨員從13人增至23人,占當時中共黨員總數的5%,團員達35人。按中共黨章的規定,成立了支部委員會,有系統、有組織的訓練自此開始。
在“東大”的三年,任弼時有機會參加過幾次大型的國際會議,開闊了眼界。1921年11月12日,帝國主義為重新劃分遠東及太平洋勢力范圍召開華盛頓九國會議。為對抗此次會議的召開,1922年1月2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起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中國派去了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進步團體的廣泛的社會代表,中共代表張國燾為團長。任弼時和劉少奇、肖勁光、卜世奇等數名“東大”學生也作為代表出席了大會。
當時,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物質生活尚處在極度匱乏中,盡管東道主盡了最大努力,代表們仍不免感到饑餓。任弼時等節省下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到代表團的住地去慰問他們。這讓代表們在幾十年后提起來還十分感動。張國燾在回憶“東大”的中國學生時寫道:
還有一件事令我感到異常親切,留下了永久不忘的印象:當時東方大學的8位青年中國朋友,用長時間省儉下來的馬鈴薯,款待我和其他幾位中國代表。這一小盤馬鈴薯非任何貴重物質所能換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與友愛的象征。
1924年1月22日,列寧逝世的噩耗傳到“東大”,任弼時滿懷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領袖肖像,擺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由于他的俄語講得好,又曾擔任中國班支部的執行委員,與“東大”支部的人比較熟悉,得到一個和“東大”支部一起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機會,不用排隊。于是,任弼時叫上蕭三一起加入到“東大”的行列中。當他倆隨隊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廳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東方民族參加“榮譽守靈”。這是葬儀中一項特殊榮譽性任務。每批4人,每次5分鐘。4人分立距列寧遺體周圍約六七米遠的四角。任弼時站在列寧右肩方向,蕭三站在列寧左腳方向,垂頭默立。60多年后,蕭三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不無激動:
在短短的5分鐘里,感想千千萬萬。我低著頭,眼睛望著安詳靜睡的列寧,5分鐘內沒有眨一下眼。
1924年,中國的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國內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陸續派人回國。同年7月23日,任弼時“東大”畢業。回國前,任弼時的堂哥任作民前來為他餞行。任作民在回憶時說:
臨行前夕,我和他來到列寧墓前。我問他:“你已經決定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了么?”“決定了。”他簡短而明確的回答。那時他20歲。
不久,任弼時和陳延年、鄭超麟等啟程返國,于8月抵達上海,開始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中國革命。
第二次赴莫:作為中國青年團中央總書記出席少共國際執委擴大會議
任弼時回國后的第一項工作,是按照黨的安排到上海大學講授俄語,同時參加青年團中央的工作。他擔任青年團江浙皖區委委員及團中央宣傳委員會下設編輯部的編輯員,和張伯簡、鄧中夏等負責編輯《中國青年》和供給《團刊》、《平民之友》稿件。這期間,任弼時用“辟世”、“辟時”、“弼實”、“辟古”等筆名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給當時的青年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5年1月26日,經過精心籌備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任弼時代表旅莫地方組織出席大會,并當選為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會上,他與張太雷、惲代英、賀昌、夏曦等9人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三屆一次全體會議上,又與張太雷、惲代英、賀昌等5人組成中央局,分工任組織部主任。是年5月,任弼時開始代理團中央總書記。7月21日,共青團中央局會議決定任弼時任團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
在舉世矚目的五卅運動中,任弼時組織團中央一班人馬,密切配合黨中央指導青年運動,大力發展青年團組織,同時向黨組織輸送了大批優秀團員,壯大了黨的隊伍。據1925年9月統計,全國團員人數已由團三大時的2400多人發展到9000多人,增加了近3倍。
任弼時剛從國外回來,就趕上場面如此恢宏的群眾斗爭,斗爭的曲折與復雜磨煉著年僅21歲的青年團中央總書記,促使他在政治上和革命實踐工作能力上一步步走向成熟。他在給仍在留學的羅亦農、王一飛的信中,告誡自己也提醒大家說:
此次回國同志……從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實際經驗,尤其是對于很普通黨團及工會組織工作,因我們在莫時沒有注意實際研究,以致不夠應用,甚至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所以我很希望你們能多將黨團、工會等組織教育等經驗以后能多注意,因為你們恐怕也快要回國了。
1926年下半年,任弼時赴廣東檢查團的工作,處理學生團體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時,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委會定于11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為出席該會,任弼時乘蘇聯郵輪“列寧號”離開廣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與新婚不久的妻子陳琮英一同赴莫。1983年2月,當年曾和任弼時乘坐一條船去蘇聯的廣州政協副主席饒衛華回憶道:
弼時同志來廣東處理問題時,我因為參加過一些團區委會,見過他。后來,我們乘同一艘船從廣州到上海。乘坐的是蘇聯船“列寧號”。上海第一次武裝起義時到上海。當時,我不知道弼時同志、陳琮英住在哪里。陳琮英沒有到廣東來,她是和楊尚昆等人從上海一路去的。1926年11月離開上海。11月7日是蘇聯國慶,在船上召開紀念會。1926年12月左右到莫斯科。到莫斯科時,陳琮英與我同班,才知道他們是同我們同時去的。
由于中國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青團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中國青年革命者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精神令各國代表贊賞。因而,共青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在會上受到各國兄弟組織代表的熱烈歡迎。會議結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寧格勒市的團組織特地邀請任弼時參加他們的大會。任弼時的第二次旅莫時間比預計的延長了。
1927年4月初,任弼時、陳琮英夫婦返回祖國。他們沒有料到的是,迎接他們是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以及15日國民黨右派在廣州進行的大屠殺。這使上海的共青團員由8000人驟減到3000人,童子團由4000人減到1000人左右。廣州團組織被摧殘,團員由6000多人驟減到3000多人,而童子團則大部分無形瓦解。嚴酷的現實,使剛剛抵達上海的任弼時對當時的革命形勢、對黨內右傾錯誤的認識越來越清晰了。
第三次赴莫,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任弼時為宣傳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立下不朽的功勛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國共合作再度形成。這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開展對日作戰。但是,國共兩黨二度合作的具體情況和合作后出現的新問題,共產國際卻不甚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共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出現了原則分歧。要想把全黨思想統一到正確方針上來,必須派人到共產國際說明與宣傳,以爭取共產國際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的理解與支持。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前往共產國際。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從山西前線回到延安僅20天,便攜陳琮英離開延安,取道西安、蘭州輾轉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再乘蘇聯飛機飛抵莫斯科。4月14日,任弼時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一份1.5萬字的書面報告大綱,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5月17日,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任弼時就書面報告又從以下4個方面作了口頭說明與補充:一、關于中國的抗日戰爭;二、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三、八路軍在抗戰中的狀況;四、關于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經過任弼時實事求是,很有說服力的報告和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戰中許多問題的認識轉變了。7月,王稼祥返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特意會見了王稼祥和任弼時,明確指出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9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同時,發出國際援華號召,從政治上、道義上、物質上援助中國抗戰。此后不久,直至今日仍為人們所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國的馬海德、奧地利的羅生特、印度的柯棣華等國際主義戰士,相繼來華支援中國抗戰。
王稼祥回國后,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繼而又向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代表們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王稼祥后來回憶時寫道:
我的報告是根據弼時在國際的報告、在國際的討論為主要內容。……在季米特洛夫與我們談話中有下列要點: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起,因而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這是季米特洛夫臨別時的贈言。
事過7年之后,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開幕式上曾這樣評價六屆六中全會: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任弼時的第三次莫斯科之行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長哥特瓦爾德有很多的工作往來,而且同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建立了廣泛的聯系;不但在國際講壇上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思想,親筆撰文在蘇聯《真理報》、《共產國際》雜志上向國際無產階級和蘇聯人民進行廣泛宣傳,而且組織人力翻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人的有關文章,在兄弟黨中分發。另外,1938年蘇聯外文出版局翻譯出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任弼時和代表團的同志們參加了校譯工作。當時參加這次翻譯工作的方志純曾回憶說: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任弼時主持翻譯并指示我們學習的。當時,任弼時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懂俄文的同志組織起來,一章一章地翻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其中第四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任弼時親自翻譯的。他們翻譯完一章,我們就學習一章。因此我們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譯本的最早讀者。任弼時的意見是,這樣既可以解決我們的學習教材問題,又可以檢查譯文的質量。后來,任弼時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中譯本帶回國內。1942年,黨在延安整風中,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為重點學習文件之一。毛澤東對任弼時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任弼時發現并負責地解決了被宗派主義干部路線打擊的同志的問題。他和周恩來一起,使沉冤六載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郁得以平反,使被“掛”了三年的原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部長吉合(張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師哲順利返國參加抗日戰爭。
陳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6月來到共產國際管轄的蘇聯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學習,其間還擔任過學生部的黨支部書記。蘇聯“清黨”、“肅托”結束后,陳郁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并被化名為“彼得”,放逐到伏爾加格勒拖拉機廠做工。整整5年,陳郁被排斥在黨組織之外。為此,陳郁寫了12封申訴信。1939年初,任弼時和周恩來一起到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商議解決陳郁的問題。不久,共產國際做出了取消1933年給陳郁的“最嚴重警告”處分,恢復組織關系,請中共代表團送其回國等決定。陳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如若不是弼時,我恐怕早就死在異國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稱弼時同志是‘黨內的媽媽,我認為,對于這個光榮的稱號,他是當之無愧的。”
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結束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調任弼時等回國。25日,任弼時同到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等離開莫斯科啟程返國。
第四次莫斯科之行,是專門同疾病作斗爭而去的。同10年未見面的女兒相聚,享受人生最后最為濃重的親情
1949年4月11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隆重召開。4月12日,任弼時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全面闡述了青年團面臨的形勢與任務,系統總結了青年團的歷史經驗。報告進行中間,任弼時因病體難支,后半部分由榮高棠代為宣讀。大會閉幕后,任弼時再一次病倒,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讓他休息養病。從此,任弼時搬到玉泉山休養所。5月8日,任弼時出現昏迷癥狀,經診斷發現,腦部血管已有器質性病變,眼底亦有小出血點。這時的診斷表明:任弼時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癥,腦血管顯著硬化,心臟初期機能障礙,腎臟初期硬化,并有輕度糖尿病,且病情在嚴重發展。
開國大典后,毛澤東為此專電斯大林,商量任弼時去蘇聯治療一事。11月下旬,中央決定任弼時去蘇聯就醫。1949年11月末,任弼時前往蘇聯治病。為了不給剛剛成立的共和國增加負擔,任弼時沒有讓家人陪護,只帶秘書朱子奇和醫生劉佳武隨行。12月上旬,任弼時抵達莫斯科,住進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療。
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訪問。這期間,毛澤東曾專程到克里姆林宮醫院及巴拉維赫療養院看望任弼時。任弼時也去看望毛澤東。一次,毛澤東留任弼時吃飯。飯桌上,任弼時向毛澤東建議,應該趕快派一批有較高政治覺悟,又有實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蘇聯來學習,培養建設新中國的各種專家。
毛澤東風趣地應道:“今后大規模的建設,沒有技術專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來取經。過去唐僧到西天取經,一路上騎的是毛驢,吃的是粗糧、野果,也沒有人歡迎接待,還要和妖魔鬼怪們斗法,好艱難啊!現在我們來取經,舒服得很啊!告訴那些來學習的娃娃們,要學習唐僧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還要學習孫大圣那種戰勝一切困難的精神,那他們就一定能取到真經。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療養期間,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同夫人朱仲麗曾多次到醫院看望任弼時。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抵達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談直至2月17日回國,在此期間也抽空到醫院看望老戰友。
在蘇聯療養期間,任弼時最開心的莫過于和分別10年的小女兒遠芳的重逢了。任遠芳是任弼時、陳琮英在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時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任弼時奉調回國。時值國內抗日戰爭艱苦的相持階段,考慮到路途的艱難和國內抗戰的形勢,為了回國后工作便利,任弼時把才剛1歲多的小女兒留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任遠芳在國際兒童院一住就是10年。她的童年是和蘇聯人民一起在艱苦的衛國戰爭中度過的。父母沒有給她留下絲毫印象,認識父親是她上小學四年級通過書信開始的,時間持續了近1年。
任弼時到莫斯科治病,在克里姆林宮醫院時,無法接女兒去住。他轉到巴拉維赫療養院后,就可以接女兒來住了。時值1950年元旦,在國際兒童院老師的帶領下,任遠芳來到了療養院。與父親的見面令任遠芳終生難忘。她回憶時寫道:
1950年初,爸爸來蘇聯養病,我再次見到了爸爸。自從懂事以后,在很長時間里我不知道自己有父母,更不知道父母是誰,是做什么的。見到父親時我問他:“你是爸爸陳林同志么?”……我同他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以后,深深感覺一種溫暖,這是我從來沒有領受過的。
任弼時十分理解女兒的心情。他沒有讓遠芳立即回國際兒童院,而是留在身邊住了8天。也就是這短短的幾天,遠芳被爸爸的愛深深地打動,投入爸爸的懷抱再也不想離開。這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是遠芳有生以來所從未經歷的全新生活。任弼時用濃濃的父愛給小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懷,給小女兒以父母親情與家庭概念的啟蒙。任弼時從教小女兒漢字、漢話入手,引導女兒回歸。8天,一晃就過去了。為了女兒的學業,任弼時還是將女兒送回了國際兒童院。
在遠芳離開療養院的第四天,任弼時見還沒有女兒的來信,就率先給女兒寫信:
你走了四天,但還沒收到你的信,我估計你能按時到達。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車上比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萬諾沃好嗎?11號趕到那兒了嗎?功課落下了嗎?溶下多少?你寫信告訴我。卡佳,你別忘了你說過的,每兩天給我寫一封信。這樣不會影響你的學習,我也可以不寂寞。……接到我的信,馬上回信。
接下來的一段是父女倆書信往返最頻繁的日子。除了表達彼此的思念外,主要是討論遠芳是否回國的問題。1950年1月20日,任弼時復信女兒,把女兒當作大人一樣,與之平等、嚴肅、認真地分析利弊,其間充滿了民主意識的循循善誘。信中寫道:
關于回國還是在蘇聯這個問題,我還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們再做決定。一、回國當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做為中國姑娘可以盡快學會中國話,這對你今后來說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將更多地了解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斗爭,這也對你非常重要;第三,你將和父親以及兄弟姐妹們生活在一起,這對你看來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為你不會講中國話,你回國后第一年只能學中文,然后才能上學(當然也可以在學校里學中文),你將耽誤一年的學習……
這就是供你選擇的具體情況。我想你最好留在蘇聯繼續學習,完成大學教育,然后帶著專業知識回國。這就是你在這里的時候我說的。
但是這一意見決不是最后決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慮對你怎樣更合適。如果你堅決要回國,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說的,如果我不帶你回國,你將永遠哭泣、思念,而且還會影響學習,那我將在莫斯科治療后,帶你一起回國。
正是在自己作主的情況下,任遠芳決定和爸爸一起回國。她接連給爸爸寫了3封信,向爸爸報告學習和生活情況,表示愿意和爸爸回國的決心。1950年1月30日,任弼時唯恐遠芳因要回國而心浮氣躁影響學習,便復信說:
上封信你已經決定和我一起回國。我希望你3月10日從伊萬諾沃來莫斯科,也就還有40天……你一定好好學習。我對你1月12日至26日的學習情況很滿意,并希望你繼續努力學習……我身體還好,血壓降到160(過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會痊愈。
然而,任弼時的身體沒有像他自己預計的那樣于2月底痊愈。拖到3月底,任弼時致電中共中央:
治療于本月底完畢。前日會診,認為結果良好,但為鞏固已得成績,速送我去黑海邊休息4至6星期后回國。
在黑海療養所期間正值春暖花開,任弼時的健康狀況較平穩,心情很愉快。5月9日,任弼時由黑海回到莫斯科。一周后,克里姆林宮醫院復查,醫生診斷為:一、第2—3期高血壓癥、糖尿病;二、第1—2期心肌營養不全;三、血管硬化。
鑒于任弼時病情有所好轉,醫生同意其回國。臨行前,醫生向任弼時提出建議:回國后先休息兩星期,9月再到療養院休養一個月;經常要有醫生照顧;工作時間要縮短,每日工作時間總共不得超過3至4小時;星期日必須休息。
1950年5月17日晚10時,任弼時父女及劉佳武從莫斯科乘坐列車回國。5月28日抵達北京。朱德親自到車站迎接。陳琮英也率子女全家出動,迎接任弼時的歸來。這是任家第一次全家團聚。任弼時高興地帶領全家拍了一張全家福。這也是最后一張全家的合影。
1950年10月1日,任弼時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國慶1周年慶典。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10月27日,年僅46歲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因病逝世。28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一同來到景山東街甲2號任弼時的寓所,親視任弼時的遺體人殮,并將一面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在他的身上。由四位領袖一起出席的追悼活動,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只有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