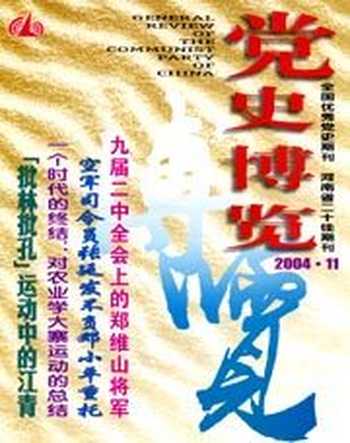俠肝義膽尤太忠
羅元生 張愛國
尤太忠(1918—1998),河南省光山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師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副軍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內蒙古軍區司令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成都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上被選為中顧委委員。
“文革”中,尤太忠見到鄧小平,立正、敬禮,還像戰爭年代一樣。鄧小平笑著問:“你怎么敢來?”尤太忠回答:“您永遠是我的老政委。”
從朝鮮戰場回國后,尤太忠先后任十二軍副軍長和二十七軍副軍長。“文革”初期,二十七軍駐防無錫。此時,尤太忠已是二十七軍的“掌門人”。
二十七軍是一支不平凡的英雄部隊。其前身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膠東軍區部隊。抗戰勝利后,膠東軍區主力進軍東北,余下的第五師、第六師和警備第三旅編為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許世友首任司令員。奠定九縱地位的是1947年5月進行的孟良崮戰役,此役全殲了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在淮海戰役中,九縱參加了碾莊圍殲黃百韜兵團,雙堆集圍殲杜聿明集團的戰斗。這兩仗打出了九縱的威風。1949年2月,華野九縱改稱解放軍第二十七軍,首任軍長就是大名鼎鼎的聶鳳智。
解放戰爭時期,尤太忠和李德生、肖永銀是王近山麾下的三只猛虎,人稱“三劍客”。當時王近山是六縱司令員,而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銀分別任十六、十七、十八旅旅長。如果說他們三位是猛虎,那王近山就是一頭雄師。王近山打仗勇猛,被稱為“王瘋子”。俗話說得好:強將手下無弱兵。在王近山的指揮下,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銀可謂身經百戰,九死一生。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二十七軍軍長的尤太忠,和他的部隊一道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一場災難,這股內亂風也不可避免地刮到了無錫。造反派揪來了尤太忠,要斗爭他。在批斗現場,將軍頭不低,腰不彎,巍然挺立,一臉殺氣,橫眉怒對。結果,造反派只能揮拳喊口號,竟無一人敢接近他。
尤太忠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凡是認準了的事就要堅持到底。他和他的上司許世友一樣,對紅衛兵在社會上搞“打砸搶”十分看不慣,對造反派沖擊部隊更是深惡痛絕。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維護無錫地區的安定作出了貢獻。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接到尤太忠的一個電話:“老肖,你到我們這里玩玩吧,我們這里蠻不錯的喲!”
二十七軍駐軍太湖邊上的無錫,江南小城,魚米之鄉,當然不錯。但是,在當時中國政局的“非常時期”,一位軍長決不會有閑情逸致邀請一位裝甲兵司令員去“玩玩”的。同樣,一個裝甲兵司令員也不會有閑情逸致去游山逛水的。
前十八旅旅長非常熟悉他的老戰友。電話里沒說什么,但兩人彼此意會。寒暄幾句后,肖永銀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尤太忠的“盛情邀請”。他知道,為了防止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被造反派揪斗,尤太忠把許世友接到無錫保護起來了。
提到許世友,兩人是再熟悉不過了。許世友罵娘,閻羅判官也要怕幾分。可是,在當時那特殊時期,“小鬼”卻把“閻王”欺負了。有一次,許世友到北京開會,下榻于京西賓館。造反派沖開部隊組成的人墻要沖進屋內。許世友抓起電話,對林副統帥辦公室吼道:“造反派要抓我,請保護我的安全!如果不行,我就要犯法,開槍打人!犯國法,國法制裁!犯軍法,軍法制裁!”說罷,拿起手槍,殺氣騰騰。
林彪也知道許世友言必行,行必果,說犯法就敢犯法,于是立即命令衛戍部隊前去解圍。
“京西之險”后,許世友又有“南京之危”。紅衛兵小將屢次沖擊許世友的家,警衛部隊奉命行事,“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無力保護許世友的安全。肖永銀深恐許世友一怒之下果真“犯法”,死說活說硬把他送上了飛機,讓尤太忠“監護”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接觸。
現在,許世友正在無錫“避難”,尤太忠打電話叫他去玩,肯定是許世友有事找他。
果然,一到無錫,許世友劈頭就說:“陶勇的孩子到處流浪呀,怎么辦?你們是不是把他們收起來呀?”
尤太忠和肖永銀兩人會意地相互看了一眼。
原來,海軍中將陶勇在“文革”期間受到沖擊,已經命喪黃泉。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難逃。李作鵬等人以各種罪名把她關押起來,致使她最后跳樓自殺。陶宅被查封,東海艦隊司令員的兒女們被逐出家門,流浪露宿于上海街頭……
陶勇的孩子流浪街頭,深深刺痛了許世友的心。本來,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安排收留幾個孩子又算得了什么?但當時許世友已自身難保,更何況上海雖是南京軍區轄區,卻在張春橋、王洪文的嚴密控制下;陶勇雖死,卻“罪惡滔天”,誰敢收留“罪臣之后”,誰就是引火燒身。許世友想告慰九泉之下的陶勇,又怕肖永銀和尤太忠為難,話沒有說,婉轉暗示。
肖永銀和尤太忠像當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樣,嚴肅認真地商量起來。兩人最后決定,由尤太忠負責找到孩子后,再秘密送到南京肖永銀處保護起來。
后來,當尤太忠把陶勇的孩子從上海找到,交給手下人帶走時,他久久地唏噓長嘆……
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為了加強北方中蘇邊界的軍事力量,二十七軍從蘇南的魚米之鄉被調到荒涼的內蒙古北部戍邊。尤太忠也隨部隊來到了內蒙古。這之后,他曾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內蒙古軍區司令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等要職。
一天,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尤太忠到包頭監獄視察,看見被打成“走資派”的老干部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幾人竟在豆油燈下捉虱子。
看到這種場面,尤太忠心頭不禁一顫。他當即召集包頭市領導,命令道:“你們把他們放出來,搞點水讓他們洗一洗,把衣服用水燙一燙。”
市領導有些為難,小聲問道:“他們是走資派,放出去好不好?”
尤太忠瞪起了眼,斬釘截鐵地說:“放!有什么問題,我負一切責任。”
像這樣的事還很多。與尤太忠一起戰斗過的史景班將軍“文革”中受沖擊,3個女兒下放內蒙古勞動。尤太忠聽說后,驅車上百里專程去看望史將軍之女,并想法將他們調回南京。
尤太忠的侄女尤嶺珠曾回憶道:1959年冬,尤太忠驚聞老母親病重,急忙返回河南光山縣磚橋鄉的老家。一到家,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幅悲慘的景象:老母臥床不起,一家人以糠為食。哥哥尤太俊正準備攜全家外出要飯。將軍見此,心情極為悲痛。再看看四周,鄰里家家如此。他萬沒想到革命勝利已經10年,家鄉的父老還這么貧困。為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他每家送去5元錢,200元全部發完。返回時,縣領導找幾個人想陪將軍吃飯。尤太忠大怒,拂袖而去。
1974年初,鄧小平復出后由江西回到北京。尤太忠聞訊,當日即隨蘇振華、李達兩將軍冒險前往探視。尤太忠見到鄧小平,立正、敬禮,還像戰爭年代一樣。鄧小平笑著問:“你怎么敢來?”尤太忠回答:“您永遠是我的老政委。”鄧小平招呼大家坐下,開始了親切的談話,就像回到戰爭年代一樣,大家無拘無束。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像尤太忠那樣講義氣、重友情,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有高尚的人格。
尤太忠記憶力驚人。他說:“這是沒有文化逼的。人用筆記,我用心記。打仗是要死人的,豈敢馬虎?”
尤太忠身材魁梧,鼻大嘴闊,雙耳奇大,雙目炯炯,眉宇間兩道豎紋,殺氣逼人,酷似京劇里的武生。
其實,在平時不打仗的時候,尤太忠很平易近人,從干部到戰士,人人皆可近,事事皆可辦。
尤太忠的個性很特別。當尤太忠在戰場上運籌帷幄之際,常常以三指捏住額頭,此時,無人敢接近去打擾他。若他舉手壓住帽沿,就表示決心已下;若脫帽而起,說明他必定會赴前沿指揮,無人能阻擋;假如他以指摸腮,臉露笑容,那么此仗勝局已定。
解放戰爭初期打榆林,首次攻城失利。六縱政委杜義德打電話問尤太忠:“老尤啊,你不是很能打嗎?怎么搞的,打了半天沒有打下來?”尤太忠漲紅了臉,放下電話,脫帽而起,直奔前沿。眾將士見旅長親臨前線,群情激憤,奮勇向前。城防被攻破后,尤太忠隨部隊一起殺進城,結果右腿被碉堡內殘敵的冷槍擊穿。在解放戰爭中,旅級干部負傷,還不多見。
尤太忠記憶力驚人。十二軍徐克杰副軍長曾回憶說:尤太忠將軍耳所聞輒終記不忘。戰爭年代,將軍有一次到縱隊接受戰斗任務,回來后指著地圖傳達,全旅3個團,出發時間,途經地點,過某山某河,何時到達何地,東西南北,分分秒秒……傳達完畢,縱隊文字命令才到,各團領導對照命令,竟無一差錯。尤太忠說:“這是沒有文化逼的。人用筆記,我用心記。打仗是要死人的,豈敢馬虎?”
抗美援朝期間,有一天,尤太忠的夫人王雪晨站在朝鮮地圖前考丈夫。王雪晨要他離開地圖,站在辨不清文字的地方,指著地圖的某處問丈夫:“這是什么地方?”尤太忠毫不猶豫地回答了她。連指十余處地名,都應答如流,無一差錯。接著王雪晨又指向偏遠地點,仍然如此。王雪晨至今仍驚異丈夫的記憶力:“朝鮮地名生僻難認,他當時文化不高,為什么指哪認哪,一字不差?”其實,尤太忠是笨鳥先飛,早已將地圖上上千個地名爛熟于心。
尤太忠精人的記憶力還表現在學習上。
1957年,尤太忠進軍事學院學習,課余從不復習,然各科均在良好以上。看到別人手忙腳亂,窮于應付,他自豪地說:“我看人家忙得很,還考不好。我是保證3分,爭取4分,不要5分。”
結業時,果然各科都在3分、4分之間,無一科5分,也無一科不及格。
尤太忠有一個特殊的習慣,這就是下部隊喜歡數豬。每到一個連隊,不問人多少,只問豬多少。連隊干部若答錯,必遭嚴厲批評。若答少一頭,將軍必會批評:弄虛作假。后來,尤太忠下部隊前,秘書都悄悄與部隊領導通氣:“人多少,沒關系。一定要把豬數清,少一頭不行,多一頭也不行。”
后來才知道,當時我國正處在困難時期,部隊要改善伙食只有靠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在那時,部隊養豬成了一項“戰略任務”。在這位貧苦農民出身的將軍看來,能讓戰士們吃上肉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他的職責。戰爭時期沒有條件不可能養豬,現在有條件了,為什么不把這件事抓起來、抓好呢?
尤太忠13歲參加紅軍,15歲入團,16歲入黨。在長征途中,他連病帶餓,幾乎把命扔在了茫茫草原上。
那是1935年的一天,詹才芳將軍見幾個士兵抬著一個重病號,欲棄之在草地上,急忙下馬詢問怎么回事。戰士答道:“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細觀察了一下,沉思片刻說:“不要扔,這么年輕,個子又大,扛機槍是把好手。你們給他一個馬尾巴試試。”
這個重病號就是尤太忠。
享受拉馬尾巴待遇后,尤太忠靠著自己堅強的毅力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隨大部隊走出了草地。后來,尤太忠將軍常常念叨詹才芳的救命之恩,常常說:“我這條命是拉馬尾巴拉出來的。”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強渡汝河,戰況慘烈。尤太忠將軍后來回憶說:“那天,困難得很啊!犧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1942年9月初的一天,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來到山西省中條山區陽城縣卵寨村,向尤太忠所在的三八六旅十七團全體官兵傳達延安整風精神。
第二天拂曉,四周響起了陣陣槍炮聲,村子已被日偽軍圍得嚴嚴實實。團長尤太忠手提駁殼槍,沖向鄧小平的住房,看見鄧小平手握“小八槍”(一種連發八顆子彈的小手槍)正與馬夫一道疾步走來。
“鄧政委,請跟我來,我先把你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尤太忠著急地說。
“團長同志,你的任務是指揮部隊把敵人打垮,而不是保護我個人的安全!”鄧小平臨危不懼。
這時,尤太忠見民運干事鄭炳全過來了,懸著的心才放下來。他大聲命令道:“快!趕快保護鄧政委轉移!”說著,頭也不回地帶領部隊與敵人激戰。
一發炮彈在鄧小平身后不遠處爆炸了,驚得戰馬發出長長的嘶鳴,引來敵人一串槍聲。護衛在鄧小平身邊的馬夫中彈犧牲了。鄭炳全一把拉住韁繩,焦急地說:“鄧政委,這兒太危險,請趕快上馬,我保護你突圍!”鄧小平笑道:“是個小老鄉呀。先別急,把敵情弄清楚再說!”
突然,敵人的槍炮聲停止了,看來尤太忠率領官兵已與敵人短兵相接了。
鄧小平隱蔽在一棵大樹下,冷靜地觀察著四周的戰況。幾分鐘之后,村子東面槍聲大作,炮聲驟起,爆炸聲、喊殺聲響成一片。緊接著又響起了八路軍嘹亮的沖鋒號聲,敵人的包圍圈被突破了。鄧小平這時才上馬向安全的地方轉移。
這次驚險的遭遇戰,特別是鄧小平臨危不懼的大將風度,給尤太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8月,劉鄧大軍開始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的作戰行動。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時而騎馬,時而步行。兩個參謀和幾個警衛員緊緊跟隨,不離左右。他們一口氣走了十多華里,來到離汝河北岸不遠的六縱指揮所時,夜幕已經降臨了。
研究部署完畢,已是夜里12時。劉鄧首長接著給各旅布置了作戰任務:十八旅旅長肖永銀帶領他的旅先攻下河對岸大、小雷崗,從敵群中殺出一條通路,帶領部隊沖出重圍;十六旅旅長尤太忠帶領本旅部隊上來接防,固守大、小雷崗及橋頭堡,抗擊敵人,掩護大軍安全渡河。
第二天,按照劉鄧首長的部署,十六旅主力接替完成任務的十八旅扼守大、小雷崗保護浮橋。等待十六旅旅長尤太忠的,是一場慘烈無比的惡戰。
次日凌晨3時左右,尤太忠把部隊帶了上來,但只有兩個團加上一個旅直,全旅兵力不到7個營。而正前面的敵人,則是1個軍。尤太忠頓感肩上責任的重大:此戰所掩護的是向南進軍的統帥部,最敬愛的劉鄧首長就在大家身邊;戰斗的成敗,關系著意義重大的戰略進攻和下一步的行動。
大、小雷崗離浮橋的橋頭約三四里地,像兩支觸角伸在外面護衛著橋頭。大雷崗在右前方,部隊南進時就從它旁邊插過。小雷崗在左前方河堤旁邊,離敵人主力所在的汝南埠很近。
根據地形判斷,敵人會先取小雷崗,因為這個村子緊挨河堤,離橋頭很近,敵人要打下小雷崗,我軍就會失去依托,很難守住橋頭。尤太忠在河堤上安置了側射火力,以備敵人進攻村子時從側背打它,并命小雷崗的部隊加速儲蓄彈藥,搶修工事。
大戰臨近,尤太忠濃眉緊鎖,渾身上下骨骼碩大,臉上有角有棱。他思考問題非常投入,在遇到嚴峻險情時,眉宇間就會形成一條很深的豎刀紋。這使他那張棱角分明的臉更加有力度,甚至有幾分兇狠。
清晨5點多鐘,劉伯承、鄧小平出現在旅指揮所。尤太忠一愣,跑出馬廄,語調里充滿了不安與焦慮:“首長,這里距敵僅一兩里地,是激戰中心,你們怎么……”
劉伯承四下觀察,問:“進小雷崗的是哪個團?”
“四十八團。首長,進掩體吧!”
“小雷崗無論如何要守住!”
“是!我已經做了布置。”
鄧小平問:“政委呢?”
“我倆分開指揮,犧牲一個,還有一個頂著。首長還是進掩體吧。”
一發炮彈呼嘯而至,“轟”地一聲,一面墻倒了,氣浪沖飛了尤太忠的帽子。尤太忠一揮手,大叫:“扶首長進指揮所!”
在馬廄里,尤太忠還是心神不定,說:“首長,你們快離開這里吧!”
劉伯承說:“敵我力量懸殊,你們擔子很重。一定要堅持到晚上,等所有部隊通過。”
“是!”尤太忠一臉肅穆。
鄧小平補充說:“部隊全部過后,把浮橋拆掉。”
“是!首長,這里不安全。”
鄧小平笑笑:“噢,不歡迎我們在這里?”
劉伯承接著說:“還有什么要求嗎?”
尤太忠極度不安,還是回答說:“是!”
鄧小平緩和氣氛說:“司令員問你有什么要求。”
尤太忠醒悟過來,想了想:“請給我們留下十八旅的一個后備營。”
“可以。鄧政委,我們……還是走吧。”
劉伯承走出馬廄,又回過頭:“尤太忠,會合地點記住了嗎?彭店!”
尤太忠深感責任重大,堅決地回答:“請首長放心,我們一定和敵人決一死戰!即使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也決不準敵人一兵一卒擾亂大軍南下的行列!”
6時許,敵人開始轟擊小雷崗。陣地上掀起幾丈高的塵土,沙石迸飛,一片迷蒙,連前沿陣地也看不清了。炮火的激烈使聯絡不時中斷,但這并未影響戰斗。連長犧牲了,戰士就頂上去,最后打到一個班只剩下兩三個人,小雷崗還牢牢地掌握在十六旅手中。
敵人完全沒想到十六旅會這么頑強,瘋狂氣焰完全被壓了下去。敵人攻不下小雷崗,10時又轉向大雷崗。所有的火力轉過來,10多架飛機助戰,把陣地打得昏天黑地,10米之外看不見人。有六七發炮彈就落在馬廄四周,門板都被掀掉了。尤太忠命大,安然無恙。他抖抖落在身上的灰土,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狗娘養的,沒膽量炸老子嘛!”
當前面部隊和敵人激戰的時候,南下大軍正以4路縱隊通過浮橋,從十六旅旁邊前進。
到下午4時,劉鄧四五萬大軍,200多輛大車,全部安全渡過了汝河。
多年后,將軍回憶起那場戰斗,仍傷感地說:“那天,困難得很啊!犧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汝河之戰,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途中最緊要、最激烈的一場戰斗,它不僅關系到縱隊的安危,更重要的是關系到中原局和野戰軍首長、統帥機關和南下部隊的安危。
尤太忠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劉鄧首長的高度評價。
1972年,尤太忠得了一場重病,夫人王雪晨送他到北京治療。剛下飛機,便見一輛由吉普車改裝的救護車飛奔而來。當醫護人員把尤太忠抬上車后,一路綠燈,直奔醫院。該“救護車”為當時中央領導人使用。這樣高的接待規格,令王雪晨心中既激動又忐忑不安。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周恩來精心安排的。這件事使尤太忠深受感動,記了一輩子。
還有一件事令尤太忠終身難忘。“文革”中的一天,周恩來在中南海找尤太忠談話,并設便宴招待。那天,尤太忠喝了三杯茅臺酒。返回部隊后不到三天,便接到中央接待辦的一封信函,上寫:某月某日,尤太忠同志喝茅臺酒三杯,需付酒費0.6元。尤太忠看后大吃一驚,急忙寄去酒費,并深感愧疚。在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時,每次赴邊防視察,每到一地,他都命令警衛人員按標準吃飯,離開時囑咐警衛人員按標準交費。所到之處,從沒有欠一分錢伙食費。
粉碎“四人幫”后,尤太忠被委以重任,先后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后來又調任中央軍委紀委第二書記。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98年,尤太忠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歷程,永遠地離開了自己親愛的人和所熱愛的部隊。8月3日,他的遺體在廣州火化后,骨灰按他的遺愿撒入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