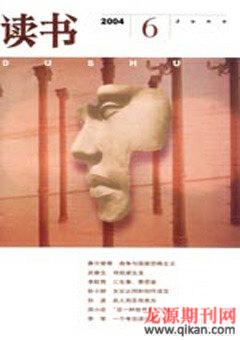編輯手記
先是關塔那摩,而后是阿布格萊布,非法關押和虐待戰俘一再成為全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一位朋友不解地問:為什么有些媒體對虐俘事件大加報道,卻對導致大規模平民傷亡的戰爭本身持支持態度?關于虐俘事件的起因,各方說法不一,但這一事件已經將“反恐”行動與恐怖本身聯系在一起,在美國和英國國內進一步瓦解著“反恐戰爭”的基礎。在新近公布的幾幅新發現的虐俘照片中,讓我最為震驚的不是那些正在施虐的畫面,而是那個在被折磨致死的伊拉克俘虜旁邊燦爛微笑的美軍女兵的照片。如果把那個歡樂的微笑與傷痕斑斑的尸體從照片上的狹小空間中分割開來,你不可能找到它們之間的任何聯系。這一殘忍的關聯足以讓人感到極深的黑暗——恐怖和死亡可以如此輕易地轉化為歡樂和滿足!這就是所謂人性的殘忍嗎?我毋寧視之為國家恐怖主義的產物,因為在當今的世界里,惟有國家恐怖主義可以用“反恐”或“人道主義干預”等高尚的言辭將暴力和殘忍正當化——這也正如當年在侵略戰爭中為帝國政府效忠的士兵從殺人中感到幸福和榮耀一般。
其實,從其他社會的眼光來看,虐俘行動雖然令人震驚,但并不比用巨型炸彈對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狂轟濫炸更為嚴重,它們不過是一連串事件中的一個事件。本期有關國家恐怖主義的討論提出的就是國家、戰爭與恐怖主義的關系。賽爾登教授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和《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等書的作者,一位資深的中國學家。過去許多年,他一直在研究東亞的戰爭及相關問題。就《讀書》而言,這次討論也是早先的“戰爭與革命”的專題及去年十二期刊載的小森陽一有關日本天皇制的研究的繼續。在“九一一”之后,媒體和社會將關注的中心從以往的國家戰爭,轉向了新的全球現象,即恐怖主義。然而,賽爾登教授提醒我們:在整個二十世紀,恐怖主義的主導形式是國家恐怖主義,它導致了上億人的死亡,這還沒有算上那些目標對內的國家恐怖主義所造成的種族清洗、政治迫害等。在二十一世紀的所謂“反恐”戰爭中,戰爭的主導方面仍然發生在國家之間: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大量的平民和并未參與侵略戰爭的軍事人員死于轟炸和有組織的迫害及謀殺。從二次大戰后的東京審判,到今天有關南斯拉夫戰犯的審判,每一次審判都是勝利者在國際法名義下對失敗者的審判。若以殺傷平民為準則,那么東京審判并未觸及美國在廣島和長崎的核打擊。霸權的邏輯能夠審判霸權嗎?美國的準則能夠審判美國嗎?究竟怎樣的規則和法律能夠實現“普遍的正義”,而不只是“勝利者的正義”?
正是從這樣的追問出發,賽爾登教授也試圖指出中國學者和讀者經常忽略的問題,即在中國公眾譴責日本的侵略罪行的時候,對于美國主導的戰后法律審判體系缺乏深入的討論,從而也很少涉及美國及其盟國在對日、德作戰中對平民進行的轟炸。正如在討論中人們思考的:一種公正的國際法和戰爭法是可能的嗎?消除導致戰爭的動力是可能的嗎?
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思考和探討。但沒有疑問的是:在“反恐”戰爭成為世界的主要話題和強權的實際行動之時,重新提出國家恐怖主義這一問題,有著特別的尖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