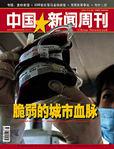《孔雀》:一種渴望純真的姿態
宋 罡
《孔雀》講述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歷史,它把那段特殊歲月的故事娓娓道來之后,似乎為第五代導演關于文革記憶的講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句點。
從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開始,中國過于豐富的近現代歷史對于個體命運的糾纏就成了一種通用的敘事模式,無論是《藍風箏》、《活著》,還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都力圖在個人化的文革記憶中取得歷史與藝術之間的平衡。《陽》淡化了前幾部影片中具有強烈傷害性的社會外力背景,而《孔雀》此番所努力營造的正是與其一脈相承的“淡淡的哀愁”;稍有迥異的是,《陽》的“大院子弟”可以在青春之后擁有繼續無限風光的條件,《孔雀》的主人公卻只能面對窘迫無奈的日常生活。
這類題材的影片,涵蓋了中國社會轉型以來20余年間主要的分歧所在:一邊是既得利益者為自己的過往不遺余力地涂抹裝飾,一邊是為衣食奔波的普通人無暇他顧選擇沉默。他們的歷史記憶就是不斷緬懷那段以青春命名的日子,而維系二者的惟一共同點就是一個已經曖昧不堪的詞匯——理想主義。
在《孔雀》中,沉浸在精致的畫面之中的人物同樣沉浸在精致有趣的細節之中,甚至可以說它堆砌細節到了泛濫的程度,煽情到了刻意的程度,而這些細節又是如此的擁有質感,這些煽情又是如此的令人感動。
顧長衛的才華在于他表現出了這樣一種精神立場——一種力圖誠實地表現真實生活的立場,而眾多中國電影的狹隘之處,恰恰是無數普通人的真實生活,被遺落在它們的視野之外。
沒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歷史是殘缺的歷史,而顧長衛所做的努力,就是來填補那殘缺的部分。但是他唯美主義的基本態度卻導致了這種立場的某種保留,這使得這部影片在表現中國人的日常經驗和日常生活以外,對于生活中該被諷刺的部分予以了回避。作為一位被稱為唯美主義的電影人的顧長衛,在自己的導演處女作中,還是不能免俗地祭起了青春回憶的大旗,而中年人對青春的戀戀不舍,總有一絲自戀的味道。
哲學家懷特海曾給青春下過一個定義:“青春就是尚未遇到悲傷的生命。”《孔雀》中的三個孩子,他們的青春結束在每一個人都試圖逾越自己獲得別種生活,結果卻永無出路的時刻,這也是他們令人無限感傷與引起共鳴的所在。雖然有人不喜歡,但也許我們還是要感謝《孔雀》那雀屏綻放的結尾,正如周國平所言:“對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價值,那種在實際生活中即使一敗涂地還始終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運兒。”
這是一種渴望純真的姿態,雖然終于在保有純真而不得之后被迫承認了世俗與無奈,但是人們還是在幻想中期待遇到美麗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