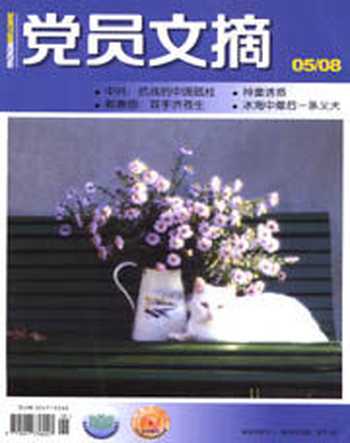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紀事
蔡 偉 李 華

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的生存陷入空前危機。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的最初反應是“不抵抗”,并要人民保持“鎮靜”,對抗日運動進行壓制。并且,蔣介石提出一個口號:“攘外必先安內。”
1932年1月下旬,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日,并不惜屈辱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執行的正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羽英二發表談話,表示“日本是中國的保護國”,日本要排擠英美等國的在華勢力,實行獨占中國。7月,蔣介石發表題為《抵御外辱與復興民族》的長篇講話,強調:“以現在的情形來看,他(日本)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占領下來,滅亡我中國”;“所以現在這時候,說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真是癡人說夢!”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仍不放棄妥協的主張,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地對日退讓的同時,國民政府卻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及其革命根據地的不斷“圍剿”。
共產黨提出“抗日救國”
但是,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后,卻未能給國民政府所謂“安內”的機會。在蔣介石致力于“圍剿”紅軍的同時,日軍不斷向南向西擴張。
就在紅軍長征之時,日本通過發動“華北事變”,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有人這樣描述1935年底的時局:“愛國有罪,冤獄遍于中國;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聯合盡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緊迫的任務。
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個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也被發表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對中國國內的抗日聯合戰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響。“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經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八一宣言”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愿意以“抗日救國”為準則,同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同胞聯合抗日,“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愿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
1935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不久,中共中央又于11月13日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明確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936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和反帝統一戰線。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張浩(林育英)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后,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與中國情況相結合,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在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并全中國的局勢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大禍,“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此時,面對日本在華北咄咄逼人的壓迫,蔣介石對日態度也開始有所強硬。在1936年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表示:“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后的犧牲。”
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等愛國人士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表示:“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停止攻襲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毛澤東于8月10日為此專門回信章乃器等愛國人士,感謝他們“善意的批評和希望”。
這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從“抗日反蔣”,開始逐步轉變為“逼蔣抗日”。為此共產黨對國民黨作出了一系列主動的姿態:
8月14日,毛澤東寫信給宋子文,指出“當今寇深禍亟”,“救亡圖存,惟有復歸于聯合戰線”,“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內對外方針”。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書》,堅決要求國民黨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轉向日本侵略者,再次申明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決議》,指出,為了“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助推統一戰線
但是,蔣介石一直放不下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1936年5月26日,國民黨政府任命陳誠為晉陜綏寧邊區剿共總指揮,并將重兵調往潼關、洛陽等地,逼迫東北軍、西北軍加緊向陜北根據地進攻。
然而在中共的努力下,紅軍與受蔣之命進攻紅軍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部隊達成一致,從戰爭狀態轉變為“三位一體”的團結,形成了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面。1936年10月15日,中共單方面發布了停戰命令,停止對國民黨軍隊進攻,宣布僅在被攻擊時實行必要的自衛。但是,蔣介石卻于12月4日親率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飛赴西安布置“剿共”,頒發對紅軍的總攻擊令,并對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若違抗“剿共”命令,將解除其武裝。
在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對外抗戰無效的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對蔣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及其高級隨員十幾人。“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并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等人赴西安談判,最終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回南京宣布抗戰。
“七七事變”催生統一戰線
為了盡快實現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在“西安事變”后國內和平的新形勢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電正在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5項要求。國民黨此次中央全會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議。
為解決兩黨如何具體實現合作和共同抗戰,從1937年2月到7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先后進行多次談判。但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仍在進攻南方紅軍游擊隊,并在蘇州審判“七君子”。國共兩黨在實現合作和共同抗戰的主要問題上,直到1937年7月初,仍未達成協議。
然而,1937年的兩場戰爭,終于對行將破繭、卻步履蹣跚的國共合作之路,起到了“催生”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華北軍隊在盧溝橋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8月13日,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上海,國民政府被迫在次日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1937年8月中旬,中共代表同國民政府代表在南京舉行第5次談判。國民政府終于同意,將在陜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8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中共的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終于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多年民族危機和矛盾的累壓后,在最后關頭終于得以實現。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 原標題為《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從民族危機到國共合作》 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