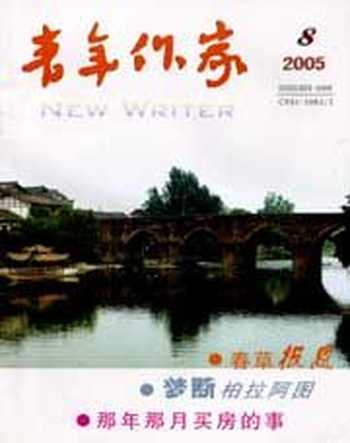特殊的戰(zhàn)士
孫艷婷
又是一個知了聲聲的夏季。今年比較炎熱,很熱的那幾天,就是夜里也難以入眠。在那樣一個輾轉反側的夜晚,我實在睡不著,沖到陽臺上納涼,隨手撥通了友人的電話。他也熱得沒法入睡,或許,這是老天為了紀念60年前那些死難的亡魂吧……這一句話透過電波從遠方傳來,我一個激靈,似被電流擊中了一般。抬眼仰望,一輪圓月掛在空中,明天又將是一個晴天吧。回想60多年前,晴日的成都,正是敵人轟炸的焦點……
“1943年的5月,那時我們在北方……八路軍裝備都比較差……日本人的裝備比我們的好多啦!還時常有飛機來轟炸……那天,聽見飛機飛來的聲響,隱蔽了半天卻沒有反應,大膽向上一看,青天白日滿地紅,是我們的飛機!當時那高興勁啊,甭提了……”現(xiàn)今81歲高齡的秦登魁老先生,祖籍山西,17歲就當上了紅小鬼。抗戰(zhàn)的時候被編在八路軍第18集團軍129師。他身體健康,耳聰目明,十分配合我的采訪。他用低沉而慈祥的聲音將那些被歷史塵封的往事娓娓道來:
你問我對日本鬼子的印象?丫頭,那些小日本可兇狠吶!但我認識一個叫岡村的,他和別的鬼子很不一樣……
1944年,秦登魁所在的隊伍在山西翼城縣牢寨村與一小隊日本人(大約40多人)開火,獲得小勝,俘虜一名日本傷兵。盡管沒了武器,這個日本傷兵仍十分兇狠,像一只受傷的野獸,對所有靠近他的人惡狠狠地咆哮。衛(wèi)生隊抬來了擔架,他死活不肯上去,幾個衛(wèi)生員都快被他磨得失去了耐心,最后只好將他綁在擔架上抬回村子。
這是小鄉(xiāng)村里第一次見著沒了武器,失了威風的日本兵。進了村口,就有許多人對著那副擔架行著注目禮。走到一半,突然一聲慘叫,驚了所有看熱鬧的人。一位年過七旬的老太太沖上前去對擔架上的俘虜又打又嚷。近距離地,日本俘虜看清了老人眼中的仇恨。或許是前幾天糧食被洗劫一空的人家吧;又或許,這就是某個被奸污的少女的奶奶。對于俘虜的下場,他的心里是有準備的,但還是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落在日軍手中的俘虜,不僅是死,而且死得很慘……閉上眼睛,日本俘虜想起遙遠的祖國,自己恐怕再也沒機會重回故里了。
在衛(wèi)生所等待死亡的俘虜,等來的卻是兩個醫(yī)生和一碗熱騰騰的煮雞蛋。3天后,日本俘虜躺不住了,要求見長官。一名衣著樸素整潔的翻譯同他進行了交談。一個月后,這名傷勢痊愈的日本俘虜哭著不肯離開八路軍部隊,從此,這個隊伍里就多了一名叫岡村的日本戰(zhàn)士!
這名特殊的戰(zhàn)士,擔任起了特殊的任務——在開戰(zhàn)以前,向日本據點喊話,爭取一些還有良知的日本人放下武器站到正義的一方來……后來,這名特殊的戰(zhàn)士還到過延安,參加了反戰(zhàn)同盟,回到日本后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成為了一名中央委員……于是岡村在人們眼里似乎就成了一個特例,但事實上,像這樣的“鬼子”在抗期間也不是只有岡村一人。
“這些小日本,眼睛瞪得跟小兔兒似的,拼刺刀啊——兇狠著吶!可是我命大啊……”83歲的宋桃小老人是河北人,說起話來很有精神,就是耳朵有點兒不好使。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是命大,死不了。
1943年,宋桃小所在的部隊在山西壽陽伏擊一隊敵人。他們事先隱蔽在一塊茂密的莊稼地里。待敵人走近時,立馬扔手榴神,敵人驚魂未定,他們一鼓作氣,沖上前和鬼子面對面拼殺起來。日本士兵訓練嚴格,雖然個子不高,刺刀卻拼得很兇。宋桃小那時年輕氣盛,身材高大,有1米80,比鬼子整整高出了一個頭!但日本人一點也不害怕,一個向前直向宋桃小心臟刺去!宋桃小忙使出防左刺進行防守,但慢了一點兒,雖沒傷到性命但左上手臂內側卻被刺中。一刀刺中,鬼子來不及收回,趁著這個當兒,宋桃小一個狠刺將小日本刺死……回部隊里,他才發(fā)現(xiàn)血已經把褲子給染紅了!直到現(xiàn)在還能清楚地看出他左上手臂的傷痕。宋老先生忿忿地說:“這小日本兒,到現(xiàn)在還不肯認罪!我這身上的傷痕還是證據啦!”“不要看小日本的刺刀玩得好,我的刺刀也拼得不差呀!”講著講著,他禁不住用手中的拐杖給我做起了演示:向前刺(刺胸)、向下刺(刺小腹)、防左刺(防守)、防右刺(防守)……有模有樣,一點兒也不含糊。末了,他笑著說,“我這刺刀就是跟一個日本人學的!”
據了解,當時確實有不少日俘被感化轉而幫助中國人。有的做刺刀教練,有的培養(yǎng)飛行員等。這些特殊的戰(zhàn)士,也為中華民族的抗戰(zhàn)做出了貢獻。在那戰(zhàn)爭年月,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能站在正義的一邊,用他們的實際行動來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贖罪。而60年后的今天,日本極右勢力仍不能正視軍國主義的罪孽,并為其招魂。
采訪結束,我感到很欣慰,那些特殊戰(zhàn)士的存在,正是良知并未完全泯滅的象征。我們有理由相信,不管怎樣掩飾,歷史終究是歷史,不會被歲月的流沙掩埋,也不可能被真正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