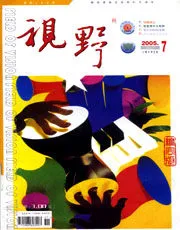肥皂劇中的悲觀主義者
劉天昭
崔永元說他有抑郁癥,然后就有人出來表示驚訝。其實我懷疑是不是真的有人覺得吃驚,因為我一直就覺得崔老師很抑郁。前些年看那本《不過如此》,聽著名字就覺得悲觀,里面別的都不記得了,就記得他說他去韓國,在那兒看著藍天,想到他女兒,淚如雨下。看完那書就覺得,這個在電視里笑嘻嘻表演著的人、娛樂大眾的人,背后的悲觀是他感受自我真實性的一個方法吧。
一個德國心理學家說:“如果世界上沒有誠實的悲觀主義者,沒有感傷主義者,沒有遭受現實困擾而追求變革的人,那我們的社會就變成了一出肥皂劇。”這幾乎是要把悲觀說成一個好東西了,而且那意思里也包含著:悲觀、感傷和焦慮的情緒,是讓泡沫凝成現實的那粒塵埃、那個小核。可以從個人經驗中明白證實的事情是,快樂的感受讓我們忘我,而痛苦的感受卻能喚醒我們強烈的存在意識。即使不去追求,一定量的痛苦于我們的生活,也還是必然的、必要的吧?
我不大知道肥皂劇的界定到底是怎樣的,從名字上看似乎是那些肥皂公司贊助播出的電視劇的意思。那樣的話,這劇種對內容和風格也沒有什么明白的規定,只要是收視率高的電視劇,就都可以幫著賣肥皂吧。這樣說起來,肥皂劇和悲觀主義者和痛苦者,也實在是沒啥本質的必然的矛盾。實際上,雖然未必全都悲得英雄,但是肥皂劇里的悲觀主義者還是挺多的。除了那些小品式的情景喜劇和鬧劇,仔細想一想,一定量的悲觀,一個至少是憂郁的角色,對于一部電視劇來說,簡直是必不可少的。
我看的第一部日劇是《沙灘小子》,到現在我都覺得那電視劇憂郁極了,寂寞極了。尤其是竹野內豐演的海都,有一點避世,話少,神情感傷,讓你覺得他總是在感覺自己心里正在流淌正在消逝的——也許是夏天吧。大概竹野內豐的那路長相就很適合演些郁郁寡歡的人吧,后來看過他演的《網絡愛情》,開頭就是:“我叫長谷川天,二十七歲,身心俱疲。”
好多被認為經典的日劇里,都有那種劇情之外的、作為人物性格的虛無感和焦灼感。好像《長假》、《東京愛情故事》、《愛情白皮書》、《美麗人生》,那愛情都有淡卻不散的哀愁在里面。那哀愁仔細想來竟是無緣無故的,再仔細想想,就覺得那里面的主人公,他對世界的一個基本態度,就是感傷的。這大概也和民族性或者民族的美學有關系吧。這些電視劇都是全東亞暢銷流行的肥皂劇,它們的主人公們俊美但是憂郁的臉,用大特寫的方式讓人幾乎要相信,悲傷里包含著一種籠罩萬物的感染力,即便是肥皂劇,也逃不出它的咒語,也不能像肥皂泡一樣快樂輕松。
(程峰摘自《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