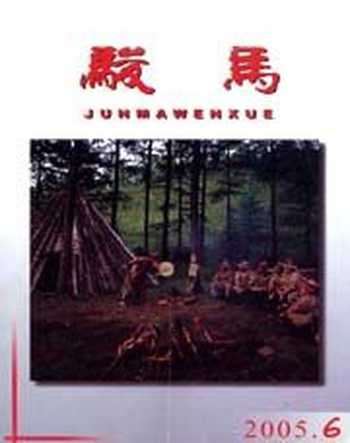冬獵
(鄂溫克族)古新軍
隆冬季節(jié),瑟熱和考力與老大叔瑪克辛木商定好了去克坡河一帶冬獵。他們在山下準備了很長時間,備足了狩獵用的小口徑子彈和在野外的生活用品,便乘坐上山運木材的汽車去了瑪克辛木的獵民點。
瑪克辛木大叔的老伴已去世多年,原來他的兩個兒子在一起看養(yǎng)四十五只馴鹿,生活平靜寂寞。前段時間,他的兩個兒子因在山上看放馴鹿太久而想山下,便已回鄉(xiāng)里的定居點了,而今僅剩老大叔一個人獨守著獵點,獨守著撮羅子(鄂溫克獵民的簡易住房),獨守著馴鹿,也獨守著忠誠的獵犬——努道。
瑟熱和考力的到來使瑪克辛木高興不已,滿臉的絡(luò)腮胡須伴著笑聲有節(jié)奏地顫抖著。瑪克辛木熱情地將他倆的行囊抱進撮羅子里,并將兩位年輕人讓進撮羅子靠近篝火的兩邊坐下。
“你們倆好好休息。大叔給你們煮上熱湯面條,吃完飯后早點歇息,養(yǎng)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啟程。”瑪克辛木一邊說著一邊開始忙著晚飯,吊在篝火上的黑鍋冒著熱氣。篝火熊熊地烤得兩個年輕人直向后仰。撮羅子里被篝火映得通明,濃濃的炊煙夾著點點火星躥出撮羅子頂端的煙孔。天色也漸漸暗淡下來。周圍的叢林沉浸在靜悄悄之中,只有幾聲輕脆的銅鈴振響回蕩在夜色中。
十一月的太陽還被寒霧籠罩著。瑪克辛木大叔早早地就把要馱東西的馴鹿拴好,將狩獵用的物品捆綁好,然后按著物品平衡重量逐個給馴鹿備上鞍子。瑟熱和考力不會給馴鹿備鞍子,也只能做到幫助瑪克辛木大叔找好了行李物品的重量平衡后,用肚帶使勁地把鞍子以及物品和鹿身捆綁在一起。馴鹿似乎感到被肚帶勒緊后的疼痛,掙扎了幾下很快就老實不動了。
瑪克辛木大叔用手拍著捆綁備完鞍子的馴鹿后背風趣地說:“走吧!走到哪兒也不會翻鞍子掉下來的。”
一切都安排得停當之后,瑪克辛木開始將馴鹿一個接一個地鏈上。瑪克辛木大叔把瑟熱和考力要牽的馴鹿給分好,并將馴鹿鏈上,分給他倆的馴鹿每人兩只,而大叔一個人就牽著鏈著的五只馴鹿。他們開始遠行了,剩下的三十多頭大小馴鹿也爭著急著地跟在隊伍的后面。
老大叔瑪克辛木上身穿著變得發(fā)灰色的犴皮夾克,頭上戴著獐子皮做的帽子,手上是大大的能伸出手的犴皮手套,腿上是犴腿皮做的套褲——阿拉木斯,腳穿一雙用犴皮做的靴子。半自動步槍帶搭在左肩上槍管朝前,獵刀挎在腰帶上,右手還握著一把砍刀在前頭領(lǐng)路和開道。雪沒膝深,馴鹿呼呼喘息冒著白氣,有的馴鹿嘴上結(jié)了冰溜子,當他們一隊人和馴鹿穿行在密林間,立時,樹上被震落下來的厚厚的雪片砸在他們的身上。
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路,瑪克辛木大叔停下來回頭向后看著瑟熱和考力是否跟上來,而瑟熱和考力這時正一前一后地踩著前邊走過的腳印,緊緊地追趕著大叔的身影。“怎么樣啊?累了吧?休息一下。”一邊說著一邊檢查馴鹿鞍子。瑟熱牽著馴鹿身體軟綿綿地倚靠在一棵大粗樹根下舒坦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氣,心里感覺特別的爽。
瑪克辛木大叔從懷里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來一個比火柴盒大的樺樹皮做的煙盒,打開之后朝盒里捻了捻又捏起送進唇里。老獵民都喜歡含煙,這種含煙方式如果是在夏季時對防火更安全,每當獵民疲勞的時候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含一下煙,這樣可以緩解身體的乏力。這不,老大叔含完煙之后精神立刻抖擻起來,又牽起馴鹿向瑟熱和考力吆喝著:“歇好啦,該上路啦!”
他們繼續(xù)向著目的地踏著深深的雪行進著,那些沒有任何羈絆的散鹿自由自在地忽前忽后地跟隨著大叔。考力和瑟熱、獵犬努道在隊伍后面像在保護著三個人和鹿群。
冬天的日光非常短暫,他們到了一個叫“敖饒道”的地方,在靠近一處冰凍的小河邊不遠處扎下了營。營地很簡單,不用搭建“撮羅子”,只是將從四周扛回來的粗木頭點燃起篝火,他們將圍著篝火度過一夜。
宿營前瑪克辛木大叔將馴鹿馱的行囊一個一個卸下來,又給馴鹿加上腿絆子后放開覓食,有個別不是很老實的馴鹿就給它拴上長長的繩子,這樣做是為了容易抓到馴鹿。
一天的路程使馴鹿也感覺到疲勞和饑餓了,一放開他們就奔跑著鉆進林子里。戴著脖鈴的馴鹿,時而近時而遠地發(fā)出清脆的聲音,“鈴……鈴……”,給寂靜的山林增添了幾分喧囂。
大叔的獵犬努道也早已找好了自己的位置,把頭和身子蜷縮到一起,眼睛卻在注視著忙碌的主人。
篝火旁,瑟熱正在忙著燒水做飯。考力打開準備露宿的行李并鋪展開,把犴皮褥子鋪在沒有清掃干凈的雪地上,鋪完了行李后考力順勢躺靠在行李上,望著天上稀落的星星。瑪克辛木大叔借助篝火的暗光,正扒著在途中打到的一只黑棒雞。毛已散落一地,白白的肉清晰可見。“今天的晚餐算是最豐盛的啦!”瑟熱邊煮著米飯邊說。瑪克辛木大叔走在最前邊時,這只棒雞在路邊突然從雪里鉆出飛上一棵落葉松粗樹杈上,當時還把大叔嚇了一跳,然后就是一聲清脆的槍響……
很快米飯已咕嘟咕嘟冒著熱氣,燉棒雞的黑鍋吊在熊熊的篝火中,散發(fā)著誘人的濃香。
瑟熱和考力這次上山?jīng)]敢?guī)敲炊嗑疲瑑H帶了兩瓶根河精制白酒,剛到獵民點時給了大叔一瓶,另一瓶擔心大叔喝多了耽誤出獵就藏了起來,瑟熱沒有吱聲,就連考力也不知道瑟熱還有一瓶酒藏到現(xiàn)在。“這回這一瓶白酒和一鍋棒雞肉真可謂是美酒佳肴啦!”考力抓起酒瓶子一邊說著一邊開啟著瓶蓋。考力找好了一個小鐵缸往里倒白酒,倒完酒后雙手端著敬送給瑪克辛木大叔。瑪克辛木大叔雙手小心翼翼地接過酒,然后用右手中指蘸蘸酒向著篝火中輕輕彈去,邊彈著嘴上邊叨咕著,瑟熱明白大叔的意思,這是在為我們這次出獵祈禱。瑟熱也接過大叔遞過來的酒,模仿著大叔的樣子恭敬地向著篝火彈了三下,接著考力也學著做了起來。瑪克辛木大叔喝了一口酒說道:“時間長了不喝酒,這一喝到嘴里感覺很甜。”大叔喝的口也大,每輪到他喝時酒總能下去不少。瑟熱和考力有意控制著喝酒的量,盡量讓大叔多喝上幾口,免得大叔因酒少而掃興。
晴朗的夜空很快布滿了星星。他們?nèi)齻€人緊挨著篝火仰面望著夜空。燃燒的木頭噼叭作響,燃著的篝火迸發(fā)出的火星直沖夜空,遠處還傳來幾聲清脆的鈴聲,打破了這寧靜的雪夜,伴著瑪克辛木大叔、琴熱和考力入眠了……
清晨醒來時他們的毛毯和鴨絨被已覆上了薄薄一層清雪。這一夜他們?nèi)齻€人睡得特別香。他們睡覺時頭都蒙在被子的里面,絲毫沒有感覺到寒冷。篝火燃了一夜,清晨,仍冒著清淡的白煙似燃非燃。
瑪克辛木大叔起來后將散開的冒著煙的木頭又聚在一起,從旁邊很近的枯樺樹干上撕下樺樹皮,又斂起一些細樹枝把篝火重新燃起來。篝火旺旺地燎烤著已露出頭睜眼張望的瑟熱和考力。幾只馴鹿在他們周圍竄來竄去,樹林間發(fā)出被馴鹿踩斷樹枝的清脆響聲。
他們急忙吃過早飯,又急急忙忙地啟程,在傍晚的時候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克坡河。
他們在克坡河的南岸山坡下的一塊平地扎了“撮羅子”。
瑟熱從馴鹿鞍子上取下鍋碗盆等炊具,又拎著黑黑的水壺和黑黑的鋁鍋,右手還夾著獵刀,深一腳淺一腳地來到小河邊,用戴犴皮手套的手撥開了冰面上的雪,再用獵刀猛扎向冰面,把砸開大小不均的冰塊,裝滿了水壺和黑黑的鋁鍋。臨離開小河邊時,瑟熱在一棵很細小的小落葉松樹干上深深地砍了一刀,作為永久的標記,至少為下次拎冰確定了路標。
在克坡河這一帶他們?nèi)齻€人活動了三天時間,每一天他們?nèi)齻€人都分別向不同方向大范圍地搜尋獵物。瑪克辛木大叔總是一個人出獵,因為這里的地形他太熟悉不過了。對于瑟熱和考力,他們的經(jīng)驗不足且膽子不算大,每次出獵他們倆結(jié)伴而行,對獵物活動的習性和范圍根本不清楚,判斷不出獵物出沒在哪山、哪溝。有時惟恐迷失方向,每次出獵都是在太陽未落山時比大叔先回到撮羅子。每一次的出獵戰(zhàn)果都不太理想。三天來瑪克辛木大叔和琴熱考力獵獲的飛龍、灰鼠等獵物加起來不到二十只。
考力倚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光著兩只腳,面對燃得通紅的篝火說:“我總琢磨著這地方人活動少獵物應(yīng)該很多,但是,是獵物不多呢,還是我們沒有找到或是沒有碰到好的比較理想的地方?”考力剛躺下馬上又坐了起來。瑪克辛木大叔、瑟熱還有考力三個人面對著篝火談?wù)撝乱徊降拇蛩恪s艋鹦苄艿厝紵厦娴踔诤诘乃畨兀€沒有燒開。
瑪克辛木大叔像作總結(jié)似的講述他這三天來所走過的溝塘和翻越的山頭的感受:“我看這里的希望不大,因為這里很可能有其他人來這一帶打過獵,飛龍稀少不成群,灰鼠子大都在山的陽面坡活動,而陽面坡的雪還稀稀落落,有的陽面坡根本沒有一點雪,幾次發(fā)現(xiàn)了灰鼠子的腳印跟蹤沒多遠就消失了,很是費力不好尋找。”
在克坡河最后的一天他們?nèi)齻€人又出獵了。瑪克辛木大叔還是獨自一個人向東山那面溝塘而去,緊跟身后的是大叔的愛犬——努道。
瑟熱和考力向西南方向出發(fā),兩個人背的都是小口徑槍,他們倆在一座山的北坡下分開,并約定好在那里會合。考力從山坡的西面繞過山頭,瑟熱直接從前面翻越這個山頭。山的北坡是茂密的灌木叢,瑟熱在灌木叢里穿來鉆去,雪沒膝深,行走很難。終于到了山頂。山頂上長滿比人還高的達子香樹叢,密密的。剛到山頂瑟熱在一小塊空地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三角形的腳印,順著腳印跟蹤還不到三四米遠,又發(fā)現(xiàn)了還散著熱氣的稀稀落落的形如大棗般的糞便。瑟熱繼續(xù)跟蹤著留在雪地上的腳印,順著這些腳印上了山又來到了一條小河邊。小河邊暖泉水流淌著。瑟熱小心地從沒有水的地方繞著越過了這條小河。但是,走過來的腳印已浸濕成一個個深深的水坑。看上去上面是雪覆蓋著,而雪下面是水,簡直就是一片陷阱。在小河邊不遠處瑟熱又發(fā)現(xiàn)了一只大犴臥過的雪窩,瑟熱這才斷定是犴,是一只大犴帶著小犴在這里活動,雪地上的痕跡是剛剛留下的。由于瑟熱頭一回遇見到這樣大的動物的腳印,心里充滿高度的緊張和興奮。這時,瑟熱急切地呼喊考力的名字,考力在不遠的地方作了回答,一會兒功夫就來到了瑟熱跟前。瑟熱告訴考力發(fā)現(xiàn)了犴的足跡并用右手指了指雪地上的痕跡,說:“在山頂上先發(fā)現(xiàn)了小犴的腳印,也許因為我們倆走路的動靜太大驚動了這兩只犴。”其實犴的嗅覺非常靈敏,早已嗅到了陌生的氣味,再加上瑟熱翻山時踩斷和碰斷達子香樹枝時發(fā)出的聲音,就足以使一大一小的犴受到驚嚇。
“你說我們倆應(yīng)該怎么辦?”瑟熱問考力,等著考力替他拿出主意。“我看呢,咱們倆還是先試著追一段,實在追不上也就只好放棄了。”考力說出自己的想法。瑟熱沒有意見,同意考力的想法,他們倆開始沿著犴跑過的足跡深一腳淺一腳,一前一后地追趕著。在他們前面的雪地上留下了間距兩米多的跳越式足跡,照這樣的速度怎能攆上四條腿的犴呢!瑟熱和考力沿著犴的足跡追趕了不到一里路,就已是氣喘吁吁了。北山坡上一片白茫茫,雪掛沉沉地壓著矮小的落葉松樹,變成了一幅幅多姿的雪雕畫面。
齊腰深的北山坡的雪,使瑟熱和考力變成了雪中兩個小矮人。
瑟熱說:“行了吧,咱倆還是放棄吧,就是累死也追不上的,況且我們倆人背的都是小口徑槍,就是追上了也得放跑。”考力也隨聲附和說:“正好趁天亮早點回去免得讓大叔惦念。”
兩個人返回營地時天已暗了。
老大叔瑪克辛木在撮羅子進門的正面對著篝火坐著,篝火上吊著水壺,大叔一邊倒茶一邊說:“你們倆咋才回來呢?是不是迷山了?累了吧,把槍里的子彈都卸下來放好,把鞋脫了烤烤火,喝口熱茶先暖和暖和。”大叔把倒?jié)M紅茶的碗遞給瑟熱和考力。他倆分別接過大叔遞過來的紅茶客氣地說:“謝謝大叔。”
瑟熱和考力邊喝著茶邊將今天到西南方向打獵的情景,講給瑪克辛木大叔聽,老大叔饒有興趣地聽著。
聽完后老大叔瑪克辛木就問瑟熱和考力,說:“你們倆是第一次打獵,一點經(jīng)驗沒有。你們倆這回把那兩只犴可嚇跑老遠了,雪又這么的深,就是讓我這老獵手去追那兩只犴也很難追上的。算啦,收拾東西往回走,我們可以在回去的途中邊走邊打!”
瑟熱和考力聽老大叔這么一說也非常贊同,說:“行!”他倆茶也不喝了,身體還沒有歇過來就開始做飯并準備明天吃的干糧。
這么多天來他們?nèi)齻€人的主食是米飯和面條。目前大米已剩下不足一頓了,也只有和面烙餅或搟面條。
瑟熱把面和好了,放在了用雨衣膠面鋪地當起的面板上,這種情形下,上哪找塊平整的木板當面案子搟餅。考力用獵刀削好一根光溜溜的樺木棍當作“搟面杖”遞給瑟熱,瑟熱用這“搟面杖”開始一張一張地在不平的雨衣膠面上搟起了圓圓的面餅,然后將搟完的面餅放入冒著煙的黑黑的燜鍋里。瑟熱烙餅的技術(shù)還可以,好像受過專門的烹飪訓練,第一張餅出鍋色澤金黃,油香味濃,聞著油餅的香味足以挑起食欲。
他們就這樣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這很難再有機會來的“克坡河”,帶著一線希望奔向來時經(jīng)過的地方——“敖饒道”。
在返回的路程中和狩獵的時間里他們的言語少多了,有時三個人都在沉默,只是吃完了早飯后互相通報出獵的方向和范圍便背起各自的獵槍出獵了。
瑟熱曾聽老獵人講過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年輕人的墓地,這位年輕人是在一次意外槍走火中不幸喪命,長眠在這個地方。當時是一個美麗的夏天,獵點兒就扎在這里,獵人很多,“撮羅子”也有很多座,年輕人聚在一起總是毛手毛腳地圍坐在撮羅子里,不是打鬧就是好奇地擺弄槍支,“新式”步槍“砰”的一聲,子彈穿過了這位年輕人的胸膛,從此,他永遠地留在了這個充滿恐怖的地方——敖饒道。
因為忌諱這件事,瑟熱只字未向大叔瑪克辛木詢問過,他硬著頭皮在宿營地的附近山林轉(zhuǎn)了一陣,空著手回到住的地方。瑟熱回到住處把篝火燃起來。由于著急往回返,他們沒有搭建“撮羅子”,也沒有支簡單的帳篷架子,只是將地上的雪推開夠睡覺大的地方,將犴皮褥子鋪在地上露天而宿。篝火冒著濃濃的白煙散遍整個山林。
瑟熱燒著水坐在火的旁邊,不一會兒考力從身后背著槍,手里拎著兩只飛龍來到瑟熱面前,將飛龍扔在了雪地上,然后把槍卸了下來,說:“這是什么地方獵物咋就這么少呢?”邊說邊摘掉頭上冒著汗?jié)駳獾拿弊印I獰嵴f:“不行明天繼續(xù)往回返,不能在這里浪費時間。咱們倆做飯吧,等著大叔回來看他怎么說。”
飯做好了。他倆靜靜地坐在篝火的旁邊一言不發(fā)地喝著濃濃的茶水,望著篝火等待著大叔回來。這頓飯是將凍得梆硬的油餅放在燜鍋里熱一下,壺里是濃濃的紅茶。咸菜在火邊烤著。
大叔終于在太陽沒有落山之前回來了,他也只打了兩只飛龍。大叔的胡須上結(jié)了冰,皮夾克的后背出汗凍硬并結(jié)了霜。他把飛龍扔在雪地上脫掉皮夾克。獵槍已被考力接過去放在大叔的行李邊。瑟熱急忙用黑黑的冒著熱氣的水壺往大碗里倒茶水,又將大碗茶恭敬地端給大叔。瑪克辛木大叔接過碗,也不管是熱燙,深深地呷了一口,把碗放在他盤坐著的腿上。瑟熱和考力說:“咱們明天還要在這里停留一天。大叔我今天發(fā)現(xiàn)了犴的腳印。明天一早我?guī)銈儌z去追趕那個留下足跡的犴,那個地方不算太遠,翻過一座小山就到了,大約有十多里路,你們倆做好準備啊!”瑟熱和考力將信將疑地在心里各自揣磨著:明天真能幸運嗎?瑟熱在這邊回答:“好!聽大叔安排。”
第二天,一大清早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吃過早飯就一同出發(fā)了。獵犬努道急急地在前面跑著。瑪克辛木大叔背著用樺木板做成的背夾子,上面綁著鋒刃的斧子,走在中間的是瑟熱,考力跟在后面。大叔背著他心愛的獵槍。瑟熱和考力分別背著小口徑槍,從威力上講,他倆背的槍遠遠不及大叔的半自動步槍,如果遇見了大的或是兇猛的獵物,顯然瑟熱和考力難以應(yīng)付。走了很長一段的路,到了一個地方,大叔瑪克辛木就停了下來,瑟熱還以為大叔是走累了停下來休息,這時大叔不言語地用右手指點著,瑟熱意識到:大叔昨天發(fā)現(xiàn)犴的地方到了。
瑟熱繼續(xù)四面地觀察著雪地,尋找著犴的足印,在不遠處,他們?nèi)齻€人行進的左側(cè),果真有一只犴臥過留下的雪窩,但雪窩已是很長時間留下的,已被幾場清雪覆蓋,顯然不是新鮮的痕跡。瑟熱從內(nèi)心里感到一陣心灰意冷沒有了信心。這時大叔瑪克辛木卸下背夾子,把獵槍斜靠在一棵樹下,槍托深深地扎在厚厚的雪里,又從背夾子上取下快刃斧子,直奔一棵小落葉松樹砍起來,放倒了兩棵小松樹后,砍光枝丫變成了兩根小桿,大叔瑪克辛木從上衣口袋里掏出犴皮繩,將兩根小桿的細端留出長五十公分捆在一起,然后抱著捆綁在一起的桿子來到放槍的地方,把槍夾在腋下右手緊握住槍的護木,回頭對瑟熱和考力下命令似地說:“把子彈上膛做好準備,注意那靠山坡的一棵大粗樹底下,那里是熊洞。”瑟熱這時恍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來。考力開始也有點心疑,但他觀察了獵犬努道的每個細節(jié),起初跑在前邊翹起尾巴的獵犬努道,不知何時跟在他身后把尾巴又夾起來了。
大叔瑪克辛木將捆在一起的兩根小桿打著叉斜拉開,放到熊的洞口,大叔說這樣做是防止熊突然鉆出洞口,是一種最安全的措施。
瑟熱和考力都緊張地端著槍,眼神集中在大叔的一舉一動上。大叔把兩個做交叉樣的小桿放好后又轉(zhuǎn)過身,將身邊的小松樹用手折斷,弄掉樹枝后對考力說:“你過來用這樹條子向洞里伸,將睡覺的熊挑弄醒,不要怕,很安全的,有我大叔在呢!”說著把樹條遞給了急忙跑過來的考力。考力按照大叔的要求,小心翼翼地將樹條伸進洞里。考力用眼睛掃了一下洞里,也看不清熊是什么姿態(tài),硬著頭皮用力攪動著樹條。
考力的旁邊,大叔端著槍閉著左眼,槍口直貼近洞口瞄準著,右手食指扣著板機。瑟熱也端著小口徑槍瞄著洞口。
突然“嗷——”的一聲,熊的腦袋鉆出洞口,正好被兩根交叉的小桿卡住只露出尖尖的嘴巴,在熊即將伸出頭的一剎那,大叔的槍響了,聲音是那樣的脆,槍響后洞里立刻變得安靜下來。這時瑪克辛木大叔還是緊握住獵槍,向洞里瞅了一眼又對兩個年輕人笑著說:“它睡著了放心吧!”
剛才打熊的那一刻高度緊張,這會兒才使他們?nèi)齻€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氣,蹲坐在熊洞的旁邊。
歇了一陣子后,他們?nèi)齻€人將一只大個頭的棕熊拽到了洞外,然后,將熊的兩個前腿拴上犴皮繩子,將它拽到了距熊洞不遠的小河邊。
扒熊皮的技巧活全由瑪克辛木大叔一人承擔,瑟熱和考力只是按照大叔的指令去做。“抓住前腿!抓住后腿!使勁!”大叔那磨得鋒利錚亮的獵刀不停地在熊的身上揮舞著,那架勢就像是技術(shù)高超的手術(shù)師。不一會兒棕熊露出白白嫩嫩厚厚的脂肪。大叔邊扒皮邊嘀咕著說:“冬天的熊穿兩件‘衣服,害得我非扒兩層皮才行。”棕熊冬眠必須要耗掉它身上厚厚的脂肪。
大叔有節(jié)奏地把棕熊扒完皮開了膛,卸下各個部位,這回可謂是熊死一張皮呀!
瑟熱盼望著早一點收拾完畢,將熊肉捆成三份就向營地返回,可是,大叔卻是穩(wěn)穩(wěn)當當一點不急。瑟熱心里在想:這么一個大熊三個人怎么能夠背回宿營地呢?
大叔瑪克辛木不聲不響地連著將幾棵細樺樹的上半節(jié)砍斷,然后又砍斷樹梢一端,在這被留下來近一人高的樹干上,搭起了呈三角形的架子,首先將熊的頭安放在上面朝正東方向,最后把熊的心肝肺等放上去,做這些活的時候,大叔沒有讓兩位年輕人動手,只顧自己干。
一切都擺放停當,大叔似乎感到活還沒有做完,又掄起他的砍刀,在搭好架子充當柱子的樺樹上,將平面砍光露出光光的白茬。
這回大叔又像美術(shù)師開始用熊的紅紅的血和篝火中黑黑的炭,充當畫筆在白白的樺樹桿的白茬上紅一道、黑一道地畫著,手指蘸著凝凍的熊血,手里攥著篝火燒過的黑炭,神情既莊重又嚴肅,仿佛是在為一個剛剛過世的老者舉行葬禮。
事后瑪克辛木大叔在回到營地后,坐在篝火旁,喝著茶水時,講給兩位年輕人瑟熱和考力說:“獵人每當獵到熊后必須這樣做,這是獵人的規(guī)矩,這叫‘祭熊懂嗎?”
瑪克辛木大叔把所能帶回的肉均分成三份,祭完熊之后剩下的是把熊肋骨、熊掌、熊大腿和小腿,熊膽,另外還有一張很重的脂肪皮,必須一件不落地背回宿地。宿營地距離這扒熊皮的地方有十多里路呢!遠道沒有輕載。他們每個人背的重量都達到五六十斤。瑪克辛木大叔仍然在前面開道領(lǐng)路。瑟熱和考力的肩膀都被繩子勒紅了,汗水濕透了后背,結(jié)了霜。到了營地后兩個年輕人卸下后背的熊肉,一攤泥似地倒躺在鋪在地上的行李上,累得不想再挪動一步。
夕陽的光芒早已被暗灰的暮色替代,瑟熱和考力硬是挺著勁起來,弄來干柴和樺樹皮把篝火點燃起來,瑪克辛木大叔在用獵刀分解著熊的肋骨,準備篝火燃起來后,將熊肉煮下鍋。
瑟熱仍風趣地說:“今晚的美餐是油餅和熊肉,解饞哪!”
篝火上又吊起黑黑的鋁鍋,鍋里煮滿了熊的肋骨。水壺也緊挨著肉鍋吊在篝火上冒著熱氣。
凍得邦邦硬的油餅在篝火邊用木棍支著煨著火。
瑪克辛木大叔在篝火旁用獵刀削著樺樹條做筷子,瑟熱和考力都默不作聲,靜靜地望著熊熊燃燒的篝火。
天色一陣比一陣暗下去,天上的星星一會兒比一會兒多起來。瑪克辛木大叔第一個抓起一塊肋骨肉,在將要送到嘴邊時學著烏鴉的叫聲發(fā)出了“嘎嘎”的聲音,學完后狠狠地啃了口骨頭上的肉,邊嚼邊沖著瑟熱和考力說:“你們倆也學著我的樣子,先學烏鴉叫然后再吃肉,知道嗎?學烏鴉叫等于說是烏鴉在吃熊肉,而不是我們?nèi)嗽诔运@是嚴肅的規(guī)矩!”
瑟熱和考力分別從鍋里夾起熊肉,也笨笨地像大叔那樣,學著烏鴉叫了起來。他倆想笑卻又不敢笑,只有生硬地學著、叫著,聲音雖然不很逼真,但這叫聲足可以震響這寂靜的山林。
這一夜,他們在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與歡笑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