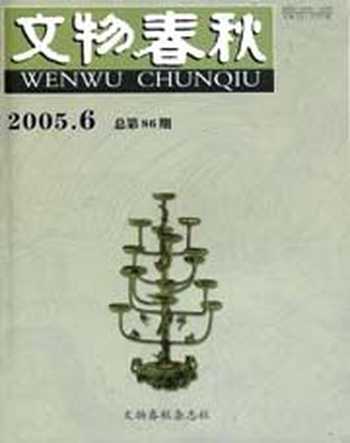關于承德民族文化遺產發掘與研究的思考
田淑華 王月華
【關鍵詞】承德;民族文化遺產;發掘;研究
【摘要】承德自古為多民族聚居之地,是一個民族關系復雜的文化區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這里一直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匯地帶,南北經濟類型交錯,多種文化因素薈萃,而文化交錯必然會產生更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民族文化。本文概述了承德民族文化遺存的豐富多彩,論述了對承德民族文化遺產發掘與研究的必要性。
一、發掘和研究承德民族文化遺產的必要性
承德一帶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其各民族的歷史、文化、藝術、宗教、民俗及考古遺跡、遺物等均屬于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的范疇,是中華民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掘和研究承德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是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還是當今發展旅游事業,促進經濟繁榮,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承德自古為中原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交往、雜居、融匯之區域
承德地處長城以北,是銜接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區域,地扼關內外要沖,同時也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交錯的地帶,歷史上多種民族雜居,多種文化因素薈萃,在民族關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史料記載:“長城以外古為引弓之國,建庭卓帳,遷徙無常。”[1]早在殷商時期,承德就居住著一些古老民族,其中包括甲骨文所記載的土方。西周至春秋時期,這里居住的民族主要是東胡和山戎,東胡地望偏東北,山戎居西南。“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溪谷,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2]在灤平發現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中,有山戎氏族酋長墓,墓中所出骨架十分高大,頭部所戴皮帽在帽沿處鑲嵌一周銅泡,耳飾大銅耳環,頸下掛有四圈由青玉管、瑪瑙、綠松石、白骨珠組成的項飾,銅珠組成的聯珠曲尺形飾件由肩部垂到膝前,腰部佩有青銅匕首,文化特征明顯。周初此地屬古燕國勢力范圍,山戎、東胡由其統屬。后來東胡勢力漸強,不斷南擾,危及燕。燕將秦開為質于胡,“歸而襲破走匈奴,東胡卻地千里”[3]。于是燕筑長城,自造陽(今河北懷來)至襄平(今遼寧遼陽),并于燕北設遼東、遼西、漁陽、右北平、上谷五郡。其中,承德地區分屬遼西、漁陽、右北平三郡。
秦漢時期,承德地區已經明確地劃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轄區。秦代,今承德市及承德、隆化、興隆、圍場、平泉、寬城各縣屬右北平郡,灤平、豐寧屬漁陽郡;西漢承秦制,承德市及承德、隆化、圍場、平泉、興隆、寬城各縣屬幽州右北平郡,灤平、豐寧屬幽州漁陽郡;東漢時期有所沿革,承德、興隆、寬城屬幽州右北平郡,而其它幾個縣屬鮮卑控制區[4]。這一時期,匈奴、烏桓、鮮卑同漢族在此區域錯居活動。漢武帝曾設烏桓校尉,通過幽州控制燕北;曹操北征烏桓即以幽州為基地。此后,烏桓部族漸散,但魏文帝時仍設有烏桓校尉,屯薊,與幽州同治所,而代烏桓而起的鮮卑族開始活躍在包括承德在內的燕北大地上。
兩晉南北朝時期,承德地區建置發生變化。西晉時,只有今興隆、寬城屬幽州北平郡,其余則屬鮮卑宇文部和段部的控制區。前秦盛時,承德地區分屬幽州漁陽郡和北平郡。北魏盛時,承德大部屬安州廣陽郡,今隆化縣置為燕樂縣,為安州和廣陽郡治所,豐寧、圍場則屬御夷鎮轄區。當時,鮮卑又分慕容、宇文、拓跋、段部、乞優、禿發6部,其中主要活動于今承德境內的是宇文和段部。宇文氏屯保饒樂水,居今赤峰以南和圍場、豐寧一帶;段部則活躍在今灤平、隆化、平泉一帶。后慕容鮮卑建立前燕和后燕政權,侵并宇文和段部,承德又為慕容所統治。
隋唐時期,隨著全國統一局勢的再次形成,承德建置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動。隋代,今承德、興隆兩縣屬漁陽郡轄區,其他縣市為奚族控制區。盛唐時,承德地區屬河北道轄區,其中隆化縣屬薊州,其他縣市屬饒樂都督府所轄。這時活躍在承德地區的民族主要是契丹和庫莫奚(奚族)。奚為鮮卑后裔,宇文之別種。唐太宗時,因奚人從征高麗有功,賜其首領并設饒樂都督府,受統于幽州節度使。后拓跋氏建北魏,承德成為北魏之轄地。
遼、金、元、明時期,全國政治形勢向大一統發展,承德的建置反映著這一歷史進程。遼代,承德屬中京道北安州和澤州轄區,是從燕京至中京、上京的必由之路。北安州治所為興化縣,在今承德市西;澤州治所為神山縣,在今平泉縣西南。當時居住在這一帶的民族主要是契丹、奚、渤海、室韋及漢族。澶淵之盟后,宋、遼兩國通好百余年,相互往來頻繁,漢族大量遷徙塞外,北方少數民族入居中原,長城內外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交流與融匯。金代,承德地區屬北京路,歸大定府管轄。元代,承德市及灤平、承德、隆化、豐寧、圍場、興隆各縣歸中書省上都路管轄,寬城、平泉屬遼陽行省大寧路管轄。蒙古人統一全國,承德的少數民族逐漸與漢族融合。明前期,承德地區均屬京師北平行都司轄區,其興州五衛在今承德市西南,會州衛在今平泉縣西南。明后期,承德地區為蒙古韃靼控制區。
清代,承德的歷史位置變得越發重要,在民族關系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雍正元年(1723年)于此置熱河廳,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為承德直隸州,乾隆七年(1742年)復為熱河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置承德府,領平泉州和灤平、豐寧、隆化(又稱皇姑屯)[5]。這一時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匯更為突出。康熙皇帝借鑒歷代帝王治國之道,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打破長城內外界限,實施“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和“以德為衛”、“以兵息兵”的軍事策略,最終實現了天下一統的治政理想,承德因此而成為促進民族團結的特殊區域。
2、承德是中原通往北方的交通要塞
在我國歷史上,長城或關塞地帶歷來是民族融合區域。古代的承德,是中原通往北方的交通要塞。從華北平原到蒙古草原交通往來的古道有三條:一為出居庸關去蒙古高原;二為出古北口(或喜峰口),穿燕山北部的丘陵地帶,向東北至松遼平原;三為沿海而行,出山海關至遼河下游。承德位于北上的中路(即古北口路)。古北口作為關城要塞,戰爭時期關上城門,南北對峙,和平年代打開城門,南北通行通商。宋《路振乘軺錄》中便有古北口榷場的記載。經濟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互通,使宋、遼兩朝交往的通道成為重要的民族文化接合部。同時這里的人口遷徙也很頻繁,人口的流動和交相錯居,給民族融合注入了活力。多種民族、多種文化共存共榮,相互影響,兼收并蓄,呈現出異彩繽紛的文化狀態。
在古北口通往遼中京的塞外之地,居住著逐水草而居、以“西樓、羊馬”為富的契丹人,以射獵、伐山、陸種為生的奚人,以冶鐵為業的渤海人,還有一些為奚人代耕的漢人。考古發現在隆化有奚人打造館,在灤平有渤海人冶鐵遺址。宋蘇頌使遼詩云:古北口“耕者甚廣,牛羊遍谷,問之皆漢人佃奚土”[6]。遼宋之間來往頻繁,常互派使者,宋朝的使節歐陽修、劉敞、蘇頌、蘇轍、王曾、路振等人使遼,都是出古北口[7]。清初,古北口至木蘭圍場成為北京通往內蒙古東部、東北、漠北、沙俄遠東的交通要道。康熙認為,承德“北界興安,東及遼水,山川形勢之雄,甲于紫塞”,“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可“控制蒙古諸部落,內以拱衛京師”,于是設置“習武綏遠”的木蘭圍場,肇建懷柔“徠遠”的避暑山莊,并沿御路設驛站,修建供每年出塞“巡邊”時休息的諸行宮。同時,把藏傳佛教作為鞏固政權的思想工具,修建宏偉的外八廟寺廟群,以綏靖荒服,柔懷遠人。清帝在此處理民族事務,不僅北方的蒙古族,就連新疆、青海、西藏的上層人物都不斷來承德朝覲皇帝,可見承德在歷朝歷代都是南北交往的交通要塞。
3、承德是清王朝的第二個政治文化中心
歷史上,遼、金、元、清均為北方牧獵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他們吸收漢族文化,沿襲秦漢以來的統治制度,而在塞外又同時保存了固有的游獵習俗;既有自己的都城,又有在行宮帷幄處理政務的習慣。遼行營衛制;金行“猛安謀克”制,對原遼朝統治下的漢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進行統治;元在立州郡的同時,對蒙古各部仍采取部落制;清代則將習武行圍、每歲秋狝定為“家法”。在處理民族關系上,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民族分裂,加強中央集權,扼制沙俄侵略,恩威并施以團結蒙古各部,取得了歷史上民族團結、安疆固邦的最大成功。隨著避暑山莊的建立,清王朝在承德設立了一系列政治機構,同時為宮廷服務的倉庫、皇莊、商業活動場所隨之發展起來。雍正元年(1723年)始設熱河廳,十一年改為承德州,到乾隆年間,承德已儼然成為一都會。“府志志府也,承德則府而都會矣。”[8]這個都會的形成,是與清朝治國安邦的政治謀略分不開的,一方面和北方民族的社會結構及生活習俗有關,另一方面是和清初針對北方的民族政策有關,承德作為清王朝第二個政治文化中心,得到了全面的繁榮和發展。
承德在歷史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決定了發掘與研究其民族文化遺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豐富多彩的承德民族文化遺存
從史前起,承德就是北方畜牧文化與黃河流域農耕文化相交錯、融匯的區域。燕山南北的兩種經濟類型、兩類文化傳統的民族(群體)既時有矛盾、沖突,又互為依存。可以說承德地區是一個最為活躍的民族大舞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融合早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早在舊石器時代,承德就有了人類活動,考古發現古人類洞穴遺存和化石點20余處,出土動物骨骼化石數十種。位于灤河流域柳河沿岸的四方洞是一處舊石器晚期人類洞穴遺存,出土石器千余件。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達數百處。圍場縣陰河沿岸發現群體人面巖畫,這是人類最早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精神象征。在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類型岔溝門遺址發現大量房屋、灰坑遺跡,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百余件,其中有“之”字紋筒形缸、劃紋碗、壓印紋陶片及細石器等;在距今7000年的趙寶溝文化類型后臺子遺址,出土了七尊女性裸體石雕像和玉琮,這是原始社會人類藝術的珍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在圍場、平泉等縣有距今45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類型的淀園子、海龍溝、東山頭遺址,淀園子出土的玉豬龍、玉環,屬紅山文化玉器群。這些文物為研究當時人類的生存環境、禮儀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提供了相關信息。
殷商時期,甲骨文中的“土方”曾與商有過頻繁的戰爭交往。據考證,“土方”地望在今承德一帶。豐寧發現的刻有“亞謾泵文的銅鼎,是商王朝封在這一帶的亞氏族部落的遺物[9]。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多有發現,平泉縣半截溝遺址即為典型的一處,其文化層堆積較厚,房址、石墻、窖藏等遺跡清晰,出土文物豐富。在隆化、興隆、圍場、豐寧等縣先后出土過鑄有族徽的青銅簋、格柄短劍、鈴首匕、羊首刀、銅戈、銅矛、蘑菇首青銅短劍、曲刃式青銅短劍等。在老哈河、灤河、伊遜河流域,發掘了數百座山戎氏族墓,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灤平縣苘子溝山戎墓群最為典型,在集中發掘的67座墓中出土文物1100多件,其中氏族酋長和奴隸主墓存在殺牲現象,用奴隸或馬、狗殉葬,隨葬品有青銅兵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及銅、玉、石、骨、瑪瑙等佩飾品。特別是大量鄂爾多斯式青銅牌飾,如半浮雕蹲踞虎形、匍匐蛙形、犬形等,形制多樣,制作精美,生動逼真。此外,還有金璜形項飾、鎏金銅帶鉤及車具。許多文物的器型、紋飾兼具南北文化特征,體現了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相互融合。這些文物不僅印證了文獻記載,而且充分說明,中國北方青銅器的共同性是由不同族源的文化因素相互影響和交融的結果,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雙向文化影響所形成的。
戰國秦漢時期,在承德地區燕秦長城及漢代長城附近分布的城垣有20余座,有的與烏桓入居塞地相關,多數為當時的屯戍之所或貿易之地。這些城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銅器、鐵器、錢幣及建筑構件。尤其是興隆縣發現的燕國生產工具鑄范,說明當時的鑄造水平已經很高。圍場先后出土5枚秦代鐵權,權體表面陰刻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計39字:“廿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伴隨出土的還有秦代瓦當和半兩錢。戰國至漢時期的墓葬多分布在同時代的城址附近,出土文物豐富多彩,鼎、豆、壺、盤、匜、簋等仿銅的成組禮器具有中原文化特征,另有用朱彩繪出銅器花紋,非常精美。隆化發現的刻銘銅戈是秦統一六國滅三晉時期的遺物。漢代墓葬中出土大量陶器、鐵劍和銅盤、銅燈、鎏金獸足器紐、銅鏡、博山爐等,其文化特征與滿城漢墓出土器物基本一致。平泉發現的漢半兩鉛質范母亦屬罕見珍品。
北魏、隋唐時期的文化遺物在承德也多有發現,如刻有紀年的北魏銅佛像、北魏太和十三年銅菩薩像、馬蹬、鐵釜、雙耳鐵鍋等。韓家店窖藏出土的奚族文化遺物,寬城發現的唐代海獸葡萄鏡、菱花形鎏金鹿紋銀盤、銀壺等,都是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的實物依據。
遼、金、元時期的文化遺存在承德地區分布更為廣泛,隆化縣土城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古城址。城址前后沿用四個朝代,即北魏的安州,遼代的北安州,金、元時期的興州。城內有建筑基址、瓷窯址,出土大量生產、生活用具及建筑構件,瓷器種類繁多,地方特征明顯。韓吉營發現獸紐鎏金“契丹節度使印”,具有唐末五代風格。灤平縣興州古城即為金、元時期的宜興故城。有的窯址和墓葬在出土遼三彩、雞冠壺等遼代典型器物的同時,多伴隨宋代瓷器及貨幣出土。灤平發現的金代農家窖藏出土了成套農業生產工具,其中農耕播種器點葫蘆是我國農業考古的重大收獲。遼、金時期的墓葬,主要有平泉遼代大長公主墓、上應杖子壁畫墓、耶律加乙里妃墓、石羊石虎墓群,圍場望道石遼墓、大局子遼墓及興隆梓木林子金代墓等。大長公主墓為遼代大型磚室墓,墓主人是遼景宗耶律賢長女耶律觀音女,其配偶即契丹國北府宰相蕭繼遠,現存大型雕刻石棺和墓志。興隆縣梓木林子墓主人為遼代貴族后裔蕭仲恭,此人曾隨天祚帝西奔被金人所執,降金后為金朝重臣,后被封為“越國王”,其墓志用契丹小字書寫,十分珍貴。平泉石羊石虎墓群的大型石刻,反映了遼代貴族在埋葬習俗上受唐宋制度影響之深。遼代墓葬中出土的銀、銅蓋臉,銅絲網套,鎏金銀冠,銀鐲及銅佛等文物極富民族特色。承德縣發現的契丹國金牌和銀牌是皇帝用以調兵遣將的圣旨牌,當與遼末金初的戰爭有關。此外,還發現了遼代渤海冶鐵遺址、石刻和摩崖造像,并出土和征集了一批宋、遼、金、元時期的官印。在隆化鴿子洞發現的元代絲織品窖藏,包括絲織品、民間契約、俸鈔記事文書、骨角飾、銀飾等,其中以絲織品為主,綾、羅、綢、緞、紗、絹、錦(納石失)一應俱全,品種有被面、襖、袍、鞋、帽、香囊、針扎和各種紋樣的帶飾等,特別是“納石失”是古代一種高級織金錦,尤為珍貴。有的服飾在紋樣及質地上明顯帶有唐宋時期的流行風格,同時又具北方蒙古草原的民族特色,充分體現了蒙漢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些文物為研究元代社會歷史、紡織技術、刺繡工藝及承德地方歷史、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明代承德屬北平府,在長城沿線發現了大量明代遺跡、遺物,特別是記載當時長城修建情況和鎮守薊遼邊鎮名將的碑刻等,為研究明代的政治、軍事及邊防事務提供了科學依椐。
清代的文物古跡在承德不僅豐富,而且名揚四海、享譽中外。避暑山莊是我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外八廟以其龐大的群體建筑,恢宏的氣勢,將歷史、民族、宗教、文化、藝術成功地融匯在一起,堪稱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寶庫。這座寶庫包容的歷史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山莊的建筑藝術、園林藝術突出體現了各民族的融合及清帝大一統的政治思想,融匯了各民族宗教和習俗的精華,并集中吸收了漢文化的精髓。清朝皇帝對各民族語言文化十分重視,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匾額、楹聯、碑刻及典籍編纂等,都體現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特征,每一處景觀從構建到題名,無不滲透著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因素,僅麗正門匾額上的五種文字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從古北口到木蘭圍場,沿清代御道大量的遺跡、遺物無不在體現一個主題,就是民族的大一統,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這是一座我們發掘不完、研究不盡的民族文化寶庫。
以上所列僅是承德民族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這些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雖然在不斷地被發掘,但人們對這些民族文化遺產尚未全部認識,大量的民族文化瑰寶仍“養在深閨人未識”,有待于今后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三、幾點思考
中國北方民族文化的發生與發展,離不開各民族活動區域的地理環境及地域變化。承德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古代文化區域,系統發掘和研究這一帶的民族文化遺產,不僅有助于對承德歷史的全面認識,而且將會使避暑山莊研究進一步深化。因此,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開展民族考古工作,解決歷史缺環問題
在民族文化的發掘中,特別是長城以北少數民族文化的發掘,難度是很大的。因為這些民族活動范圍和勢力范圍非常廣闊,流動性大,游牧遷徙,且長于征戰,生存環境惡劣,不善論經治史,因此史籍記述甚略。發掘和研究民族文化遺產,田野考古尤為重要。就承德而言,大量地上、地下古文化遺存,如縣區的考古遺跡、民俗文物及山莊內外有關清代的遺址等,有待我們去調查,通過考古手段掌握翔實的第一手資料,這是民族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礎工作。應該對所有的遺跡、遺物進行科學斷代,認真研究,確定族屬,同時加強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各學科的密切合作。
縱觀承德已有的考古資料,雖然比較豐富,但尚有許多歷史缺環。如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文化遺存至今仍為空白,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典型遺存需要進一步調查與發掘,還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系統考古調查及其族屬問題的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調查和研究等。近年來承德山戎文化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成果,但缺乏系統和深入。應該在前段工作的基礎上,重點對山戎文化遺存比較集中的灤平、豐寧、隆化等縣進行系統的田野考古調查,開展課題研究,以全面揭示山戎文化的內涵及在燕山北部的分布規律和發展脈絡,解決相關的學術問題。還有遼代奚族問題、戰國至漢代城址、遼代城址及其相關學術問題,都需要通過民族考古學的開展,深入發掘民族文化遺產來逐一解決。
2、搜集檔案資料
承德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但史籍中對長城以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記載卻很少。這些游牧民族,有的沒有自己的文字(如匈奴),有的雖然曾有過文字但早已失傳(如鮮卑),有的民族文字雖流傳至今但不為人們所熟識,難以辨讀其意(如女真、契丹),還有的能夠辨認卻不能普遍使用(如蒙、滿),還有些古代民族文字資料至今鮮為人知。所以,挖掘、搜集、整理各民族的檔案資料也是開展民族文化研究重要的基礎工作之一。
3、注重考古與文獻結合
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研究,不能就文物說文物,要透過文物看歷史。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說:“中國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承德地區民族文化是滿天星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的文化內涵、文化面貌、發展淵源以及在這一帶更迭交錯、縱橫變化的地域關系等問題的研究,都需要考古與文獻的有機結合。考古可以糾正和補充文獻記載上的謬誤和不足,文獻可以為考古與勘探、調查與發掘提供科學線索。因此,文獻與實物相互印證,兩者緊密結合,民族文化遺產的發掘與研究才會全面系統,更具科學性。
————————
[1][8]清道光九年《承德府志》。
[2][3]《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
[4][5]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
[6]金毓黻主編:《東北通史》?穴上編?雪,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遼寧大學1981年翻印。
[7]《宋史》,中華書局,1959年;《遼史·地理志》引王曾:《上契丹書事》。
[9]《承德地區文物普查報告》,內部資料。
主要參考文獻:
《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文集》,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
(作者單位:承德市文物研究所、
灤平縣博物館)
〔責任編輯: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