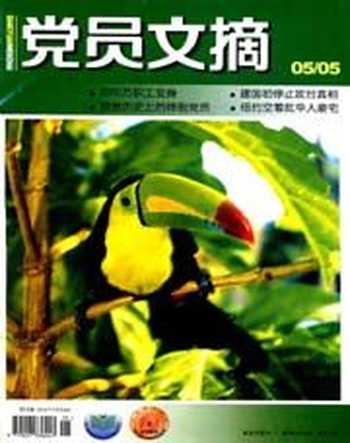建筑招投標中的黑幕:假的,還是假的
劉萬永
“干這種齷齪的事,簡直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
2004年7月15日早上7時30分,一輛黑色桑塔納轎車開進北京某區工程交易中心。
“老規矩,進了開標室,咱們就誰也不認識誰了!”在車里,賈利剛一邊分發標書,一邊叮囑三位同事。標書用牛皮紙袋子封裝,上面分別寫著四家公司的名字。
“知道了!”同事們顯然對此心知肚明。
9時整,××住宅小區工程監理項目開標儀式準時開始。招標公司、建設單位代表、市場管理人員嚴肅地坐在一邊,四家投標單位的“代表”——賈利剛和他的三名同事坐在對面。
主持人莊嚴地打開密封的標書,檢查單位印章是否清晰,手續是否齊全,然后把正本交給唱標人。
“開始唱標。”主持人示意。
“我公司接到貴單位招標文件后,經領導研究決定,現以報價34萬元監理費,費率1.7%承接該工程。”賈利剛聲音宏亮地宣讀標書。現在,他的身份是A監理公司經理。
市場管理人員準確地把他的話錄入計算機。
“我公司接到你單位招標文件后,經領導研究決定,現以34萬元監理費,費率1.7%承接該工程。”科里的司機把賈利剛的話重復了一遍,不過,他現在的身份是B監理公司辦公室主任。
接著,另兩名同事分別以C監理公司經理、D監理公司經理助理的身份宣讀了各自的報價和費率。四家的報價都是一樣的。9時30分,開標儀式結束。
“終于演完了!”回公司的路上,賈利剛深深地松了一口氣,每次開完標,他都會有這種感覺。按規定,當天下午專家要評標,幾天之后才會公布哪家公司中標,但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公司肯定會中,上午的活動只是做做樣子。
剛才還形同陌路的三名同事早已聊起天來,賈利剛卻心情沮喪,“50多歲的人了,還干這種齷齪的事,簡直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
四年來,賈利剛演出了十幾回,早已深惡痛絕,決心把黑幕說出來!
“這幾年公司沒有中過一個真標”
今年54歲的賈利剛對建筑行業非常熟悉。1991年,他開始擔任《建筑勞務報》主編。2000年,賈利剛調到北京首建工程咨詢監理有限公司負責經營,2004年后任市場部經理,主要負責建筑工程監理招投標工作,2004年10月離開公司。
四年時間,賈利剛參加了幾十項工程監理招投標,親歷了招投標的各個程序,有時還要協助甲方辦理招投標手續。他深刻地感覺到,建設工程招投標活動是有法可依的,有形建筑市場的規則是健全的,程序也是嚴謹的。可就在這規范的市場管理下,卻涌動著不規范的“地下活動”。
按照建筑法規,施工、監理企業為了能承接工程、獲取任務,必須在招投標市場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才能擁有進入建筑市場的一席之地,這是企業的生存之本。因此,招投標市場競爭的成敗與否,關系到企業的命運,拿不到任務,一切都是空談。
負責招投標的前兩年,賈利剛經常跑到工程交易中心查看大屏幕上的相關信息,刷卡登記。公司領導也非常重視,接到招標文件立即組織評審,安排專業人員撰寫監理大綱,對參加投標的每一項工程都抱有很高期望。可十幾次招標下來,每一次都杳無音訊。據賈利剛統計,從市場大屏幕上獲取信息登記投標,被建設單位邀請入圍參加投標的項目只有30%。盡管經過百般努力,最后中標的機率是零。
“陪標,就是大家一起演戲”
賈利剛的郁悶并沒持續很久,因為他掌握了招投標的游戲規則:“陪標”。
所謂“陪標”,就是在工程項目進入招投標程序前,建設單位已經確定了意向單位,然后由意向單位根據投標程序要求,聯系關系單位參加邀標,以便確保意向單位達到中標目的的活動。
按規定,建筑工程施工招投標至少要有七家競標,而監理招投標要求至少四家競標。對賈利剛來說,找三家監理公司陪標并不是什么難事,因為大家需要相互幫忙。
一次,賈利剛所在的公司承接了一項10萬平方米的工程,業主是一家新注冊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為了慎重選擇合作單位,開發公司先分別找了四五家監理公司,自行組織招投標。
經過考察和評審投標書,總監理工程師經過面試,最后確定賈利剛所在的公司為意向中標單位。“你們自己找三家單位吧,再找個人協助辦理招投標手續。”
賈利剛則心知肚明。“在實戰中,其實哪家中標,從標書裝訂上能看出來,我們自家的標書裝訂一本35元,是精裝本;陪標的一本8元錢,是簡裝本。從投標書的薄厚上也能區分哪家是真,哪家是假”。
開標那天,照樣是賈利剛和部門三名同事出場演戲。
不過此次,卻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市場管理代表指著三份標書相同的痕跡,小聲對招標公司代理人說:“這明顯是一家做的吧。”原來,三份標書都是在同一復印機上復印的,在每頁紙上相同的地方都有油墨的痕跡。賈利剛的心提了起來。
只見招標公司代理人跟市場管理代表小聲說了幾句,她也就不吭聲了。
推杯換盞、歌舞相伴,關鍵還要糖衣炮彈!
“只要干上這一行都很清楚,要想承接任務就要從源頭抓起,臨拜佛再燒香已經來不及了。”賈利剛說,我們要調動一切因素尋找工程信息,有的工程剛一立項,就已有不少商家開始跟蹤了,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同建設單位建立特殊的關系,不斷地加大投入,取得開發單位關鍵人物的首肯。
賈利剛說,在自己尋找監理項目的接觸中,一般都要把建設單位或中間人請出來,大致要經過三個層次,一是推杯換盞,二是歌舞相伴,三是“袒”誠相見。
有一次,在一家飯店里,由中間人引見賈利剛見到了一位開發單位的主管。對方聲稱投資3000萬元在某小區內建一座國際學校,50萬元的監理費只給40萬元。
“我一聽打八折還能承受,就開始推杯換盞。在他們的提示下,進入第二個層次。前面消費500元,后面消費3000元。”
過后,中間人帶話,還要賈利剛所在的監理公司給回扣現金10萬元,不同意就免談。
所謂應酬,就是吃喝玩樂。禮品也要爭相拜送,煙酒、字畫、古董等等。各種招數能讓人眼花繚亂,難以抵擋。
公司甚至有專門的資金安排規定,為公司介紹并承接一項工程監理任務,如正常收費可提取應收監理費的10%作為獎勵基金。“這實際就是射向掌握工程支配權力人物的糖衣炮彈” 。
賈利剛說,正是由于這種私下運作,不少工程項目在沒有進入招投標程序前,就已經有了中標對象,這種私下的活動才是真正的招投標實戰,等進入了市場登記,大屏幕開始發布工程信息時,招投標活動已經接近了尾聲。后期制作階段,實際上也就是走過場演戲,其結局完全取決于“導演”和“編劇”。
“什么時候講假話需要勇氣,一切就都正常了”
“我不希望看到全國都在演戲,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今年2月,賈利剛以一名普通建筑從業者的身份,把加快推進工程招投標改革的建議寄給了建設部部長。
“我相信部領導會重視的。”他說,“講真話是需要勇氣的,什么時候講假話需要勇氣,一切就都正常了。”
最近,有一個消息讓賈利剛感到欣慰:《建筑法》修訂工作已經完成了修改稿,報送國務院法制辦征求意見,現已交全國人大,以期年底完成對該法的修訂。
新修訂的《建筑法》將特別針對當前工程建設招投標活動中的資格預審、評標、中標等環節可能引發的腐敗問題,尤其是領導干部插手和干預國有投資工程招投標活動等重點問題進行遏制。修訂后的《建筑法》將強化對專業工程招投標活動的監管,同時嚴格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加快信用體系建設,消除政府工程建設中滋生腐敗的條件,對工程招投標進行全面規范。
這與賈利剛平時對招投標改革的思考有些不謀而合,他根據自己的經歷與感受總結了五條:
一是施工、監理企業按照資質等級在不同層次、規模、范圍內競標,實行“分餐制”,促進強者,保護弱者。
二是按程序公開建設單位意向與專家評標相結合,改變現在投標書一錘定音的模式。
三是在關鍵環節嚴格控制資金到位率,招標時聯合審議開工資金落實情況,控制資金流向。
四是拓寬政府主管部門市場服務范圍,包括統一組織代理招標、進行招投標單位信用評議等。
五是監控體系由有形市場向無形市場延伸,從源頭上加強工程支配權的監督控制,以預控為主,降低腐敗現象的滋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