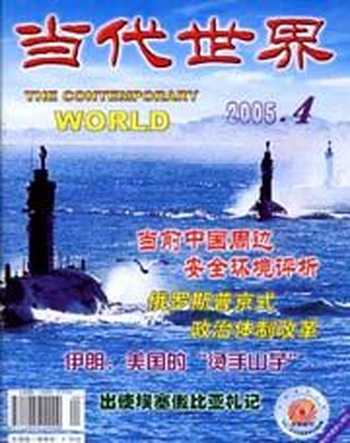美國圖謀扼殺中國核武器計劃內幕 (中)
侯紅育
蔣經國與肯尼迪密談
采取行動的可行性
1963年9月,蔣介石派兒子蔣經國訪問華盛頓,探討對北京的核計劃應采取的措施。中情局局長麥科恩與蔣經國集中討論華盛頓與臺北在對中國大陸采取軍事行動上的分歧。談話最終轉移到對大陸的核計劃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上。
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擁有核武器將使蔣介石“光復大陸”的希望徹底破滅,蔣經國在幾個場合都提出了攻擊中國核設施的問題。他在與肯尼迪會見的前一天到中情局訪問,并參加了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空襲的討論。后來,蔣經國與國家安全助理邦迪討論了對大陸核設施進行打擊的問題。邦迪贊同“削弱”大陸的一些措施,但他懷疑國民黨奪取大陸領土的可行性,稱這可能會導致北京與莫斯科重新結盟或“引發大沖突”。蔣經國提出對大陸的核設施采取行動,建議美國為國民黨突擊隊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持”。邦迪回答說,“美國對制定一些行動計劃非常感興趣”,這可以“延緩和阻止中國的核計劃”。但是,他認為這些措施需要“最周密的研究”。
9月11日,肯尼迪與蔣經國進行了長時間對話。肯尼迪對向中國核設施派遣突襲隊的建議提出疑問。他問:“向這么遠的距離空投300至500兵力是否可行......投送兵力的飛機會不會被擊落?"根據記錄,蔣經國回答說,用突擊隊襲擊的建議“昨天已經過中情局官員研討,他們認為這個計劃是可行的”。肯尼迪的詢問表明他對這些建議的可行性懷有疑慮,他強調計劃要“切實可行”,可以“削弱中共政權”。為了避免在古巴發生的豬灣事件重演,華盛頓和臺北需要更多更準確的大陸情報。
幾天之后,蔣經國與麥科恩正式將他與肯尼迪及其顧問達成的諒解確定下來。麥科恩和蔣經國同意成立一個計劃小組,研究由國民黨軍隊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襲擊的可行性。任何行動都需要獲得最高層的聯合批準。遺憾的是,這一計劃小組的報告至今仍未解密。
美官方完成采取
行動可行性的報告
1963年秋天以后,對中國核計劃如何辦的問題不僅成為美國政府高層會議的主要議題,而且也成為記者報道的主要對象。最突出的是非常有影響的專欄作家斯徒沃特連續在9月和10月的《星期六晚報》專欄里寫到,有必要對中國的核計劃采取軍事行動。他斷言,“總統和其內圈已經原則同意,必須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中國發展核武器,阻止中國成為核大國。”
在幕后,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襲擊。1964年初,中情局仔細研究了空投國民黨兵和進行其他秘密行動的可能性。五角大樓研究了準軍事性的行動。1963年11月18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斯韋爾·泰勒向其同仁提交了一份以《我們怎樣才能阻止或遲滯中國成功實施核武器計劃》為題的文件,供下一次會議討論。國防部副部長吉爾帕特里克在一個月后建議參聯會成立一個跨部門小組,“考慮阻止中共核武器計劃的方式和方法”。此外,參聯會還對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早些時候提出的制定緊急計劃,對中國發動常規打擊,以癱瘓中國核武器計劃作出了反應。12月中旬,參聯會制定了一個多梯隊攻擊的計劃,旨在使中國的核設施造成重大損失,遲滯中國的核計劃。
1963年秋天,鮑爾斯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他建議美國對中國核設施采取行動,否則印度將擔心中國的核能力,從而刺激印度發展核武器。
除軍事選擇之外,肯尼迪與他的顧問還力圖獲得蘇聯在不擴散協議上的合作。1963年秋,國務卿臘斯克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聯合國討論不擴散問題。當葛羅米柯提及多邊力量計劃這一問題時,臘斯克刺激他說,莫斯科向中國提供核幫助時就已“失去了貞操”。10月10日,葛羅米柯與肯尼迪進行對話,表示愿對中國間接施加壓力。葛羅米柯認為,進一步孤立中國,要求中國遵守不擴散標準,將“使中國的政治形勢更困難和更微妙。”肯尼迪問中國什么時候會擁有核武器,葛羅米柯說不知道,稱“蘇聯沒有給中國任何東西”。
在肯尼迪考慮對中國采取行動時,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計劃人員卻打起了退堂鼓,開始對中國的核武器計劃將會產生“不可容忍的”影響的論調產生懷疑。早在1963年7月,在哈里曼試圖與赫魯曉夫就與蘇聯合作打擊中國核設施之前的幾個星期,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沃爾特·羅斯特通知他說,北京可能發展最低限度的核能力,不可能使“任何人信服”中國能“用核武器作為侵略的保護傘”,不僅“美國占壓倒性優勢的核力量”將威懾北京,而且“中國期望保持其核力量作為一個可信的核威懾將使中國在對抗美國時變得更小心翼翼”。
羅斯特的助手羅伯特·約翰遜已經完成了《中共核爆炸和核能力》的報告。1963年10月,約翰遜將其報告壓縮到100頁,并廣泛散發。他曾經與國務院、國防部、軍備控制與裁軍署、中情局和其他情報機構的官員密切合作。他的報告獲得了廣泛認同。肯尼迪總統的一些顧問考慮為總統提供一份報告,但他可能從未目睹。
羅伯特·約翰遜的研究報告避開使用“威脅性的形勢”等言詞。報告的結論稱,中國擁有核能力,“在無限期的將來,將不會改變大國之間的真正力量平衡或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不需要美國進行重大戰略調整。對約翰遜而言,“中美兩國力量的極大不對稱性和中國容易受到傷害的情況”將使中國的核威脅受到極大制約。擁有核武器的中國將在美國的打擊范圍之內,而中國卻無力打擊美國,這就迫使中國“在侵略時考慮美國的核或非核攻擊”,從而使得中國“非常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國受到“嚴重攻擊”。約翰遜的觀點是,中國需要發展核力量威懾對其本土的攻擊,因此不可能改變其謹慎的軍事政策。
雖然羅伯特·約翰遜淡化了軍事威脅,但他對中國進行核試驗造成的軍事影響并不樂觀。他認為,中國領導人不大可能進行“嚴重的公開威脅”,但他們會恰當地認為核能力能“削弱美國盟友的意志”,促使他們包容中國,從而侵蝕美國在東亞的影響。中國將把核武器作為一件“政治武器,以贏得尊重,推動中立化和鼓勵革命者”。
羅伯特·約翰遜認為,為了抵消中國擁有核武器后產生的政治影響,美國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動。在軍事政治方面,一旦北京爆炸了核武器,美國必須準備向盟友“再次做出安全承諾”,幫助盟友與中國對抗,以抵消“中國的影響,抗擊中國的壓力,并阻止盟友發展核能力”。美國要重申對盟友的安全承諾,就需要“以足夠的軍事力量,公開和快速地對中國的軍事入侵做出反應,但不應過分依賴核武器”。如果華盛頓過分依賴核武器威懾大規模的“非核武裝入侵”,美國的亞洲盟友就會更傾向于同北京合作。他期望肯尼迪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足以震懾北京。
臘斯克閱讀羅伯特·約翰遜的研究報告后,頗受影響。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羅伯特·科默認為,約翰遜的估計使得對中國核設施進行打擊的預防性行動變得無關緊要。他在向麥喬治·邦迪匯報時說,“如果我對約翰遜的報告理解正確”,北京將會“很慎重”,“我們就沒有必要”攻擊中國的核設施。
科默對預防性行動的懷疑,并不足以阻止中情局和國防部正在進行的計劃。1963年秋天,羅斯特要求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準備一份對中國核設施采取直接行動的報告。羅伯特·約翰遜受命主持這一研究課題,研究人員來自中情局和國防部。
不久,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繼任。新總統認識到需要一個更靈活的對華政策,但也很矛盾。他上任幾個星期后與參議員里查德·羅素進行電話交談時稱,“沒有疑問”美國遲早不得不承認中國。羅素認為在當時進行這樣的談話,等于施放“政治毒藥”。強大的臺灣游說集團無疑影響總統的考慮,但他也受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的煩擾,認為中國是對美國在太平洋的力量的重大威脅。
在林登·約翰遜對中國核設施做出決定前幾個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羅伯特·科默仍認為沒有必要作出過度的反應。然而,科默的頂頭上司、國家安全助理邦迪贊成“對中國進行預防性攻擊”,希望做更多的準備工作。但總統有自己的想法。約翰遜與肯尼迪不同,他沒有對中國的核武器計劃作公開的評論,更少談論采取“措施”,攻擊中國的核設施。
1964年4月中旬,羅伯特·約翰遜完成了《對中國核設施采取行動的可行性的探討》的報告。由于高度敏感性,這一研究報告被標為“絕密”,至今仍未解密。但該報告的一部分內容出現在國務院的《外交關系》系列中。幸運的是,由約翰遜自己撰寫的一些報告已解密,這些報告總結了這一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
羅伯特·約翰遜確定了四種攻擊方式:一是美國公開實施非核空中攻擊;二是國民黨軍隊實施空中攻擊;三是利用大陸內的特務進行秘密攻擊;四是空投國民黨部隊實施顛覆活動。約翰遜認為,美國空中打擊是有問題的,因為需要多梯次攻擊才能徹底摧毀目標。利用大陸境內的特務實施地面攻擊,不切實際,因為得不到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而國民黨軍隊沒有能力自己進行空中打擊,美國又不能完全掩蓋其對國民黨的支援。如果空投100名國民黨部隊,他們可以對中國的核設施造成重大破壞,但不會徹底摧毀中國的核設施。
約翰遜寫道,預防性軍事行動有顯著的軍事優勢,可摧毀中國的核設施,從而立即去除刺激印度發展核武器的因素和阻止日本發展核武器。而且中國將失去政治、心理和國防上的優勢。
羅伯特·約翰遜還指出了采取激烈行動的負面因素。首先,由于美國情報機構獲得的中共核武器計劃的情報不全,美國可能還沒有確定所有與核相關的目標。第二,攻擊只能贏得一些時間,也許是3年或者是5年。因為北京決心獲得核威懾能力,中國會重新恢復核計劃,可能會建地下設施,并加強空防,以阻止另一次攻擊。第三,不能排除中國對臺灣或美國在東亞基地進行報復。最后,對中國進行無緣無故的攻擊將要付出沉重的外交代價。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將批評美國“不愿意接受共產黨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主要角色的存在”。一些人會說,美國的攻擊行動與試圖淡化中國核能力的重要性相矛盾。還有一些人會攻擊美國,認為單獨將中國列出來是種族歧視,或將“加速戰爭爆發的嚴重危險”。
一個能贏得國際社會接受的行動方案是,要達成一項全世界范圍內的軍備控制協議,如不擴散條約或終止核材料生產條約。一旦談判達成這樣的條約,如果中國公開藐視這些條約,國際輿論可能就會接受對中國采取的行動。但如果通過談判達成這些條約,中國可能已經試驗了核武器,這些條約對中國就沒有任何影響力。法國也不大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這樣蘇聯也不會支持單獨將中國列出來的行動。約翰遜認為蘇聯“非常不可能”默認美國對中國采取行動。
約翰遜認為,如果中國公開干預老撾或越南的內部戰爭,世界輿論更有可能接受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問題是,徹底摧毀已知的中國腹地的核設施將需要大規模的轟炸機攻擊。中國或蘇聯可能將“有限的戰爭行動”視作是對大陸大規模攻擊的開始,因此,“不能排除報復的可能性”。
約翰遜贊同采取秘密行動,這樣中國掌握不住美國的把柄。國民黨顛覆部隊可以破壞包頭的核設施,但如需要對蘭州或其他地方的核設施采取行動,問題就更復雜了。“同時進行攻擊是必要的,但很難操作”。而且,中國對臺灣的報復將會使美國處于“非常困難的國際處境”。總而言之,約翰遜建議保留秘密行動方式,以待中國公開進行侵略時,美國轟炸機攻擊中國核設施將不會卷入太大的風險中。
羅伯特·約翰遜的分析與肯尼迪總統1963年的考慮截然不同。約翰遜認為,對中國的核武器計劃采取預防性攻擊是危險的,而且有可能失敗,還會損害美國的形象,削弱美國的聲譽。
1964年4月20日,在該報告被送交到白宮前幾天,國家安全助理邦迪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邁克爾·福雷斯特爾告訴同仁說,他們對羅伯特·約翰遜關于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影響的論述十分不滿。邦迪和福雷斯特爾認為,中國的核能力“將產生重大的政治后果”,而該報告卻嚴重淡化了其后果。邦迪傾向于對中國實施預防性行動,認為羅伯特·約翰遜對軍事攻擊的分析不夠積極。為了確保讓總統看到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的分析,臘斯克將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進行了高度濃縮,并在4月底送給總統。
當美國政府內部仍在繼續爭論如何對待中國發展核武器時,中國在1964年的前8個月繼續穩步地實施核計劃。錯誤的情報使羅伯特·約翰遜得出蘭州的設施“尚未完工和可能不會完工”的結論,但實際上蘭州的核設施已經制造出高濃縮鈾。4月,酒泉的核設施已經制造出用于第一枚原子彈的核部件。6月,九院成功進行了模擬爆炸試驗。8月19日,酒泉的工人開始組裝中國第一次原子彈試驗的爆炸物。
(本文責任編輯:季仰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