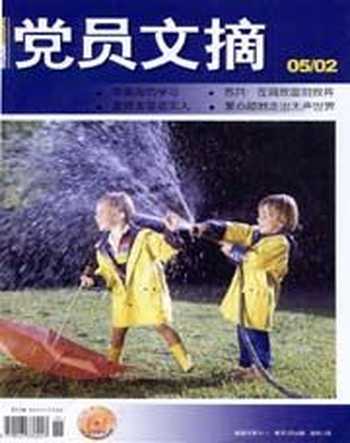蘇州GDP神話下的陰影
韓燕明 徐心如
中國創造了GDP增長的奇跡,蘇州更是奇跡中的奇跡。2004年上半年達18%,而且在未來幾年仍將會狂飆突進,但這樣的發展模式能為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帶來多少促進,卻要打上一個大問號。
2004年上半年,蘇州各項經濟指標又向前邁了一大步:GDP總量增長18%,緊跟在上海、北京、廣州這些傳統意義上的特大型城市之后,在全國大中城市GDP總量中排名第四。
對于只有590萬人口的一個地級城市而言,蘇州的經濟規模是一個奇跡。
“這樣的發展速度還看不到減緩的勢頭。”蘇州市政府官員說。由于近兩年上千億元的生產性投入,這些資金都將在未來幾年轉化為GDP數字,因此蘇州GDP高速增長的勢頭還將持續,并可能在2008年前超越北京、廣州,成為僅次于上海的經濟“巨無霸”城市。
但在蘇州GDP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以外資投入為主體的發展模式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給耀眼的經濟光環上投下陰影。
GDP增長與人均收入不對稱
2003年末,蘇州GDP總量為2802億元,人均高達4.75萬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23美元,高出一直領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為全國各大中城市中的狀元。
但蘇州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卻并不如此樂觀。按人均收入計算,蘇州只能排在長三角16個大中城市的第七位。蘇州就業群體的工資收入普遍偏低,大學本科畢業生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大專生、技校生收入在1000元左右,來自附近省市農村的外來打工族收入則只有幾百元。
隨著近幾年房價狂漲,普通就業群體的生存壓力日益增大。從南京大學畢業后在蘇州一家外資企業打工的張彬抱怨,自己辛苦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半個平方米的住房,他甚至說,自己是“住在天堂,活在地獄”。
有專家將蘇州和成都兩座東西部城市的統計年報作了比較后發現,除GDP、進出口總額等數字蘇州大大超過成都外,在許多有關居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上,處于東部最發達地區的蘇州,還比不上地處西部內陸的成都。比如體現老百姓消費水準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成都是771.5億元,蘇州是526.1億元;在體現當地居民富裕程度的城鄉居民儲蓄余額上,成都是1494.4億元,蘇州是1470.5億元;人均住房面積,成都是27.1平方米,蘇州為18.6平方米;私家車擁有量,2003年成都私人擁有汽車34.5萬輛,蘇州是16.8萬輛。
是世界工廠,還是其加工車間?
2003年底,蘇州全年合同引進外資124.96億美元,實際引進外資68.05億美元,均居全國首位,占全國引進外資額的十分之一。在蘇州經濟中,外資已經成為發展主力。
在蘇州新加坡開發園區的示范帶動下,蘇州掀起了一陣園區經濟熱潮:全蘇州境內先后冒出16個國家級、省級開發區,以及星羅棋布、不計其數的縣級、鎮級、村級開發區。有一個在蘇州當地流傳很廣的說法:在深圳,一個椰子掉下來會砸到四個總經理;而在蘇州,往四周一指,每一處都是開發區。
有媒體報道稱,蘇州已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集中的地區,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在世界工廠名稱下面隱藏著的卻是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實質:由內地提供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再加上各類優惠的稅收政策,外資企業將生產過程的低端部分——主要是加工和組裝環節設在當地。這些低端環節的最大特點是:耗費勞動力多、勞動強度大、附加值低。
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是10美元,但其在中國的離岸價格卻只有2美元。這2美元還不是最終利潤——其中的1美元是管理費和運輸費,剩下的1美元中,0.65美元用于支付來料費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國企業主和工人的所得。
瑞士與美國合資的羅技公司在蘇州生產的羅技鼠標,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在這一價格中,羅技拿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進入零部件供應商的腰包,中國從每只鼠標中僅能拿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
目前,蘇州每年外貿進出口高達656.63億美元,且以年均80%的高速遞增。但要將這樣的低端產業鏈條地區稱為世界工廠是錯誤的,稱為世界工廠的加工車間恐怕還差不多。
而且,這樣的車間還像蒙古包一樣“逐水草而居”——哪里的政策更優惠,哪里的土地、勞動力更廉價,就往哪里搬遷。在蘇州目前引進的外資中,就不乏一些在珠三角“免二減三”政策到期后的企業。他們轉移到蘇州后,又可以繼續享受蘇州方面提供的稅收減免優惠。蘇州當地的一位官員說,等蘇州提供的減免優惠到期之后,這些“蒙古包”企業向其他地方轉移,“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角色錯位:政府成了市場主力
“在蘇州辦事,找廠長、經理沒有用,要找局長、找書記。” 一位在蘇州投資的臺商說。
目前,蘇州經濟的主力是外資投入。一家跨國公司到蘇州來設廠,產值動輒就是幾億、幾十億元,經濟指標迅速得到提升,所以各級政府都樂意通過招商引資來獲得政績。
1994年,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蘇州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條件,在蘇州城東合作開發了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隨著該園區招商條件的逐漸成熟,蘇州又在城西如法炮制,開辟了新的工業開發區——蘇州新區,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新加坡方面為此提出抗議,認為蘇州市政府是在挖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墻腳。蘇州市政府回答的理由也非常實在:如果蘇州不開辟新區,那鄰近的吳江、昆山,甚至無錫、常州也肯定會用更加優惠的招商引資手段來吸引外資。最后的結果是,新加坡方面只能承認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
沿著幾條穿越蘇州境內的主要公路干道,兩旁到處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和已經建成的廠房,難得一見連片農田。那個我們記憶中熟悉的河道縱橫、沃野千里的江南水鄉,在蘇南地區工業化的急行軍中,已經離我們遠去。
據一份統計報告稱,蘇州的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消耗掉4000畝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長速度下,蘇州的耕地每年以近10萬畝的速度在消失。2003年,蘇州GDP增長了18%,而糧食產量下降了23%,油料作物下降了20%,蠶繭下降了40%。
蘇州各個市縣、各個鄉鎮為在招商引資上完成更多的指標,不惜在地價、稅收政策上血拼。一畝“七通一平”后的工業用地,土地成本至少在15萬元以上,但在蘇州很多縣市,外商花5萬元就能拿到。一些外商說,他們也常常搞不懂一些優惠政策從何而來。
政府主導下的蘇州經濟,雖然取得了GDP高速增長的奇跡,但其運作方式卻是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背離的。在政府唱主角的市場中,招商引資成為最省力、最易見成效的捷徑,而發展本土型的創新型企業則成為費工費時、吃力不討好的事。
可以預料的是,由于近幾年外資的大量涌入,蘇州GDP在未來幾年仍將會是狂飆突進式的發展,但這樣的發展模式究竟能為中國經濟地位、經濟實力的提升帶來多少促進,對中國從一個制造業大國向一個制造業強國轉變提供多少幫助,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