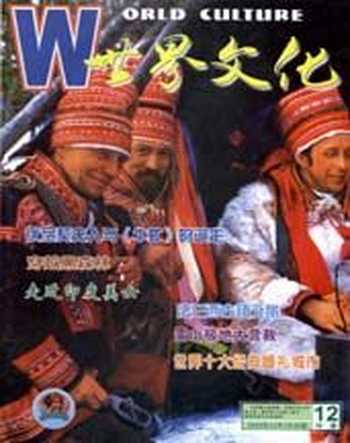文化的沖突 血脈的融合
龔莉紅
從第一批華人抵達美洲大陸開始,他們就把文明古國的歷史、文化、思維方式也帶到了這個嶄新的國度。華裔們從來沒有停止用自己的筆端來表達對這個國度的思考,特別是華裔女性作家,她們的文學創作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同。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最早且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代女作家是黃玉雪,她的《華女阿五》(1945年)在美國最先得到承認,她本人也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東南亞做巡回演講。第二階段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湯婷婷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的《女勇士》(1976年)和《中國佬》(1980年)都獲得過國家圖書評論界獎,后者還獲得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提名。而第三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現在,譚恩美無疑是其中最閃亮的新星,她的《喜福會》(1989年)獲得國家圖書評論界獎、1991年最佳小說獎等,而她的第二本小說《灶神之妻》(1991年)一經問世,就成為美國最暢銷的小說之一。
這些華裔女作家大多從家庭事件中尋找素材,最后提升到兩種異質文化的沖突和融合。譚恩美從中美兩國文化沖突和隔閡縫隙中看到女性的掙扎和母女間從隔閡到融合。她在第二部小說《灶神之妻》中以自己第一代華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將在大陸有著坎坷經歷的中國母親和在美國有著文化困惑的美國女兒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描寫得淋漓盡致。
《灶神之妻》以女兒珍珠作為主要的敘事主角,她向母親隱瞞了自己患有多發性硬化癥的病情,而母親也向女兒隱瞞了她在中國和第一個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經歷,以及第二任丈夫美國人吉米·路易幫助她擺脫在中國的痛苦折磨來到美國的經歷。母親仍然是中國式的,而女兒卻是完全的美國化,兩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著很深的隔閡。這種文化的糾紛和沖突主題,不單單是在譚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別的體現,它幾乎是一個母題,在許多海外華文文學中反復吟唱,同時在海外游子心中縈繞。
中華倫理和西方價值觀的沖突
中國儒家文化中,強調“三綱五常”、“三從四德”,要求中國女性“未嫁從父”、“嫁后從夫”、“夫死從子”。《灶神之妻》中的母親江雯麗在書中卻沒有尊崇“三從四德”。江雯麗出生在20世紀初上海的一個富商之家,由于母親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她被父親一怒之下扔到崇明的叔叔家,從小就沒有“未嫁從父”。長大嫁人后,她的丈夫是個心胸狹窄、自私小氣的施暴者,雖然是個飛行員,但是沒有文化,對她百般凌辱。他在外吃喝嫖賭,在家不顧親生女兒的死活。江雯麗忍無可忍,決意離婚,他們來到上海時,她曾幻想依靠父親的權勢來擺脫與文福的婚姻。可當了漢奸、破了產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國民黨當過兵的女婿的支撐。她只好再次忍氣吞聲,直到父親死后,才得到一個愛她的美國人吉米·路易的幫助,到了美國。母親在中國的婚姻中,也沒有“嫁后從夫”。來到美國,丈夫死后,她也沒有依靠任何一個子女,自己開花店,自給自足。母親夫死后也沒有“從子”。
母親江雯麗雖然不是一個自覺地反抗封建倫理綱常的女子,但是她所作的一切符合美國自由、平等和民主價值觀。“天賦人權”也是母親最終享受到的。中國的封建倫理在美國這塊土地上,得到了徹底的解脫。這樣的故事情節讓強調“自助者天助”的美國讀者擁有了強烈的閱讀期待。
在兩種價值觀念的沖突中,母親最終選擇了西方的價值體系。同時,作者又安排了美國人吉米·路易給予母親無私的愛和幫助。吉米是西方的男性,他體魄魁梧而且彬彬有禮,崇尚自由、平等、民主。而母親是東方的女性,美麗聰慧卻被暴虐的東方丈夫統治,缺乏愛情和安全感。母親通過吉米的愛情和移民幫助逃離父權統治的行徑,最終被東方主義理解為西方解放了東方。東方主義認為:東方總是代表落后原始、神秘、奇特多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則是理性、進步、科學、文明多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紀初,西方的文明終于將東方文明發現并解救出來。譚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東方。
母女的文化沖突和隔膜
“母愛女孝是父子倫理的變體,是傳統文化中儒家家庭倫理觀最重要的屬性之一。華裔作家也擅長通過母愛女孝倫理的體現來反思傳統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國人的,并以此反映新舊文化與中西文化的差異。”譚恩美的成名作《喜福會》中,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寫出了在東西方文化背景中,母女之間關系怎樣由隔閡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部同樣暢銷的小說中,她依然通過第一代移民的中國母親和本土生長的美國女兒之間的關系來反思不同文化帶給人們的快樂和憂傷。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寫東西方之間的倫理價值觀有著沖突以外,作為血緣關系的母女也在兩種文化的熔爐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家庭”既代表著家長對子女的權力,又意味著子女對其依賴關系。“血緣關系”伴隨著“孝道”的產生,所謂“百善孝為先”。但是在女兒珍珠14歲“充滿了憤世嫉俗的怒火”的時刻,她做了讓母親很難原諒的事情。女兒拒絕悼念瀕臨死亡的父親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這個人,這個病人已經瘦得不像樣子,他呻吟著,衰弱無力,直到臨終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親。他與我的父親一點也不像,我的父親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強壯、仁慈,總是慷慨大度,笑聲不斷。”“我怒氣沖沖,滿臉淚痕地跑上哥倫布大街,一直跑到海灣,也不管那些怔怔盯著我的游人。結果,我錯過了葬禮。”為了這件事情,女兒和母親關系一直很緊張。正如文中所說:“我們兩個都贏了,也都輸了。”
結婚后,女兒看望母親也只是像例行公事而已,珍珠在從母親的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望著窗外急馳而過的風景:水庫,起伏不平的小山坡,還有我路過上百次的同樣的房子,從來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這距離橫亙在我和我母親之間,把我們分開了。”這中間的距離就是文化的差異和隔閡。雖然女兒珍珠有著中國人的臉,但是她自小長在美國,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止都是美國式的,她主張父母與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對子女沒有絕對的權威。而母親對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國式的,需要嚴格地服從和遵守,一旦女兒反抗,母親便覺得觸犯了中國的“忠孝”觀念,更不用說不看一眼瀕臨死亡的父親吉米了,那在中國簡直是大逆不道,是不可饒恕的罪過。她不知道,女兒其實也是愛父親的,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罷了。
血脈的融合消弭了隔閡
中國有一句古話:“血濃于水”。的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更迭中,宗族主義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沖突和隔閡中,血緣關系對于移居在他鄉的華裔來說,也是最好的黏合劑。雖然中國只是存在于女兒珍珠幾乎模糊的記憶中,但是畢竟自己中國人的外貌和族群認同心理是不能磨滅的;雖然美國是她現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國”是更具有象征性的、具體無意識的“家園”。
無論文化如何的產生隔閡,總是有最無法割舍的血脈維系著母女的關系。母親終于在整理房間的時候,看見了意想不到的東西。她發現女兒將父親的逝世日期記在一張卡片上,同時上面蓋著黑紗。當時,母親想到:“只有在這時我才想到我錯了。我想馬上就給阿珍(即女兒)打電話,告訴她,現在我才知道,你傷心過,你哭過,不是在臉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愛你爸爸。”母親立刻理解了女兒當時因為憤怒和絕望而沒有與垂死的父親告別的心情。女兒沒有從行動上安慰父親,但是在心中卻一直深深地緬懷著他。
女兒則通過母親的敘述進行了一次文化尋根,和母親一起追憶了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母親經歷了怎樣的滄桑生活和情感糾葛后才更了解母親的。通過這次文化尋根和精神砥礪,女兒自覺尋找和確認自我在現實與精神上的歸屬。尋根這個主題,作者在前一本書《喜福會》上已經通過四對母女的故事闡釋過,《灶神之妻》繼續通過“母親和女兒”這條生命鏈來追溯。譚恩美的文藝理論觀跳出了“美國敘事”或“中國記憶”單一的思維模式,她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場上,熔鑄和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華裔文學《灶神之妻》。
母親的愛和關懷通過血脈源源不斷地滲透到女兒的身上,女兒最終也沐浴于母愛或者說是中國特有的家庭血緣凝聚力中。女兒珍珠愿意用中草藥來治療多發性硬化癥,母親也送給女兒一個含有寓意的女菩薩“莫愁”,她希望中國的菩薩“莫愁”保佑美國長大的女兒珍珠。這次文化尋根意義的談話,終于讓中國血脈的融合消弭了文化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