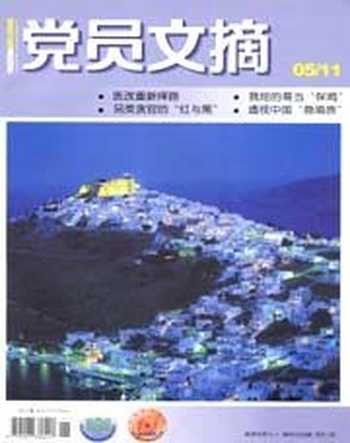透視中國“隱婚族”
羅雪揮 曹紅蓓
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所謂的“終身大事”只有一件,就是結婚。而近年來,完全有能力張揚卻對結婚低調處理者越來越多。其中一些人,對自己的婚訊要么矢口否認,要么秘而不宣。
這些被稱為“隱婚族”的人,前腳邁進了婚姻的門檻,后腳仍停留在單身生活里。
“你要讓人覺得你是‘可得的”
“你覺得亮出已婚身份最常遇到的麻煩是什么?”在《中國新聞周刊》和新浪網聯合進行的“隱婚調查”中,一半以上的人如此回答:異性對自己失去興趣。
余琥(化名)今年30出頭,是一家網站的頻道主編。在余琥的女性同事看來,他對女孩子特別好:他會很自然地夸你皮膚漂亮;一道上下車的時候給你拉車門;過生日送你禮物;你下午無意間說出想吃火鍋,他晚上就會請你到火鍋店。一位曾經感受過余琥的這種好的女孩說:“他總讓人覺得,他是不是在追我啊,可又絕無言語表達,也沒有什么明顯的肢體暗示。”
余琥經常和女孩單獨出去吃飯,或一起出去玩。只是到了周末晚上,他總是說:“我還有點事,先走了。”常有人問他:“你條件這么好,怎么會沒有女朋友啊?”他樂呵呵地答:“就是沒有啊,有合適的給我想著點。”但假如你真的給他介紹對象,他就會以各種借口推辭。
余琥所在的部門里,有不少人愛看影碟。有時候他們會把賣碟的叫進辦公室,每到這時,另外部門的一個女孩子就會過來,跟余琥他們一塊選碟。選完了,余琥半真半假地說:“算了,我都一塊兒付了吧。”那女孩就說聲“謝謝”。
“后來當我知道那女孩就是他老婆的時候,驚訝死了!”一個輾轉得悉了余琥秘密的同事說。
“余琥有個‘理論:你要讓人覺得你是‘可得的,你周圍的環境就會特別好。”在這位同事看來,余琥的“可得的理論”,似乎可以使他在婚后繼續保持一種“較有活力的異性環境”,但他的那些舉動,放在已婚的背景下,就顯得有些不自然了。
“單身”派對
“很新鮮,坦率地說也很興奮,但還有一點不安,畢竟不是自由身。”林蕙(化名)回憶自己半年前參加過的一場單身Party,仍然興致勃勃。她是受朋友所托,暗中去做市場調查的,因為朋友的公司也想開展類似的項目。
盡管林蕙已經是6歲孩子的母親,但模樣秀麗清純,一到單身Party就成了熱門人物。盡管牢記著自己的工作目的,林蕙還是在異性傾慕的眼神中感到了莫名的驕傲和欣喜。而令她詫異的是,她發現在這個為單身交友而舉辦的Party上,還有不少明顯感覺是已婚的男士。和真單身比起來,他們口齒流利,可是身上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曖昧,想要接觸卻又畏首畏尾,隨時留著退路。
“當然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已婚,在這種單身Party上,大家百分百不會說實話。”林蕙說。活動剛剛結束,就有很多電話打來,希望接著約會。當著丈夫的面,林蕙不得不一遍遍告知對方自己已婚。
林蕙對這次參加單身Party的經歷始終念念不忘,甚至向閨中好友們推薦,在婚姻走入平淡時,不妨再扮一回單身,不為出軌,只為那份久違了的被異性關愛、仰慕的感覺。
“偽單身”:我一個人住
29歲的張纖(化名)和先生處于分居狀態,尚未去辦理離婚手續。
因為自己是假扮單身,張纖對對方的單身信息也分外謹慎。張纖說,現在“偽單身”防不勝防,大部分人都不戴結婚戒指,鮮有人隨身帶著老婆孩子的照片,而除非婚姻關系特別融洽的人會時不時在同事前提起“另一半”,如果感情一般,往往保持緘默。想在他的熟人那里求證他已婚與否越來越困難,只能憑經驗分辨。
張纖認為,特別要提防那些太太出國的留守男士,以及長期出差或者由外地公司長期派駐本地的人。他們一般不會主動表白婚姻狀況,而是會有意無意透露一些單身的信息,比如一個人住,一個人煮飯,周末去玩的都是客戶和同事,從來不提家人,仿佛身邊沒有女人的影子。而這些小把戲,對張纖來說容易引起警惕,她會再三試探,以確保自己碰見的是真單身,免得浪費時間和感情。
“隱婚隱去的是婚姻的神圣性”
臨床心理學家、被稱為“愛情博士”的黃維仁認為,“隱婚現象,其實說明婚姻中有些情感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就婚姻的主流而言,隱婚還是個別現象。”婚戀問題專家陳非子說。他發現,再婚過程中隱婚的相對更多,“再婚男女往往很謹慎,害怕萬一又變了,不好交待”。除了再婚隱婚,因為一時對婚姻狀態不適而隱婚、純粹因為不想透露個人信息而隱婚、為繼續保持異性環境而隱婚和工作中的隱婚,在隱婚中都有很大比例。
比較已婚者,陳非子說:“單身始終會帶來一些優勢。”單身帶來的就是自由,交友機會多,選擇機會多,相應的工作機會多,這在當今社會更為明顯。如是,在充滿了誘惑與可能的情況下,隱婚尤易滋生。
此外,工作中的隱婚很多還有相當實際的原因,如有單位規定員工內部不得談戀愛;又如,一些單位規定,單身外地員工的探親假一年一次,而已婚外地員工的探親假就變成四年一次。在這種情況下,隱婚與其說是為了前途,不如說是為了福利。
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婚姻史專家鄧志偉看來,中國社會目前的“松散、沙化”,從許多方面給隱婚制造著條件:取消福利分房,取締強制性婚檢,結婚不用單位出證明,工作者跳槽頻繁,人們結不結婚,和單位似乎再沒什么關系。城市中人們打破了單位的界限分散居住,加之鄰里關系的疏離,人的家庭私秘性大大增強。
心理學者周振基將人們對婚戀態度的變化也列入促使隱婚增加的因素。周振基認為,現在人們普遍晚婚,不像以前,從年齡就可以看出結沒結婚。另外,對婚前同居的默認更使得人們無法輕易判斷出一個有性伴侶者究竟有沒有結婚。
論及過去人們對婚姻的張揚,周振基提到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在當時的社會,婚姻在人的心理上具有成功、滿足、炫耀的作用;今天,社會對一個人成功的認同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是否娶妻生子等生活層面,而逐漸擴展到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多重標準。這些成功標準的變化尤其體現在男性身上,而大多數女性對婚姻狀況仍然相對張揚。
隱婚現象的出現,不僅是個人對自己婚姻的重視程度降低的體現,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外在因素重視程度的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中國人而言,如何堅持婚姻的神圣性,確實是個考驗。
(摘自《世界報》 原標題為《偽單身》 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