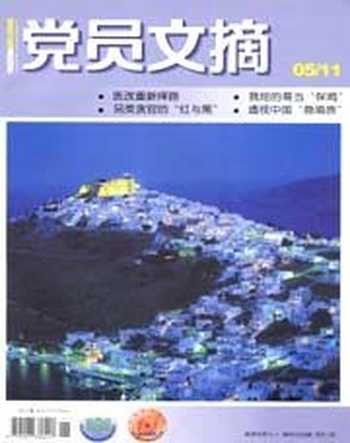“弱校”困境
劉 冰 一 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以下簡稱烏市)小學6年級學生王青(化名)的母親最近接到了一個令她欣喜萬分的電話。來電人稱,她代表本市一所知名中學邀請王青去該校讀初中,并承諾免交跨區費,其他費用與學區內學生一樣。此后一周內,王青的父母又分別接到另兩所知名中學同樣的邀請電話。
看著周圍其他家長因為孩子擇校的事整天忙碌和發愁,王青的父母感到極為驕傲:小學6年,王青每學期的考試成績都保持在全年級前3名內,各種獲獎證書有一大摞。
直到現在,王青的父母也不清楚這幾所學校是怎么知道他們家的電話號碼的。
名校:人心所向優生薈萃
聽到烏市某初中名校分校“小升初”開始招生的消息,高兵一大早就帶著孩子的資料等在了校門口。在校門打開之前,已擠滿了和高兵有著同樣目的的家長,他們相互交流著今年烏市初中名校的報名條件、收費情況和考試時間。這種盛況在其他幾所名校同樣上演著。
高兵是烏魯木齊縣安寧渠鎮人,1997年來到烏市,從推著板車叫賣水果,發展到現在已擁有幾家水果、鮮花專賣店。因為忙生意,高兵的兒子一直在安寧渠由他的父母帶著。為了孩子將來能上烏市最好的中學,高兵3年前給孩子買了烏市戶口,1年前在烏市某初中名校的學區范圍內花十幾萬元買了1套7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就高兵所知,在這個小區買房的,50%以上都是為了孩子。
在該校分校招生的第一天,前來咨詢、填表的家長絡繹不絕,招生報名表、獲獎證書復印件已摞成厚厚的兩沓。招生老師手里拿著數份區屬各小學不同名目的參賽成績單和獲獎名單,以此審驗家長提供的獲獎證書。
招生老師告知,該校校本部今年初一計劃招8個班,生源均為學區內的,這些學生的費用按國家規定收取;與一所私立學校合辦的分校計劃招6個班,每個班56人,生源均為學區外、在小學期間獲過學科競賽自治區級一、二、三等獎的。其中,一等獎獲得者初中每學期交跨區費900元,其他費用按國家規定執行;二、三等獎獲得者3年交1.5萬元,一次性交清。
“弱校”:人才凋零前途未卜
前不久,烏市某報登出一篇有關呼喚教育公正的文章。其中寫道:“某區屬中學2004年按區劃分來的初一新生有300多人,預計可開6個班,可等到提學籍卡時才發現有150多名新生的學籍卡神奇失蹤,原來都是被某些‘名校提前抽走了。該校作過統計,凡是在小學各項競賽中獲獎的學生,在小學擔任過班干部、課代表的學生都已被‘一網打盡。到開學時,只有90多人報到……”
文中提到的中學在當地是學生和家長心目中的“弱校”。該校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校小學部去年有4個班的畢業生近200人,到9月開學時,來該校中學部報到的只有四五十人,而且其中大多數學生成績較差,有的畢業考試語文、數學兩門都不及格。
“我校的尖子生是被某些名校打電話邀走的,而且以保證不收取額外費用為條件。更多的學生被通知參加其他學校的入學考試,近60名學生連學籍卡也不要就一去不返了。”這位工作人員無奈地說。據說學生放棄了學籍卡,可在新的學校重新獲得。
“弱校” 師生一聲嘆息
市場化的社會大環境決定了學校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誰能爭取到更多優秀學生,就意味著誰擁有較高的升學率,較高的社會認知度,豐厚的經濟利益。所以,學校間互挖墻腳的做法每學期都在進行著。
這些學校是如何掌握各小學優秀生的聯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的?一位教育界人士分析:一是由名校老師通過在“弱校”工作的大學同學或其他關系弄到;二是由名校老師到各小學暗訪得來;三是各區教育局為了將本區內的名校培養成市級、自治區級重點中學,有意而為之。
一些在“弱校”任教的老師認為,人往高處走無可厚非,但名校利用非正常手段對“弱校”進行“掠奪”,讓他們感到寒心。“弱校”學生的基礎薄弱,培養一個好學生,老師要付出比名校老師多得多的心血和精力,結果卻是培養出一個被挖走一個,這對老師積極性的打擊是巨大的。
而在“弱校”,更多的學生則抱著自暴自棄的態度混日子。在一所剛剛開學的“弱校”,陽光下,一大群半大男孩子自發舉行的籃球賽正激烈地進行著。這群男孩來自該校不同年級不同班級。上午的最后兩節課他們都沒去上,這對他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其中球技頗高的一個穿著黃衣白褲的男生名叫易陽,是該校的“逃學大王”。
易陽被分到這所“弱校”以來,就不斷和家長鬧別扭,認為是家長沒本事。于是,他的父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四處托關系,在初二開學時終于將易陽轉到一所好一些的學校。易陽決心在新學校好好學習。盡管很努力,他的排名始終處于中下游,一個學期后,再沒有一個班愿意接收他,他只好又回到了原校。但在原校想學習的人太少了,哥們兒總拉著他逃課打籃球。易陽覺得回到原校就等于什么前途也沒了,再學也沒用,努力學習的勁頭徹底消失了。
“弱校” 惡性循環何時休
這些“弱校”都有一些叫老師頭疼不已的學生。他們既不聽課也不老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破壞課堂紀律,和老師對著干,還時時強調他有受教育的權利。開家長會,連一半的家長都到不齊,更別說平時主動與老師溝通了。老師拿的都是“死”工資,沒有什么福利,出了校門都不好意思提自己是該校的老師。學校教職員工的子女沒有一個在本校上學。
老師們說,每堂課的1/3時間要用于維持紀律,即使付出多于名校老師百倍的心血也換不來名校的成績;他們一半精力得放在對差生的說服教育上,投入到教學上的精力就很有限了,這極大地影響了業務能力的提高。年輕老師為此憂心忡忡——同年畢業的同學,因為所處教學環境不同、培訓機會不同,幾年后,業務能力、收入水平、社會認知度的差距明顯拉大。如果學生過少,老師還有下崗的可能。年輕、有能力的老師想盡辦法往好學校“跳”,能靜下心來鉆研業務的老師不多。
這些學校的學生普遍自卑。有些學生主動和在好學校上學的親戚疏遠,盡量不來往;學習好的學生一個個考走了,從“好學校”淘汰下來的則來到這里。
針對“弱校”一步步陷入窘境,一位中學老師認為,凡事都是外因與內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學校辦不好,有歷史、社會以及家庭的原因,但也要認真總結一下自身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學校由差變好的例子不是沒有,就是烏市的名校中,有的在若干年前也還是普通中學,人家為什么就能做強,做出名牌來?
一位教育界人士對此既無奈又擔憂:如果把差生、問題學生都集中到一些學校,結果就是這些學校辦不下去。他建議,教育主管部門要從長遠著眼,應以行政的強制手段有所作為。
(摘自《中國青年報》 本刊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