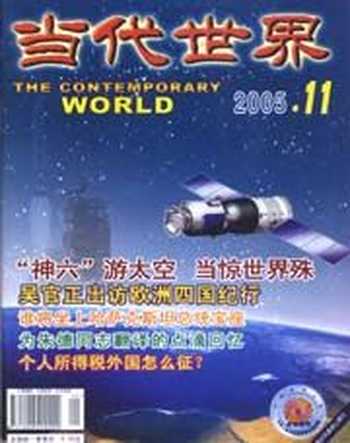大國關系與中國因素
蘇祖輝
今年以來,大國關系總體上仍保持平穩態勢,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調整。自“9·11”以來,以反恐為粘合劑的大國合作向傳統大國關系回擺,地緣政治和多邊政治因素成為大國互動的著力點。美國因素依然是大國互動的重要牽動力,同時中國因素日益成為大國關注的重點。
美國因素:牽動大國關系新一輪互動
(一)美國對外戰略調整初現端倪,遏制大國崛起需求上升。經過三年多的反恐斗爭,雖然美國在伊拉克仍然焦頭爛額,但它認為,從總體上來看恐怖主義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恐怖主義對美國安全的威脅有所下降。這使得美國一直以來為了推進反恐戰略而有求于其他大國合作的動力開始減弱。反恐、防擴散雖然仍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目標,但近一段時期以來,美國國內在反恐問題上出現一定分歧,顯示出美國外交戰略開始醞釀調整。而從美國今年以來的實際動作來看,美國明顯加大了對大國崛起帶來的潛在挑戰的關注。美國外交戰略的調整使“9·11”事件后,以反恐為粘合劑的大國關系向傳統大國關系回擺,地緣政治因素在大國互動中的影響和作用再度上升。美國在繼續推進“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滲透,以擠壓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此外,美國還加大了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戰略投入,調整亞太軍事部署,深化美日軍事同盟,大搞平衡和均勢戰略,以保持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權。
(二)美國豐富對外戰略手段,牽動其他大國積極回應。布什連任后,美國的外交戰略手段日益豐富,實用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同時加重。美國軟硬兩手并舉,將運用軍事力量和擴展民主相結合,更加重視輸出所謂“民主自由”。此外,美國對其單邊主義政策進行調整,注重修補盟友關系和借重多邊舞臺,以尋求合作和認同,在世界范圍內恢復和擴展“軟實力”。美國的一系列調整引發了其他大國的積極回應。鑒于美國無可匹敵的實力,其他大國為爭取主動,謀求自身利益,極力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對抗。歐盟在經濟、政治和安全等諸多領域仍無法完全脫離美國,而且歐盟內患重重,憲法危機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嚴重受挫。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歐盟將更多集中于化解內部矛盾,政治一體化進程將趨緩,其“政治矮子”的形象短期內無法改變,對美國的牽制力也將有所減弱。以上諸多因素使歐盟沒有理由拒絕美國釋放出的主動修補關系的“善意”,歐盟在伊朗核問題、巴以問題上加強了與美國的配合,尤其是在伊朗核問題上,歐盟更是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俄羅斯雖然不斷遭到美國的地緣擠壓,但囿于自身實力,維持與美國關系的總體穩定仍然是其政策基調。日本對美國的需求也在上升,試圖“傍美自重”,尋求美國對其政治大國夢想的支持,因而主動迎合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
地緣和多邊政治因素:
大國戰略互動的著力點
(一)中東、中亞以及亞太成為大國互動的地緣戰略重點。美俄在獨聯體地區的爭奪呈加劇之勢。為進一步擠壓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美國繼續在獨聯體地區策動“顏色革命”。以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為開端,美國將觸角逐步伸向與俄羅斯關系密切的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國。為抵御美式民主的滲透,緩解地緣戰略壓力,俄羅斯加大了經營獨聯體的力度。但獨聯體建設仍面臨重重困難,有日漸式微的危險,美攻俄守的態勢短期內無法逆轉。俄羅斯還加快了與歐盟的合作步伐,推進俄歐“統一空間”計劃,并積極推動中印俄三邊協作。美俄在中東地區也暗中角力。俄羅斯不顧美國的反對,與伊朗簽署核燃料供應和廢料回收協議,并與敘利亞達成出售防空導彈系統協議。美歐關系雖然有所緩和,但深層次分歧依然難以消除。布什連任后,美歐雙方互訪不斷,推動美歐關系回暖。美歐在伊朗核問題上加強協調與合作,但歐盟在中東地區存在重要地緣戰略利益,雙方在解決該問題的方式和目標上的分歧很難調和。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國有意將日本打造為“遠東的英國”,刻意提升美日同盟,加快推進美日軍事一體化。美國支持日本卷入臺灣問題,雙方還首次明確將臺海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給東亞安全形勢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二)聯合國改革問題成為大國角逐的重要戰場。由于聯合國改革尤其是安理會的改革事關世界權力的重新分配和國際秩序的調整,因而成為大國角逐的焦點。各大國出于各自利益考慮,施展各種手段,明爭暗斗,圍繞聯合國改革問題展開了新一輪博弈。日本和德國試圖擠進安理會,實現其政治大國夢想,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也希望利用“入常”進一步增強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影響力。“五常”中的美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四國為維護其既有地位,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都堅守否決權底線,但各懷打算。為推進其全球戰略部署,美國試圖主導聯合國改革進程。隨著聯合國改革的深入,美國的介入也逐步加深,以幾乎全盤推翻首腦峰會成果文件草案的激烈方式,企圖改變改革進程,將之納入自己的軌道。美國在支持日本“入常”問題上也是“口惠而實不至”,引起日本的抱怨。英國和法國對“四國聯盟”表示支持,但總體上對聯合國改革較為超脫。俄羅斯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的實用主義態度較為明顯,力求不得罪任何一方,并試圖利用日本“爭常”與之作交易,為其在日俄領土爭端問題上爭取籌碼。各方在人權、發展等關鍵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導致聯大峰會成果有限,聯合國改革進程放緩。
中國因素:漸成大國關注焦點
(一)各大國對中國的戰略關注日益增加。由于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地區和國際格局的影響日益顯著,各國對華戰略關注持續增加。一方面,中國重視并積極開展大國外交,牽動大國關系的互動。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在地區事務中的重要作用,各國對華借重的心理也在上升。中美在反恐、防擴散等問題上繼續開展合作,美國在聯合國也沒有再提反華人權議案,對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反應也較為克制。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在朝核問題上借重中國的需求將進一步加大。俄羅斯為應對西方的地緣戰略壓力,對中國的態度也趨于積極,雙邊關系有所發展。中俄徹底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俄羅斯還在能源、涉臺等問題上對中國予以配合。俄羅斯在烏克蘭“橙色革命”前后積極促成中俄首次聯合軍演,顯示出加強與中國的戰略合作的決心。歐洲對中國的關注進一步上升,中歐關系繼續發展。雙方經貿合作迅速發展,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在最后時刻達成協議,隨后產生的紡織品壓港危機也本著互諒互讓的雙贏精神得以順利解決。
(二)中國因素對大國互動產生多方影響。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一些大國對中國的防范心理也有所上升,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逐步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進程,中國與其他大國的經貿摩擦增多。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上不斷向中國施壓,中國與美歐在紡織品貿易問題上不時出現爭端。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雖然經過談判已暫告一段落,但中美之間進行了多輪磋商,仍然存在深刻分歧,至今無法達成妥協。由于摻雜著復雜的政治因素,中美經貿關系問題仍將制約中美關系的發展。此外,美國在軍事、經濟和資源等領域對中國的戒心加重。美國國內媒體和包括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中情局局長戈斯在內的一些政要極力鼓吹“中國軍事威脅論”。美國還極力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并對以色列在對華軍售問題上不斷施壓。中日關系總體上保持穩定,但在歷史、領土、東海油氣田的開發等問題上的爭端時有惡化。日本對中國快速發展所持的心態日益失衡,對中國的態度也趨于強硬,在臺海問題上的立場也有向美國靠攏。俄羅斯對中國也存在一定的防范心理,中俄在經貿合作上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歐盟在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問題上與美國最終達成妥協,這一問題仍將繼續困擾中歐關系。此外,歐盟在人權、政治制度等問題上對中國仍然還存在一定的疑慮。
(本文責任編輯:劉萬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