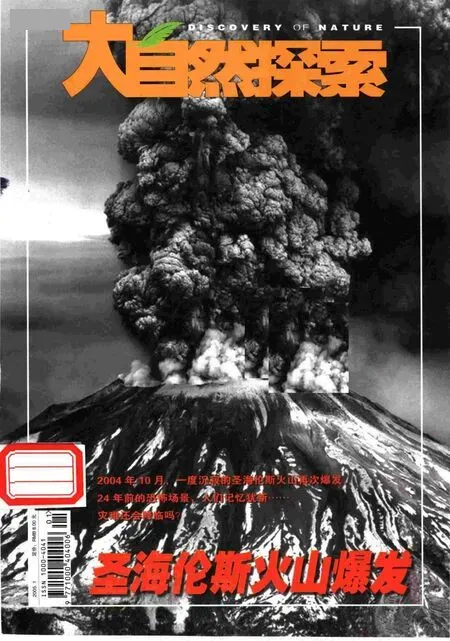時間,打造蘭花成熟之美
編譯楊斧
如果你向一位仍然富有魅力的中老年婦女打聽她保持青春和美麗的秘訣,那么你所得到的可能是蒙娜麗莎式的嫣然一笑和巧妙的所問非所答。迄今,當植物學家探索植物王國中魅力無窮的“女王”——蘭花的奧秘時,也遇到了類似的令人費解的難題。
蘭花家族——蘭科植物,具有比地球上任何植物家族都更豐富的物種:自然形成的種類大約有3萬種,人工培育的雜交品種更達數萬個。多數蘭科植物是附生植物,它們并不扎根于土壤中,而是將根不產生傷害地緊緊附著在熱帶森林上層喬木的樹干或枝杈上。少數蘭科植物是腐生種類,它們缺少葉綠素,靠真菌提供生活所需的營養物質;在澳大利亞,有些屬的蘭花終生在地下生活。除了黑色外,蘭花有各種顏色。蘭花并不都是芳香宜人,它們所散發出的氣味變化很大,從巧克力般的誘人香味到腐肉般的臭味,各種稀奇的怪味都有。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蘭花植物如此驚人的多樣性?是它們極其復雜和異乎尋常的生活方式。蘭科植物與其他有花植物相比,在許多方面差別都很大。看上去蘭花似乎是孤芳自賞,其實它們與許多其他類群的生物(動物、真菌等)有著密切聯系。達爾文曾經寫過一部關于蘭花的書——《蘭花的傳粉》,書中講述了英國本土和國外的蘭花借助于昆蟲傳粉的種種技巧。這本書繼承了他的進化論思想,也是對自然選擇學說的有力證明。然而這已是100多年前的事,而今天借助于諸如“基因順序測定”這類強有力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植物生物學家已經能夠重寫這一具有迷人花朵的植物家族的歷史。
奇特的生存方式
蘭科屬于被子植物中的百合綱,同綱的著名家族——禾本科、百合科等的每一朵花中,雄蕊的數量都是3的倍數,但蘭科植物的花卻十分特殊,通常只有一枚能育的雄蕊,而且這枚雄蕊與雌蕊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被稱為蕊柱的雌雄同體的結構。花粉產生在蕊柱頂部的花藥中。與眾不同的是,蘭花的花粉粒相互之間粘合在一起,形成2—8個花粉團,這些花粉團又共同連在一個被稱為粘盤的具黏性的墊狀物上,這種復雜的結構被稱為花粉塊。在花粉塊的上部有一形如兜帽的藥帽,起到阻止自花傳粉的作用。但花粉塊卻很容易被傳粉昆蟲的身體或蜂鳥的喙帶走。當來訪的傳粉者接觸到花粉塊下部的粘盤時,整個花粉塊就會隨粘盤一起被“俘獲”。通常蘭花的雌蕊位于蕊柱的中下部,接收花粉的柱頭呈穴狀,位于粘盤的下面。當攜帶著花粉塊的傳粉者在兩朵花之間運動時,暴露在空氣中的花粉塊就會很快收縮變形,使其位置和方向正好適合下一朵花的柱頭穴接收。
對于每一朵蘭花來說,花粉塊通常僅有一個,而柱頭穴也僅容得下一個花粉塊,因此這接待傳粉者的惟一一次機會就顯得彌足珍貴。為了確保這一次傳粉的成功,負責吸引傳粉者的花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三枚花瓣中的一枚演變成了唇瓣。它通常是蘭花中最大、最艷麗和最精致的部分,位于蕊柱的前下方,既為傳粉昆蟲提供了一個降落的平臺,又往往擔負著引誘和容留傳粉者的重任,當傳粉者落在唇瓣上或從由其形成的陷阱(牢獄)中逃出時,身體上部正巧緊貼著蕊柱的上部,保證了花粉塊的取、送成功。在被子植物中,許多靠昆蟲或其他小型動物傳粉的花朵,都為傳粉者準備了報酬一花蜜、花粉甚至臨時的新房,以爭取傳粉者為其服務。但蘭花卻往往另辟蹊徑,靠氣味、顏色、形狀等方面的擬態誘騙傳粉者為其義務勞動。所有這些特化、調整、融合與無報酬的誘騙和只有一次的機會相聯系,似乎是一種風險很大的生殖策略,但顯然蘭花是成功的。由此可見,蘭科堪稱最卓越的被子植物家族。
一旦傳粉受精成功,一朵蘭花的子房便發育為一個充滿數萬個微小種子的蒴果。蘭花的種子如塵埃一樣細小,僅由胚和種皮組成,沒有儲存營養物質的胚乳,也沒有子葉。顯然,微小的種子更有利于在空氣中遠距離傳播,擴大了種群生存的空間。但沒有營養物質的儲備,一旦萌發,就會因“斷糧”而失去動力,無法繼續生長,使新生命夭折。如何“魚與熊掌兼得”?聰明的蘭花通過與真菌結盟得到了兩全其美的結果。
蘭花的種皮在正常情況下可以起到保護胚免受傷害,保持種子內的水分和防止微生物侵入的作用。但當與一類“友好”的真菌菌絲相遇時,種皮就失去了防御能力不得不讓其通過。而一旦菌絲與胚細胞相遇就開始了它們的同盟關系,菌絲源源不斷地為胚及萌發后形成的幼苗提供生長發育所必需的營養物質,同時也從對方細胞中獲得某些生活所需的化合物。這種同盟關系一般在蘭花幼苗展開綠葉,能夠進行光合作用而獨立生活時為止;但在某些蘭科植物身上,這種同盟關系會終生保持,因此在它們身上始終不產生葉綠素,失去了進行光合作用的能力,一直得依賴真菌的喂養。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微生物異養”。
古老的起源
蘭科是一個特殊的植物家族,如何對其進行分類,并找出它與其他科之間的親緣關系,是學術上爭論的焦點之一。有的人以蘭花的種子為分類的依據,將蘭科與其他靠異養微生物生活的類群安排在一起。有的人則以花為主要依據,認為蘭科在親緣關系上靠近百合科。還有的人將蘭科單獨置于一個目——蘭目中,這樣一來似乎就沒什么好爭的了。然而,DNA測序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類學依據——精確測定生物染色體上組成遺傳基因的核酸的排列順序,它能幫助生物學家了解某物種在生物演化史上所處的位置,揭示它的來龍去脈。
DNA測定研究表明:蘭科是天門冬目的成員,該目還包括龍舌蘭科、天門冬科、風信子科、鳶尾科和蔥科。蘭科在該目的“系統樹”上是位于基部的一個分枝。目前,科學家推測出蘭科在1億年前就已經分化形成了。這比傳統的認識早了許多。以往,植物學家認為蘭科起源較晚,其原因主要基于這樣一種事實:絕大多數在南美洲和非洲分布的蘭科類群,要么分布在新大陸,要么分布在舊大陸,極少有同一類群植物同時出現在這兩個大陸上的現象。這說明,這些類群基本上是在1億年前南方大陸板塊斷裂成兩個新板塊(南美洲和非洲)之后演化形成的。另外還有人認為:蘭科中的絕大多數種類是附生植物,它們應該是在有花植物組成的森林大量出現以后才演化形成;再有,多數蘭科植物特定的傳粉昆蟲成為有花植物傳粉者的時間較晚,因此認為蘭科植物的歷史不會很長。然而DNA數據顯示,蘭科具有古老的起源。
以蘭科中的香莢蘭亞科為例。香莢蘭亞科包括15個屬。該亞科的演化歷史以往一直令植物學家感到困惑不解:它們都具有比較進化的特征,如有些是攀援藤本,有些具有帶翅的種子,多數具有十分精巧的異花傳粉技能。然而,它們又具有一些通常在更原始的蘭科植物身上出現的特征,如生活方式是地生的,花粉粒并不聚在一起形成花粉團,而且雄蕊和雌蕊的融合程度比多數蘭科植物都低。而來自DNA的
信息告訴我們,香莢蘭亞科的植物很早就與蘭科家族中的其他類群分道揚鑣了。它的歷史淵源可以從“大陸漂移學說”得到佐證。
據考證,在中生代時南半球有一塊超級大陸——岡瓦納大陸,今天的南美洲、非洲、印度半島、澳大利亞和南極洲都包括在內。在距今大約1億年時,這塊大陸開始分裂,使南美洲與非洲斷開。以后在距今9000萬年至8500萬年時,南極洲、澳大利亞及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亞島也逐漸分裂形成。今天,我們可以在這些岡瓦納大陸的“碎片”上發現許多大陸漂移后各自獨立形成的蘭科新類群。但植物學家也發現。蘭科中香莢蘭屬的種類卻呈環地球熱帶地區廣泛分布的局面,在中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尤其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及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新喀里多尼亞等地,都能見到它們的身影。顯然,這一類群在1億年前岡瓦納大陸開始斷裂成非洲和南美洲之前就已經形成,并且已將子孫散布在這塊古大陸的幾乎各處。這也正是DNA向我們指出的事實。
多樣的變化
說到這里,一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在被子植物中具有1億年以上歷史的家族并不罕見,但為什么惟有蘭科植物變得如此與眾不同?通常認為:一場由協同進化精心編導的“芭蕾”——蘭科植物與特異傳粉者的精巧配合過程,是種群產生激烈分化的主要動力。但是,DNA提供的信息卻另辟蹊徑,使我們耳目一新。
在表明蘭科植物在演化過程中所形成的親緣關系圖表——“系統樹”上,我們可以看到,出現最晚的一個分枝上包括了現存蘭科植物中85%以上的種類。這種情況通常表明:在分枝即將開始的歷史時期,在蘭科植物的一些產地曾經發生過環境條件的驟變,例如干旱導致的沙漠化,或在植物體上發生了某些突變,例如一枚花瓣特化成貯存花蜜的“容器”。這樣的變化往往激發了物種進化的活力,造成新物種大量出現的局面。結果,一次生物演化史上的物種“大爆發”就出現了。
現在,DNA研究給出了一種與上述觀點截然不同的原因——從地生到附生的生活方式的轉變,可能引發了蘭科家族物種多樣性的大爆發。
眾所周知,地生植物與附生植物的生活環境具有極大的差異。當一種蘭花將自己的新家從地面搬到高大的森林樹種的“脊梁”上開始過附生生活時,它所面臨的首先是眾多生理學上的問題:水分、光照、礦質營養,因此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植物的根、莖、葉等營養器官,只有基本的生活條件得到了保證,才有可能進一步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因此,在這種從地生到附生的轉變中,因環境脅迫造成的營養器官在形態結構、生理功能等方面的變異,才是新物種形成的重要基礎,其作用超過了生殖器官與傳粉者協同進化對新物種形成的影響。
在蘭科植物的演化史上,生活方式的轉變方向并不是單一的,有些類群由于生態環境的變化等原因,往往又選擇了由附生環境向地生環境的遷移,在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中,是否同樣促使了大量新物種的誕生?研究者對蘭科中沼蘭族植物DNA的研究幫助我們解決了這一問題。沼蘭族植物廣泛分布在熱帶、亞熱帶及溫帶地區,共有三個屬——鳶尾蘭屬、沼蘭屬和羊耳蒜屬,其中鳶尾蘭屬的種類都是附生植物,與之相反,沼蘭屬的種類幾乎都是地生的,而羊耳蒜屬的種類附生、地生基本各占一半。通常認為:沼蘭族植物的祖先是附生植物,后來由其分化出的三個屬中,有兩個屬各自獨立地選擇了地生方式。但來自該族50多個種的DNA檢測結果表明:所有的附生種類都源于一個共同祖先,而所有的地生種類則都來自另一個祖先。而一些種類最后又由樹上下到地面的行為,僅僅是一些偶然事件促成的。
上述研究結果顯然向傳統分類學以花的結構為基礎進行分類的方法提出了挑戰。先進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和計算機的普遍應用,令當代的自然探索者如虎添翼,在前輩們的研究基礎上,他們理應做出更客觀和更前瞻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