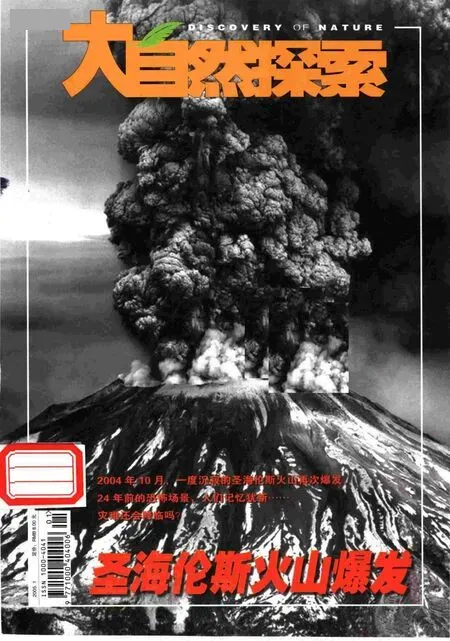來自古代的聲音
編譯葉曦
有時候,你會很容易就忘了木乃伊是人的遺骸,是干尸。但是,只要你仔細地“傾聽”這些不朽的死者無聲的述說,你就會了解那些遠比恐怖電影的情節更怪異的故事。
木乃伊有各種各樣的來歷。有時,它們是被活著的人以無限的敬仰、高超的技巧、莊嚴的儀式精心保存下來的;有時,它們是在沒有空氣的泥沼中、在長年冰封的荒野中、在滴水不見的沙漠中,純粹于偶然間被大自然賦予永垂之身的。為了破解木乃伊隱藏的種種奧秘,現代的木乃伊制作者(其中很多是專家、學者)正在復原它們的本來面貌。
不管是幾千年前還是幾百年前制作的木乃伊,都是現代人一窺過去世界的窗口。木乃伊不僅能揭示古人的外在容貌和內心世界,而且能反映出各種不同的古代文化的種種細節。甚至,通過對木乃伊進行研究,還有助于找到治療現代疾病的辦法。
沒錯,從那些保存至今的古代死者身上,現代人能知道和學到的東西實在很多、很多。
高處的獻祭
千年冰封的安第斯山峰上,完美地保存著三具印加兒童的木乃伊。
康斯坦莎·塞魯蒂向來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人”,這是因為她是移民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她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平原上長大的,在她自己看來,她無論是同安第斯山還是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都沒有什么特殊的淵源。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從小時候起就對安第斯山和在這座山上居住、在這座山上拜祭的人們情有獨鐘。塞魯蒂說,“一定是有什么情結讓我對這座圣山魂牽夢縈,但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情結。就是為了這種情結,我才決心要成為一名高山考古學家,這是我一生的追求。”
5年前,塞魯蒂幫助組織了一次十分了不起的考古探險之旅。在阿根廷遙遠的西部地區,有一座名為“尤伊亞科”的火山,海拔高達6723米,山上稀薄的空氣足以嚇退那些體力或毅力不佳的攀登者。正是在這里,塞魯蒂和頗有聲望的高山考古學家約翰·雷因哈得聯手工作,從而發現了迄今為止已知海拔最高的印加遺址,并且發掘出了迄今為止已知保存最為完整的木乃伊——三個印加兒童的干尸。
這三個孩子是什么人?他們為什么會被活埋在這座高山冰墓中?這些都是難解的奧秘,因為盡管印加人擁有在他們那個時代出類拔萃的技術和藝術能力,卻未留下任何文字記錄。不過,塞魯蒂和其他一些考古學者運用種種考古線索、16世紀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文獻和因為嚴寒而保存下來的古代DNA,正在一步一步地重現幾百年前在安第斯山山頂所發生的一切。在塞魯蒂看來,這些木乃伊就好比是信使,是作為他們在世時的那個世界的代表,被獻祭給山神的祭品。
事實上,在西班牙殖民者的文獻中,對阿根廷西北部遙遠山區的記述少之又少。這一地區是后來才加入印加帝國的,在16世紀的印加帝國鼎盛時期,帝國的疆域沿著南美洲西海岸綿延達3000公里。塞魯蒂做出系統而全面地調查這一大片區域的決定,是在1999年,那一年她才28歲,還是一名高山考古的新手。在這之前5年,也就是在塞魯蒂拿到人類學的學位之后,她開始攀登高山。在這5年間,她已征服了阿根廷國內最高的80座山峰。
根據塞魯蒂的發現,許多山頭上都有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就有人進行過宗教儀式的證據,這些證據通常是焦炭或低矮的石墻——它們是小型圣祠的殘留物。不過,有時候也能在山頂上找到更大規模、更重要的人類活動遺址,不光有圣祠,還包括搭有屋頂的正規居所,甚至還有墓地。為了到達那些更加遙遠的遺址,塞魯蒂常常得攀登8個小時。她通常在夜間開始登山,這樣就能在早晨抵達,而且在天亮之后的頭幾個小時里,風沒有那么大。
為什么印加人和他們的先人愿意耗費這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攀登這些險惡的山峰,難道目的僅僅是為了修建圣祠、祭拜神靈?比基魯蒂更早,高山考古學家雷因哈得是從20幾年前就開始了在安第斯山地區的考古發掘工作的,當時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越靠近山巔也就越接近太陽。太陽正是印加人崇拜的圣物,難怪有人相信:印加人之所以如此勞神費事地在山頂修建圣祠,就是為了祭拜太陽神,就是為了更靠近太陽神。但雷因哈得并不這么看。他認為,印加人這般不辭辛勞,其實是為了祭拜山神,因為在印加人看來大山正是他們的保護神,是主宰天氣的風雨神。為了給自己的理論尋找證據,雷因哈得開始在山峰上搜索古印加遺址。
在找到了不少的山頂印加遺址之后,雷因哈得相信尤伊亞科山的山頂上一定也有這樣的遺址。當時,塞魯蒂也注意到了這座火山。在阿根廷北部和智利交界線周圍的一大片區域里,尤伊亞科火山是最高的山,其山頂終年冰封,永不解凍。“尤伊亞科”在印加語言中意為“欺騙之水”,這很可能是由于盡管山巔蓋著冰帽,卻無水從山上流下。共同的興趣讓雷因哈得和塞魯蒂攜起手來,在獲得阿根廷政府的許可之后,他們于1999年初開始了尤伊亞科山探索之旅。
這是一次千辛萬苦之旅。在一般人所無法承受的生理和自然條件下,雷因哈得、塞魯蒂和他們的一些助手在尤伊亞科山上總共待了23天。要知道,一旦到了海拔5800米以上,一般人就很難適應。高山缺氧會造成人體細胞的永久性損壞,人體免疫力開始下降,腦部和肺部也可能積水。在最好的情況下,你的神智和判斷能力也可能受到影響;而在最壞的情況下,你恐怕就一命嗚呼了。由于天氣太冷,風太大,就連在操作精密的測量儀器時也不能取掉厚厚的手套,而且電子儀器也常常會發生低溫故障。就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考古探險隊在山頂上一待就是13天,創下了高山考古的連續工作時間新紀錄。
雷因哈得一行在尤伊亞科山上找到的最明顯的遺址,就是靠近山頂的兩座石建居所。旁邊則是一個長10米、寬6米的區域,四周有低矮的石墻環繞。初看上去這個區域并不顯眼,但正是在這里,探險隊發現了一張意義不凡的祭臺。于是,他們開始進行發掘,兩天之后他們就發現地面下1.5米處有一個小坑穴,坑中蜷縮著一具小男孩的干尸。男孩身穿一件亮紅色的寬松外衣,尸體呈胎兒姿態,臉埋在兩膝之間。
雷因哈得和塞魯蒂的隊伍很快又發現了第二個小墓,墓中的裹尸布下面是另一具兒童的干尸。這是一個女孩,她的頭發被非常細致地編成了好多條細小的辮子。小女孩雙腿交叉,頭懶洋洋地靠在肩膀上,就好像永遠地睡著了。最后,探險隊又發現了第三具兒童干尸。這同樣是個小女孩,在過去500多年中的某個時候,她的尸體明顯遭到過雷擊,她的裹尸布有一部分已被損毀,所以塞魯蒂第一眼就見到了她那張仰向天空的美麗面龐。探險隊員們給這個女孩起名為“雷電女孩”。“那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塞魯蒂回憶說。“我們不是在發現某個人,而就像是在會晤某個古人。”
除了“雷電女孩”有些表皮毀損之外,三具兒童干尸的保存狀況都非常不錯。原因是因為這里太冷,從不解凍。三個孩子被深深地冰封在山頂地面下達500年之久,從未遭遇過由于解凍而帶來的細胞破裂及身體組織
損壞等問題。x光透視表明,這三具兒童木乃伊的內部器官保存狀況在迄今為止已發現的所有木乃伊中都排在最佳之列。他們的大腦看上去就好像他們剛剛才離世一樣,他們的肺部也仍然鼓脹著空氣,甚至就連他們的心臟和血管中也都還有血液。不僅如此,他們的身體上也沒有任何創傷的痕跡。研究者們根據這三個孩子的牙齒和骨骼估計,“雷電女孩”死時的年齡只有6歲。那個男孩為7歲,而另一個女孩則可能已有15歲。
印加人為何會讓三個孩子凍死在這高山頂上?雷因哈得和塞魯蒂認為,西班牙殖民者記錄的文獻中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卡帕科洽”儀式——印加人最重要的一種宗教儀式上,他們會把最漂亮、最純潔的兒童或少女祭獻給神靈。就在儀式開始之前不久,被選中的孩子們會被帶到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在那里,國王會主持舉行一個持續好幾天的盛大節日,然后,
由官員、祭司和孩子家人組成的隊伍就從首都出發,前往山上的圣所。一路上,這個隊伍只能步行,并且要盡量走直線。
迄今為止已發現了大約
20具被用來獻祭的孩子干尸。從尸體情況來看,當時的“劊子手”曾盡量讓孩子們死得不那么痛苦。一些孩子可能是被毒死的,還有一些是被悶死、勒死或被擊頭致死的,其余的則可能是被暴露在嚴寒之中、最后被凍死的,尤伊亞科山的山頂上可能就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按照塞魯蒂的解釋,這些孩子被帶到山頂上以后,祭司們一邊生火和掩埋供品,一邊等待孩子們在嚴寒中被冷得逐漸失去知覺,此后他們就會把孩子們埋進墓坑中。
在孩子們被用來獻祭之前,他們很可能被使用了麻醉藥物。當這些孩子木乃伊被迅速(以防腐爛)送進實驗室之后,科學家檢測了其頭發中的藥物含量,結果發現,木乃伊頭發中不含煙草成分,但可卡因的含量很高。不但如此,孩子們在死前至少10天就開始主動或被動地大量服用可可,因為至少要經過這么長的時間,在體內循環的化學物才能夠沉積在頭發里。那位15歲少女的可可服用量尤其高,因為其頭發中的可卡因含量竟然是現代安第斯山山民平均值的3倍以上。除此之外,她的嘴唇邊還有細碎的可可葉片。塞魯蒂認為,在印加帝國時期,可可的消費被國家嚴格控制,可是這些孩子卻在大量服用可可,這很顯然是國家要他們這么干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印加人在用兒童進行獻祭時還算得上是相對“仁慈”的,因為他們注意了盡量減少被獻祭兒童死時的痛苦,然而用活人獻祭的行為本身就是古人的一種愚昧無知的殘暴之舉,是對人類本身摧殘,是在當時認識水平極其低下條件下的瘋狂行為,這種大悲劇已經成為歷史,永遠不會重演。
在“卡帕科洽”儀式上埋下的供品,則揭示了這一宗教儀式的其他一些細節。這些供品現在已十分罕見,這是因為絕大多數印加遺址要么早已被西班牙殖民者徹底毀壞,要么在后來遭到了劫掠。幸運的是,這三個孩子的墓穴中就出土了100多件同樣保存完好的隨葬物品,其中包括一種異常華美的頭飾,是用巨大的白色羽毛做成的,而這種大羽毛是屬于哪種鳥類則至今仍未被查明。隨葬品中還有一些裝著頭發的袋子,很可能就是孩子自己的頭發。塞魯蒂認為,印加人相信頭發具有神奇的力量。在首次為孩子剪頭發之前,印加人要舉行隆重的儀式,并且把長頭發編成成百上千根辮子,以免發絲散落出來。
在尤伊亞科山頂印加遺址找到的其他物品。進一步凸現出“卡帕科洽”儀式的重要程度。在這些印加遺物中,有一條珠光寶氣、煞是好看的項鏈,是用生活在厄瓜多爾海域的一種粉紅色閃光貝殼制作的。對印加人來說,這種貝殼比金子還珍貴,因為它是如此稀罕。山頂遺址還出土了精美的織物和容器,從中可見當時的工匠在制作這些貢品時簡直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些內嵌復雜金屬片圖案的貢品顯然并非一個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好多個工匠的通力協作。這些實實在在的證據,證明了“卡帕科洽”儀式在一統印加江山方面有著何等重大的作用。
對塞魯蒂來說,其中最有趣的貢品之一,是一組牧羊小雕像,包括羊群和一個牧羊人。這組雕像是用金、銀和粉紅色閃光貝殼做成的。塞魯蒂相信,這組雕像表明了“卡帕科洽”儀式的一個意圖,就是想提高牲畜的繁殖能力。不過,這種復雜的儀式顯然還有其他許多方面的象征意義。塞魯蒂認為,舉行“卡帕科洽”儀式的最主要目的還是同一個新國王的繼位有關,新國王需要通過這種儀式來保證帝國的完整,來加強中央集權,來重建人與“神”之間的平衡。塞魯蒂指出,“卡帕科洽”中的“卡帕”意為“與王權有關的”,“科洽”意為“邪惡、罪惡或宇宙的失衡”。而雷因哈得認為,或許還有其他許多災難性的事件,如重大的自然災害和劇烈的社會動蕩等,都可能促使印加人向山神求佑祈福。
對研究者們來說,有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可見,就是對山神的崇拜深深扎根于安第斯文化中,這一傳統甚至持續到了今天。看來,印加領導者利用這種信仰,就能勸服子民把大量時間和財物(甚至還包括子民的孩子)奉獻于山頂的儀式中,目的正是要以此來穩固王權、統一帝國。
2000年,有關專家對那三具印加孩子木乃伊進行了
DNA分析。結果表明,孩子的父母很可能是自愿把自己的子女獻祭給神靈的,因為那兩個女孩可能互為親戚。盡管線粒體DNA(注:一種遺傳物質。并且只由母體遺傳給后代)分析結果顯示,她倆不可能有同一個母親,但是對細胞核中的染色體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在9個基因序列中,她倆就有7個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說,她們可能擁有同一個爸爸。
科學家希望通過分析、比較當代安第斯人和這三個孩子的DNA,得到有關這些孩子的血緣和出生地的進一步信息,但這項工作的完成尚需時日,因為這需要大量現代安第斯人的DNA樣本,而目前已經獲得的樣本數還遠遠不夠。不過,哪怕只運用已有的樣本,科學家就已找到了那個15歲少女的一個親戚。一個秘魯人。目前居住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其線粒體DNA同那個15歲少女的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DNA分析還揭示了另一個令塞魯蒂始料不及的結果。為了確保所研究的那三個孩子的DNA樣本(目標樣本)未受到污染,所有與三具木乃伊接觸過的人都被要求接受DNA測試。測試結果表明,目標樣本沒有受到污染,但是塞魯蒂的DNA比其他大多數人都更接近那三個孩子。也就是說,塞魯蒂體內毫無疑問地涌動著南美洲當地人的血液。至此,塞魯蒂那種天生對大山的“莫名”熱愛就不是“莫名”的了——出乎塞魯蒂想象、卻又讓她感慨萬千的是,她和那三個凍結在時間長河里的印加孩子原來竟有那么多的相似!
天堂里的寄生蟲
將一種現代瘟疫追根溯源至古埃及,或許有助于科學家制服這一疾病的“現代版”。
木乃伊的下落真是千奇百怪。比如:薔薇十字會員(注:也叫煉金占星術士,十七八世紀一些秘密社團的成員,自稱會玄術)曾經在一家奢侈品商店里買到過一具
木乃伊;在英國約克郡士嘉堡鎮礦工康復之家的地面下,也曾埋葬過一具木乃伊。1868年,英國威爾士王子愛德華訪問埃及時,竟然一次就“發現”了30具木乃伊。其實,這些木乃伊全是事先從流動商人手中買來的,然后被一起放進一個很容易被愛德華王子“發現”,的墳墓中。在過去的幾百年中,大量的埃及木乃伊流向了各種稀奇古怪的地方。但不管它們現在身在何處,也不管它們是如何去到這些地方的,羅莎麗·戴維和英國曼徹斯特的埃及木乃伊研究小組都想得到它們身上的一小塊,僅僅很小一塊就夠了—不管是肝臟、直腸的一小塊,還是膀胱、皮膚的一小塊,都行曼徹斯特研究組對木乃伊碎片的熱忱始于1996年。當時,總部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國際醫療服務公司的總裁康蒂斯打電話給羅莎麗說,他的公司正在同埃及的政府合作進行一項有關血吸蟲病的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事實上,埃及人口中有10%都感染了血吸蟲病。康蒂斯對羅莎麗說:“如果能調查一下古代這種病的流行情況,或許不僅將是十分有趣的,而且也可能將會很有幫助。而主持這項工作的最明顯的人選,就是你——曼徹斯特博物館埃及分館的負責人羅莎麗。你有興趣做一些流行病學方面的科學探案工作嗎?”這項工作的實質是查明血吸蟲病在過去5000年里的流行、變化情況。羅莎麗當即答應了康蒂斯的請求。
羅莎麗之所以答應開展這項研究,是因為她希望了解血吸蟲病的類型在古代和現在有何不同,同時她也想知道這種病在不同時期的發病率有何不同。如果能查清這些情況,或許將有助于揭示埃及歷史上一些奇怪事件的真相。比如,對于公元前2181年“舊王朝”的崩潰,迄今為止一直缺乏符合邏輯的解釋,專家們懷疑血吸蟲病在這中間起了作用。假如因這種病死的人太多,整個社會恐怕就只有崩潰。
康蒂斯希望開展這項研究,當然并不只著眼于破解一些歷史謎題。事實上,研究古代的血吸蟲,首要目的是弄清這種惡蟲的一部分進化史,為開發新的治療手段或更好的疫苗提供幫助。到了2001年,羅莎麗的研究小組已經取得了一項重大的突破性成果,這項成果有可能幫助研究者們最終解開血吸蟲怎樣發展、變化并“智勝”其宿主之謎。這項成果的潛在效益無疑是十分巨大的。
血吸蟲病是由生活在人體內的寄生蟲引起的,但血吸蟲的幼蟲在淡水蝸牛中繁殖。被感染的蝸牛釋放出微小的叉尾幼蟲,稱為“尾蚴”,尾蚴游至最近的人體皮膚上,并開始挖洞。在被污染水域游泳、洗東西或釣魚的人都可能被感染。尾蚴進入皮下后,穿過肌肉侵入肝臟,在那里長大成蟲。
在埃及,現在有兩種血吸蟲——埃及血吸蟲和曼氏血吸蟲,其中前者集中于膀胱和排尿系統中,后者則侵犯直腸和肝臟。血吸蟲本身不會造成什么傷害,但是它們那有刺的卵會鉤在宿主的身體組織上,導致出血和發炎,這又進一步導致組織鈣化。如果不進行及時、有效的治療,血吸蟲病就可能發展成膀胱癌,或導致肝臟衰竭。
目前,全球有大約兩億血吸蟲病患者,其中大約600萬名患者在埃及。在埃及血吸蟲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政府一直在推行大規模的治療,同時開展血吸蟲科普教育,并且努力清除當地水源中的蝸牛。這些努力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1991年,埃及有40%的入口感染血吸蟲病;到了2001年,這一數字已經降到了10%。不過,重新感染的機會仍然很大,最終治療也必須持續進行下去。盡管人們對血吸蟲病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但至今仍然沒有研制出疫苗。另外還有跡象表明血吸蟲可能正在產生抗藥性。因此,研究者們需要在血吸蟲的“盔甲”上找到一個缺口——而羅莎麗等人的工作或許能在這方面提供幫助。
毫無疑問,古埃及人也遭到了血吸蟲病的困擾。在古埃及紙草文獻中記述的“aaa”病,就非常符合血吸蟲病的特征,但更明顯的證據則來自木乃伊本身。當古埃及人為制作木乃伊而為死者涂藥防腐時,死者體內的寄生蟲自然也被保存了下來。多年來,科學家已在木乃伊體內發現了一系列的寄生蟲種類,其中就包括血吸蟲。但是,要想查明血吸蟲病在過去5000年中的情況,羅莎麗和她的研究小組的首要任務就是取得盡可能多的木乃伊樣本。也就是說,羅莎麗和她的研究小組必須獲得成千上萬個木乃伊身體切片樣本,而且這些樣本還得來自埃及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不同個體,還得來自男女老少、各個階層。因此,為了尋找到足夠多的木乃伊樣本,羅莎麗等人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廣泛搜尋。1997年羅莎麗建立了“曼徹斯特木乃伊身體組織銀行”,實際上它是博物館中一個特制的防火保險箱,專門用來保存人們捐贈的木乃伊切片樣本。
追蹤木乃伊和獲取木乃伊身體組織樣本的工作落到了研究小組成員翠西肩上。“你得廣開思路,因為它們(木乃伊)可能出現在任何稀奇古怪的角落,”翠西說。尋找木乃伊的所在地點是搜尋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因為勸說人們獻出一點點木乃伊樣本其實并不太難。在頭一年中,翠西向全球各地的博物館、醫學院及其他學校、對外開放的豪華古宅和其他任何可能擁有一具埃及木乃伊的人和單位發出了總共8000封求助信。-其中,之所以向豪華古宅發信,是因為其原來的主人有可能曾經將木乃伊當作紀念品帶回家。翠西發現,有些地方有幾百具木乃伊,有些地方只有一具,還有些地方則只有木乃伊的頭顱,或一只手,或一只腳,甚至只有一根手指。過去人們常常只把木乃伊身上的一部分作為紀念品買回家,因為這樣很容易運輸。
由于翠西的辛勤工作,“木乃伊身體組織銀行”已經擁有上千個樣本,并且這個數字還在穩步增長。研究小組最想得到的是膀胱、直腸和肝臟的樣本,因為這些器官中最有可能包含蟲卵或成蟲。有些木乃伊制作者喜歡把死者的內部器官和身體的其余部分分開來進行處理,并且把內臟存儲在罐子里。遇到這種情況,取樣就容易一些。還有一些木乃伊制作者習慣把經過單獨處理的內臟器官放回死者體內,不過不是總能放對地方,直腸或許會被塞進胸腔。但是,通過內窺鏡仔細觀察,還是常常有可能對所需的器官進行定位和取樣。然而,許多木乃伊都是不完整的,常常只剩下骨骼、皮膚,也許還有一點點肌肉。
在翠西搜尋木乃伊的同時,翠希婭——翠西的一位同事則在尋找從木乃伊身體組織里探查血吸蟲和蟲卵的辦法。在活組織中,探查過往感染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尋找抗體,這些抗體是在人體遭到血吸蟲攻擊時產生的。但人死后抗體很快就會分解,因此在木乃伊身上幾乎沒有可能找到抗體。于是,翠希婭改而搜尋比抗體堅韌得多的分子——躺在血吸蟲卵表面的抗原。
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翠希婭才找到了一種理想的抗毒血清,其中包含的抗體能夠瞄準她所選中的抗原,并與之結合。找到合適的抗體之后,下一步的工作是給抗體添加一種熒光“分子標簽”,以便讓抗體能夠在顯微鏡下面“現形”。當翠希婭把抗體和“分子標簽”用到感染了血吸蟲病的老鼠身體組織樣本中時,她清楚地看見了發出蒼白綠光的血吸蟲卵輪廊。“這證明,這
種辦法至少對現代人身體組織來說是十分有效的,”翠希婭說。接下來,就需要在取自木乃伊的古代身體組織樣本上進行“實戰”了。
“實戰”的確要困難一些。不管想在顯微鏡下面看什么東西,都需要切出最薄的身體組織切片。可是,木乃伊的身體組織既干又脆,其中常常還含有堅硬的沙粒,足以損壞任何刀刃,哪怕是金剛石刀刃也一樣。因此,樣本首先需要被加水軟化。其次,要解決沙粒問題,辦法是使用氫氟酸溶液,這種危險的溶液在溶解沙粒方面非常有效。最后,經過軟化和除沙粒后的樣本還需要一些支撐,因此還需要將樣本浸入松酯里。經過這一系列程序之后,翠希婭終于能得心應手地切出最薄的樣本切片了。這樣,她就能著手在已死去很久的古人身上嘗試運用自己開發的新技術。
她的第一個樣本來自博物館所藏的一具木乃伊的膀胱。這個被稱為“1766號木乃伊”的女性死于公元1世紀或2世紀。先前的x光透視結果顯示她的膀胱中有鈣化組織,由此幾乎可以肯定她感染過血吸蟲病。假如翠希婭在她的膀胱中都找不到血吸蟲卵的話,那么要想在她身體的其余任何部分找到血吸蟲蟲卵幾乎就不可能。結果不出意料:在顯微鏡下面,翠希婭看見了多個蟲卵,而且一眼就可辨認出它們屬于埃及吸血蟲。接著,翠希婭大吃一驚——她看見了一條成蟲的頭部,甚至連上面的吸管也清清楚楚。
經過抗原測試,科學家們將會知道在埃及歷史上的不同時期血吸蟲病的發病率有多高,以及患者都是哪些人。1998年,康蒂斯及其同事完成了一項研究,內容是現代埃及血吸蟲病患者的特點分析。但羅莎麗研究小組的研究結果卻很可能與康蒂斯等人的研究結果大相徑庭。這是為什么呢?
在當代埃及,血吸蟲病患者幾乎都集中在鄉村,城鎮居民中極少有人患上此病。在感染者中,兒童比成人多,男孩比女孩多,這是因為孩子們一旦經過治療而初愈后,就又迫不及待地想玩水,其中男孩又比女孩愛玩水。而在當代埃及情況卻不同,血吸蟲病分布情況顯現出明顯的區域集中特點,比如:一些村莊里的發病率很高,但不多遠處的另一些村莊里的發病率卻極低。此外,現代灌溉方案為蝸牛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人類活動也改變了兩種血吸蟲(埃及血吸蟲和曼氏血吸蟲)的分布情況。1971年,埃及阿斯旺大壩建成,在開羅以北的三角洲地區,攜帶埃及血吸蟲卵的蝸牛開始消亡。與此同時,攜帶曼氏血吸蟲(一種致命性更強的血吸蟲)蟲卵的蝸牛卻乘虛而入。
在古埃及,人口比現在要少很多,但無論是村民還是城鎮居民,無論是男女老少,無論貧富,所有人感染血吸蟲病的概率都是一樣的。這一點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羅莎麗認為,這是因為在古代即使最高貴的人也可能下過河,其花園中的游泳池池水也可能來自河中。這樣,古埃及人人都可能感染埃及血吸蟲病。不過,對于曼氏血吸蟲最早于何時出現在埃及,科學界至今仍爭論不休。“看來它(曼氏血吸蟲)是在現代才進入埃及的,因為我們至今沒有在埃及木乃伊身上找到曼氏血吸蟲的蟲卵或者成蟲。不過,我們還在繼續找。”羅莎麗說。
迄今為止,翠希婭已經檢測了50個不同的木乃伊樣本,并發現其中30%感染過血吸蟲病。盡管樣本數量還太少,不足以由此做出任何結論,但是它也帶來了一個謎題:如果血吸蟲病在古埃及確實很流行,那么大部分人口都會深受其害,整個民族幾乎都成為病夫。可是,古埃及人卻創造出了如此驚人的文明。這是為什么呢?羅莎麗認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古埃及人所攜帶的成蟲少,所以癥狀并不嚴重,畢竟那時的人口數量和蝸牛數量都遠遠比現在少。但是,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就是在過去的幾百年里血吸蟲一直在變得越來越可怕。
2001年取得的一項突破性研究成果,或許有助于破解上述奧秘。當時,翠希婭從木乃伊身體組織里的血吸蟲殘骸中成功地提取了血吸蟲的DNA,這就為調查血吸蟲的進化史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比較古代血吸蟲和現代血吸蟲的基因圖譜。下一步羅莎麗的研究小組將查明血吸蟲究竟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的。“這是一種狡猾的惡蟲,它看來總是領先于人類好幾步。”羅莎麗說。
完美的肖像
世界最古老的肖像畫所揭示的不僅是面孔。考古學家們更想知道:為什么古埃及人希望后人以為自己就是肖像畫上的那個樣子?
她長著一個鷹鉤鼻,下巴有點尖,發型很怪異。不過,這個只知道被稱為“AES74713”的婦女身上卻有一些更耐人尋味的東西。看著她的眼睛,你會有些許不安的感覺。這或許是由于那不僅是一雙眼睛,而且是兩扇可以窺探那個生死在接近2000年前的死者靈魂的窗戶。
“AES74713”的肖像畫及其他來自公元1世紀和2世紀的千幅埃及肖像畫,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精確描繪人類面容的畫像。這些肖像畫統稱“法揚肖像”,畫中人物的姿態大多明顯具有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特征。人們普遍相信,這些肖像畫忠實地記錄了古埃及時代的生活和時尚。可是,畫中的信息是否真的有那么“忠實”呢寧新的研究顯示,其實并非所有的“法揚肖像”都完全真實地描繪了逝者,因為有些死者生前故意讓人(或由自己)把自己畫成具有他人的特征。
法揚是位于埃及首都開羅以西1 00公里的一片青蔥綠地。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后,一幫希臘商人和官員在此定居。他們逐漸吸納了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習俗,當時流行的木乃伊制作程序之一就是用精細的亞麻布包裹尸體。而希臘人有一項創新,就是在包裹尸體之后在死者頭部放一張死者的肖像畫。這種肖像畫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與傳統的埃及繪畫風格大不相同,而同當時歐洲繪畫及雕塑中的寫實風格很一致。
“法揚肖像”看起來像是油畫,但實際上是色蠟畫,即把溶化的彩色蠟液當成“顏料”,用小抹刀畫在木板上。自1888年起,英國考古學家威廉·弗林德斯·佩特里陸續發現了許多“法揚肖像”,他確信這些畫像都是對死者的真實描繪。他指出,這些畫像都是在經過切割之后被放進木乃伊的繃帶下面的,這就暗示以前畫像是掛在家里的。在一處陵墓中,佩特里甚至還發現了一幅有完整畫框的肖像畫,當時這幅肖像畫就立在一具木乃伊的旁邊。
一些歷史學家認同佩特里的觀點,他們認為,“法揚肖像”不僅是對死者面容的真實反映,而且其中一些畫像中的面孔看上去比木乃伊要年輕些,這說明有些畫像在死者生前就早已畫好。然而,在“法揚肖像”重見天日100多年后,2001年有人對這些畫像的精確程度進行了驗證。英國科學家從木乃伊的頭骨入手,用石膏重建死者的面容,然后將重建的面容與畫像上的面容作對比。
如今,只有不到10%的“法揚肖像”仍舊纏在木乃伊上,并且這些木乃伊大多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博物館和私人手中。幸運的是,倫敦博物館就提供了兩個纏有畫像的木乃伊頭顱。其中一個是一名50歲男子,而另一個就是“AES74713”——一名20多歲的婦女。
科學家們在不看肖像畫的情況下,首先復制了木
乃伊的頭顱。然后,他們根據死者的性別、死時的年齡和人種特點(從頭骨上可以推斷出)來重現死者的面部肌肉。經過幾星期的辛苦工作之后,兩個死者的面貌被重現出來。那個50歲男子臉寬平,鷹鉤鼻。方下巴。“AES74713”的臉窄小而精致,厚嘴唇,鷹鉤鼻略偏向左。當倫敦博物館的人員打開這兩人的肖像畫時,科學家們驚喜不已——重建的死者面容同畫中的死者肖像很相像。由此看來,佩特里當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接著,科學家們又重建了另外兩具木乃伊的面容。其中一具“法揚木乃伊”是一名30歲男子,由丹麥哥本哈根博物館提供,重建出來的面貌特點是寬顴骨。鼻寬且直,嘴唇厚,方下巴,這些都與肖像畫上的死者面容特征不符合,因為肖像畫顯示的死者臉長而窄,鼻子長,下巴圓。也就是說,重建的死者面容明顯具有非洲黑人的特點,而肖像畫上的人看上去則像是高加索人。不僅如此,肖像畫上的人看上去肯定不止30歲。
科學家將這具木乃伊的頭骨照片疊加到他的肖像畫上,結果發現兩者毫不匹配。這要么是因為肖像畫作者的畫技太差,要么是由于畫上的人和死者原本就不是同一個人。科學家們更傾向于相信是后一個原因,因為在同時制作大量木乃伊時的確有可能將肖像畫和木乃伊搞混。不過,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后來的歐洲中間商故意將肖像畫和木乃伊張冠李戴,尤其是把美女或帥哥的肖像畫纏在面容模糊難辨的木乃伊頭上,以次充好。
另一具“法揚木乃伊”來自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他的頭骨也明顯具有非洲黑人的特點,重建出來的面部特征是寬鼻子,方下巴,厚嘴唇。而肖像畫上的人卻皮膚白皙,鼻子窄,貌年輕。可是,畫中人面部的其他特征卻又和重建出來的特征很一致。頭骨照片疊加到肖像畫上,結果發現兩者就是同一個人。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現在一些古埃及學家相信,答案就是:當時的一種時尚就是要讓自己看起來更像是希臘人。事實上,當時希臘和羅馬文化對埃及的影響很大,在服飾和發型方面尤其明顯。到公元1世紀羅馬人征服埃及時,那些生活在法揚的希臘人已經和當地的埃及人通婚達300年之久,但人們當時更強調自己的歐洲血統,因為羅馬征服者同意為具有歐洲血統者減稅25%。
當然,僅憑四具木乃伊是遠遠不能斷定“法揚肖像”的本質特征的。不過考古學家們現在普遍相信,“法揚肖像”作者的目標一定是要盡可能真實地反映被畫者的本來面貌,不過,繪畫過程中也肯定進行了必要的美化,畢竟繪畫者向來都需要適當地奉承被畫者。這或許就是“法揚肖像”的基本特點。
“不朽”的秘密
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死者肉體的腐爛?考古學家正在運用各種手段,探索尸身“永垂不朽”之謎。
塵歸塵,土歸土。死神會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人死后尸體很快就會腐爛,通常的情況總是這樣。但時不時地也有某種力量(不管是自然造化還是人為因素)能阻止尸體腐爛,從而把尸體變成了木乃伊。既然有那么多人對“活著的逝者”——木乃伊很著迷,因此就有必要弄清木乃伊是怎樣制作出來的。當然,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科學家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冷凍、風干及某些化學物質,這些物質能阻止細菌和人體酶分解尸體組織。至于上述問題的答案細節,隨著科學家們的進一步探索才剛剛開始浮現。
以埃及木乃伊為例,我們知道脫水是其中的關鍵,因為脫水的過程就把細菌作惡所需的水給剝奪了。但是,木乃伊究竟是怎樣制作的呢?對于具體的制作法,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者一直作為商業機密而守口如瓶,因而至今無人知曉。不過,古埃及木乃伊制作業的行外人還是留下了有關木乃伊制作方法的一些記述。但是,這些記述中是否已包含木乃伊制作方法的一切細節呢?誰也不敢肯定。
一些科學家認為,要想知道古代歷史學家是否真實地記錄了古埃及木乃伊制作過程的所有細節,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他們的記述來實際制作木乃伊。看看會有什么結果。1 994年,按照美國巴爾蒂莫市一位老人的遺愿,他的遺體被捐給科學家做研究用。這樣,科學家就獲得了制作木乃伊的良好“素材”。
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其他人的記述,科學家首先將死者的大腦和腹部器官取出,然后用裝有泡堿(鹽、碳酸鈉和重碳酸鹽的混合物)的亞麻口袋充填空隙。這些泡堿是從埃及已經干涸的鹽湖中取來的,這是為了完全遵循歷史記錄。接著,科學家用284千克泡堿覆蓋尸體,并將泡堿和尸體置放在一間既熱又干燥的屋子里,一放就是35天。科學家們猜想,35天后他們看到的多半會是一堆腐臭的爛肉。
然而他們一打開房門,鼻子就告訴他們情況遠遠不是他們所預想的那樣。尸體散發出一種略帶刺激性的魚腥味,不算好聞,但也不算難聞。移走泡堿后,一具干尸出現在他們眼前。看上去,那簡直就是一具典型的埃及木乃伊,像皮革一樣的褐色肉皮跟埃及木乃伊完全一樣。由此看來,埃及木乃伊尸身3000年不腐就并不奇怪了。
人體的一半以上成分是水,而泡堿幾乎將這些水分完全吸干。就那具尸體而言,僅在臀部和背部幾處地方還明顯可見水分和油脂。仔細檢查這具干尸之后,科學家為它涂上油,并用香料和木屑充填空隙,再用亞麻布包裹干尸。在古埃及,此舉被認為可以讓死者免遭蚊蟲叮咬,同時也能讓死者看上去豐滿一些。現在,這具木乃伊已被保存了10年多之久,毫無腐敗跡象。一些科學家因此推測說,除水是制作木乃伊的關鍵之所在。
真是這樣嗎?有一些專家認為,除了除水,還有其他一些關鍵性的步驟。比如,按照史書記載,尸體干燥后,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者還會用油、蠟和松酯涂抹尸體表面。此舉曾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宗教意味、卻并無什么實際意義的行為,但現在看來不是這樣,因為陵墓中通常都很潮濕,如果不采取進一步的防水和防腐措施,干尸就會因再度吸水而腐爛。對13具埃及木乃伊的檢測發現。其中12具干尸身體表面的涂抹和覆蓋物中都含有松酯或蜂蠟(兩者都有抗菌作用),只有一具沒有。而這具干尸的保存狀況恰恰最差。不僅如此,大多數干尸表面還涂有其他植物油,它們可以聚合成像油漆一樣的保護層,這也正是人們在油畫上涂抹亞麻籽油的原因。因此,涂抹防護層才有可能確保干尸歷經千年而不腐。
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者無疑算得上是高手,但木乃伊完全可以不經過人手而自然形成。時不時地會有一具干尸從冰川中冒出來,或者從北極的永凍層中現身。只要能避開風,這些干尸就可能會在天然狀態下躺在地下幾百年乃至幾千年而不腐。天然的凍干過程可除掉尸體75%的重量。但在凍干之前,如果出現解凍、再冰凍的情況,尸體的細胞結構就會被破壞,這就是許多極地木乃伊的身體組織在顯微鏡下面也十分難辨的原因。
另外還有沼澤干尸。人體為何能在沼澤中長久保存,為什么一些沼澤干尸能夠保存得很好,而另一些卻不能,這些問題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未解之謎。但毫無疑問的是,沼澤水面下的寒冷和缺氧能將尸體的腐爛速度降至最低。在實驗中,研究者把一些豬埋入英國約克郡被水浸透的荒野地下。6個月后,豬身完好無損,皮膚、肌肉組織和內部器官無一受損。1年之后,豬身仍舊完好。不僅如此,一些身體組織的保存時間更為長久。比如,哪怕是在一般的墳墓中,頭發和指甲也能保存成百上千年。
在另一項實驗中,研究者將6頭豬崽埋入英國北部沼澤中1平方米的范圍內。兩年半過后,其中兩頭豬崽只剩下骨架,兩頭尚存一些身體組織,還有兩頭幾乎完好無損。惟一的區別是,保存狀況最好的那兩頭豬崽所埋的位置是那1平方米范圍內最潮濕的地方。
在缺氧的冷水中,細菌和其他分解體很難存活,而在一些沼澤中還含有一種天然防腐劑——泥炭蘚多糖。泥炭蘚是泥沼中最主要的植物,泥炭蘚多糖是包含在泥炭蘚葉片中的一種復雜糖分子,泥炭蘚多糖分子中包含多組羰基,而羰基與蛋白質上面的胺發生反應后可以使細菌酶失去活性。
一些研究者還相信,泥炭蘚多糖在塑造沼澤干尸的容貌方面也有作用。尸體剛埋入沼澤時,皮膚薄且色淺;而變成干尸后,皮膚則厚、硬得像皮革一樣。制革人在制作皮革時用的是甲醛,而泥炭蘚多糖看來和甲醛有著同樣的功效。要想最形象地理解為什么能夠形成沼澤干尸,就不妨把沼澤看成是一汪甲醛。當然事實也許并非那么簡單。對沼澤干尸皮膚進行的檢測表明,其中并不含有有機的制革成分。
很明顯,這些“活著的死人”還沒打算向現代人吐露自己“永垂不朽”的所有秘密。即使這樣,隨著科學探索的進一步深入,木乃伊及其他一切干尸的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