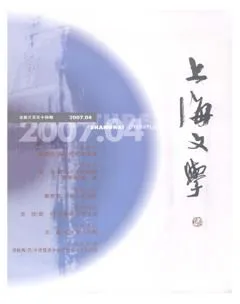我對小麥的感情
2007-12-29 00:00:00北北
上海文學 2007年4期
一
關上車門后,我掃了車內一眼,車內面積四平方米不到。
然后,調整后視鏡。
曹九朵比我矮十幾公分,她的視線與我不同。每天早上八點她接車時,把后視鏡調低點,傍晚這個時候我再調高,循環往復。接下去,我的手它自己知道做什么,想都不用想,食指已經壓到中控面板上的一個按鈕上,車載收音機立即有清晰的聲音傳出:嘀,嘀,嘀……!北京時間十七點整。
下午五點的太陽還像脾氣火爆的少年,見誰曬誰。我瞇起眼往外看,樓密密豎著,路像塊玻璃明晃晃地耀眼。發動,掛檔,踩油門,手輕輕搭住方向盤,上半截墨綠下半截銀灰的菱帥就魚一樣滑出文儒巷。
我一天的生活開始了。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從這時候開始。
小麥說:“速度生活,純粹的收聽樂趣。”
小麥也上班了。小麥坐在一個男人旁邊。我是小麥。男人就接著說,我是周若,周大主持。然后兩人一起高高興興地報數字,一共三串,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