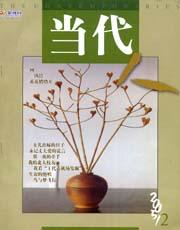午夜河流上的淘金船
毛云爾
我不知道該從早晨還是午夜開始我的敘述,哪一種敘述才是更接受它們的理想途徑呢?我 所指的它們是幾艘淘金船,停泊在我每天必經的河面上。這些鋼鐵鑄造的船只,仿佛幾個孔 武有力卻又瘦骨粼嶙的人,這是初次邂逅它們時,我在心中產生的不免滑稽的印象。
1997年的某一天,我像一粒平常的草籽不為注意地,隨著一陣風飄蕩,然后落進了這座小 城,在一個逼仄的縫隙里開始了漫長的扎根過程。在小城身旁蜿蜒流淌著聲名赫赫的汨羅江 。城市距離河流那么近,就像誰緊貼著河岸佇立在那里,流逝的河水幾乎可以舔到他裸露著 的腳趾。我所在的單位就是其中的腳趾之一,和汨羅江相距咫尺。我可以時常聞到那種屬于 河流的混雜著腥味的獨特氣息,也可以聆聽到河流輕微的喘息聲,仿佛一個不堪重負的人在 廣袤大地上緩慢地前進。
我租住在河的另一邊,生活被一分為二,出現了此岸和彼岸。僅僅是一河之隔,兩岸的景 象竟然大相徑庭,那里,大片的稻田和蓊郁的植被尚未被水泥覆蓋,吞噬。相對這邊繁華似 錦的文明而言,有掩飾不住的質樸與粗糙,散發著農耕時代的落后氣息。每天,我匆匆來往 于河的兩岸,仿佛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穿梭,體驗著文明與原始,感受著喧囂和寧靜。這是兩 種不同的血液,不同的呼吸,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它們在身體中的更替與交換。
每天早晨六點左右,我沿著一條逶迤的土路,穿過幾處樹絲和大片稻田,和那些衣襟上沾 滿泥土、挑著擔子的賣菜人一起,小心翼翼地過河,然后淹沒在迎面撲來的喧囂里。傍晚時 分,我從喧囂中抽身而出,沿原路返回,回到河那邊近似透明的寧靜中。一路上,總有三三 兩兩和我一樣空著雙手回家的人,在黃昏暈眩的光線里,大家臉上的神情無一例外地,既疲 憊又輕松。但后來一段時間,由于加班,抑或無法推辭的應酬,我總是天黑了才回家,有幾 個晚上回去的時候已是午夜十二點了。因為在喧囂中陷得太深太久,我感到身體中的疲憊像 巖石一樣堆積,那樣沉,那樣重。這時,往往剩下我一個人踽踽獨行在回家的路上。身后的 小城依然喧囂,燈火闌珊。而前面,在我回家的道路上,夜色凝重,像化不開的濃稠墨汁, 一層又一層地覆蓋。我感到了孤單與落寞,同時因為前行方向的迷失,心中茫然起來。
汨羅江同樣被夜色所覆蓋。那緩慢的幾乎看不見流運的河水,用自身微弱的光芒與黑暗努 力區分開來。過河的時候,我瞥見上游不遠處,有一盞燈閃爍著,像孤伶伶的一朵花,在黑 暗巖石的罅隙中曳動。在它微弱光暈的籠罩之下,幾艘船在震耳欲聾地轟鳴,沾滿銹跡的傳 送帶從河流中緩緩升起,到達半空又慢慢沉下去,被撈起來的大量泥沙和卵石從半空中傾瀉 而下,相互碰撞,接二連三地爆發出混雜的沉悶聲響。這是幾艘忙碌不停的淘金船。白天, 河面上呈現出一片繁雜景象,從下游駛來的小客輪和附近捕撈魚蝦的小舢板挨擠在一起。是 不是因為它們晃動的身影,致使我忽略了淘金船的存在呢?而現在,小客輪隨波逐流回到下 游去了,數只舢板像蜷縮的幾團陰影,停靠在岸邊。狹窄的河面變得開闊,同時也平靜下來 。就在這開闊且平靜的河流背景之上,淘金船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這午夜時分,也許屬于它 們的一天真正開始了,幾只淘金船迎來了命運中的輝煌白晝。它使我想起那些夜闌人靜時分 寫作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在內心深處尋找,企圖尋覓到那些閃光的文字的金片。在這個隆冬 的午夜,我沒有理由不對這幾艘淘金船肅然起敬。我佇立在下游不遠處的橋面上,急于回家 的欲念淡薄下來,因黑暗和闃寂滋生的恐懼消失了。我明顯感到有什么在撞擊我的靈魂,使 之顫栗。我甚至還感覺到一片轟鳴聲從身體內部源源不斷地傳遞出來,似乎自己就是一條負 重的河流,淘金船正將於積其中的泥沙撈起來,然后運送到某處。
我在橋面上佇立了許久,寒風像揮之不去的粘液,包裹著我的身體,體溫一點點地散失。 直到身體麻木了,我才挪動腳步,沿著黑暗中的道路朝著家的方向,繼續走下去。到第二天 早晨,再次過河的時候,那震耳欲聾的淘金船喑啞了,變得悄無聲息,像幾個通宵達旦的人 因為過度疲勞,終于睡去了。面對躺在透著寒意的河面上的淘金船,目睹它們似乎快要散架 的疲憊不堪的樣子,我不禁放慢了腳步,生怕打擾了它們酣睡似的,從它們身邊躡手躡足地 走過去。
在午夜回家的路上,我還能夠遭遇到另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也是一個生活中習慣了熬夜 的人。我和呼他老袁。當他的身影驀然出現在我面前時,也就意味著回家的道路走到盡頭了 。我租住的房子和他守門的一個加工編織的小廠緊挨在一起,而他并不是廠里的職工,也非 當地的“土著”。兩個漂泊的人就這樣因為某種緣份成了親密的鄰居。在沉沉夜色中,我租 住的那幢三層樓房只凸現出一個淡淡的、模糊的輪廓,仿佛一幅抽象水墨畫。窗前等待的燈 光因為困倦已經熄滅了,妻子和少不更事的兒子像鄉間最為常見的兩粒植物種子,帶著不為 人知的憧憬與遐想,沉睡在泥土一樣的黑暗深處。而一墻之隔的廠房內,熾烈的燈光宛若一 鍋金屬的沸水,蕩漾著,卻又是那樣悄然無聲。不大的廠房人去樓空。在空曠、闃寂的廠房 內,一個身影孑立其中,一會兒彎曲,幾乎貼著地面,一會兒挺立,艱難地伸展,似乎要突 破身體的極限,到達某種高處。這是老袁在一絲不茍地將編織袋打捆,碼堆。每次,我都要 在經過廠房的時候站立幾分鐘,默不作聲地注視一會兒。在夜色凝重的午夜,和我剛剛經過 的河面上的淘金船有的不同,老袁的忙碌幾乎不發出半點聲音,然而,他卻又多么類似一艘 淘金船,在生活的河流里,他也許比任何人更加夢寐以求淘出金子,從而使他黯淡的命運綻 放出熠熠光彩。他現在正處在生活的困難時期,有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撫養,要供他們 讀書,而他的妻子是一個啞巴,他的坐骨神經又像時好時壞的天氣,反復地疼痛。可以想象 ,壓在他身上的是怎樣一副難以承受的重擔。
有一次,我問他一個晚上有多少報酬,他告訴我針一個編織袋打捆并碼堆工錢五厘。粗略 一算,一個晚上所得無幾,在龐大的支出面前,幾乎為零。這讓我不禁為他通宵達旦近似徒 勞的忙碌惋惜起來,同時為他不堪重負的命運擔憂。但是,他并沒有我想象中那樣悲觀,沮 喪。他置信不疑,生活的前景定會云開霧散,一派明媚。“等兩個孩子讀書畢業了……”在 我們的談話中,這是他出現頻率最多的語言。或許因為這種信念的支持,使他對眼下的生活 變得極容易滿足。他的啞妻亦同樣如此。一天,我的妻子將一件半舊的連衣裙和高跟皮鞋送 給她,她立即忙不迭地穿上,高高地站在廠房狹窄的樓梯頂上,作遠眺狀。風將草綠色的連 衣裙吹得飄揚起來,像舒展開來的翅膀。她微笑著。在她傻呵呵的笑容面前,滿地的陽光似 乎變得黯然失色了。
倘若說河面上震耳欲聾的淘金船讓我感到震撼的話,那么,那些淘金船一樣在內心深處尋 找閃光文字的寫作者,則讓我感受到一份詩意的浪漫,而老袁——這艘在生活的河流上不吭 一聲的淘金船,讓我體會到的卻是難以言棕的沉重。
淘金船或多或少都會淘到金子,這僅僅是運氣問題,只有那倒霉透頂的才兩手空空,最終 一無所獲。如果不是淘金船而是淘沙船呢,結果又會怎樣?疑問的產生是后來的事情。我終 于發現自己的錯誤,那在午夜河面上震耳欲聾的并不是淘金船。有人告訴我真相,那是向艘 淘沙船而已,為附近的建筑工地提供泥沙和卵石,也就是說,這些通宵達旦轟鳴的船只,不 會而且永遠不會淘出哪怕是薄薄的一片金子來。這樣的事實,讓我陷入失望一悵惆之中。
這也是后來的事情。我和老袁的關系漸漸疏遠,其中的原因是我另找了棲身的處所。在一 個撒滿陽光的十月的下午,將近一年不見的老袁從泥土中冒出來似的,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神情頹唐卻又一身輕松的樣子。他告訴我一個令人驚訝、無法置信的事實:他的啞妻死了, 互于晚期惡性腫瘤。難道沒有一絲預兆嗎?我不相信病魔會潛伏得這么隱秘。死前一定非常 痛苦吧?我揣測著。老袁告訴我,應該有預兆的,死前也很痛苦,只是他的啞妻無法用語言 表達出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我想,不能夠將內心的痛苦說出來的人,應該是世上最痛苦 最無奈的人了。
過幾天就是他啞妻的祭日,老袁忙于買祭品,便匆匆走了。他走路的姿勢仍一瘸一拐,身 體不停地晃動,傾斜。我突然想起午夜河流上忙碌不停的船只來,因為負載太多,船向一邊 傾斜。抑或是另外一種情況,船突然空了,失去了重心。我選擇了后者。如今,老袁的兩個 孩子都初中畢業了,女兒在南方的發廊里打工,兒子在這個臨河的小城里當上了一名電器維 修學徒,他累贅一樣的啞妻也死了。壓在他身上不堪承受的重擔終于卸下來了。
這或許就是所謂的難以承受之重與難以承受之輕。當我陷入這類形而上的思考,便驟然之 間與那條緩慢流淌的生活的河流拉開了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