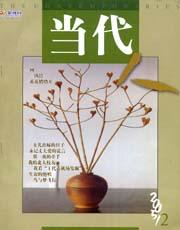秋天的飄落
朱靜輝
這個秋天里我去了兩次火化場,一個是送朋友,一個是老家來的堂哥,他來這個城市治病 ,就永遠地留在了這個城市。
我之所以對這個嚴肅的問題有了說的欲望,是我在這個秋天里感到生命的無常,生死的無 界限。盡管人一生下來就逐步邁向死亡,可聰明的人是不愿想到死,他們只想到如何生活的 更美好,在其一生中如何最大的占有財富,那個美麗的花環一直在遠處引誘著人們走向虛無 。
我的朋友是那么精致的一個女人,大學畢業后做廣告起家,是那種吃得了辛苦又拿的起放 得下的人。她掙有上千萬產業,開著“寶馬”,晚禮服和宴會上永遠是一襲旗袍在身的女人 。她開著車跑在每天都走的京津高速路上,這條她再熟悉不過的路,那晚她一定感到陌生, 高速路像一條黑色的帶子把她帶到了遠方。
出事的前幾天,我還見過她,那天,她穿了一件月白織錦的旗袍,一只翡翠的鐲子,白色 半跟跟皮鞋,墨一樣的長發在腦后挽一個圓圓的蓬松的發髻。臉有點蒼白,畢竟已是快四直 的女人了,但一份成熟的優雅使她依然美麗。那天她還對我說,找個時間,我們倆去北京三 聯書店,坐在二樓選個角落,要上一壺大麥茶,好好地看它半天書。我知道她是在找尋過去 的夢,找尋過去那份單純和寧靜。但這點愿望她都沒有實現。
前些年,我還一直關心她的個人生活,很是給她操了一陣心,但這幾年我希望她成家的念 頭像風一樣消失了,婚姻的列車已隆隆地開這,她莫名其妙地被遺落在站臺上。雖然現在事 業有成,人生的天地寬了,生活的空間卻窄了,看著那么實際的男人,我覺得能配的上她的 男人到哪里去找呢?有的男人是看上她的財,有的男人是看上她的色,有的男人財色都要, 婚姻的本質呢?這么多年在商海打拼,女友的戒備之心日甚。她逃不出女人的弱點,她曾夢 想過:有一個恩愛的丈夫,把這一切交給他打理,自己相夫教子,過一種簡單的生活,純粹 的家庭主婦的生活。說這話的時候,女友的臉部線條柔和極了,雙眼漾出的溫柔要把你化掉 。這對女人來說不難的生活,對她就是一種奢望。已記不清有多少次,睡眼蒙中,你被床 頭的電話驚醒,那端傳來女友的呼救聲,我知道她又走不出去了。等你趕到時,她像只貓一 樣蜷縮在那寬大的紅木床上,雙手冰涼。她會拿出那張身穿黑絲絨旗袍的照片,說是她死后 要把這張照片烤瓷后放在墓碑上。
女友有一句經典:“打點打點心情好重新上路。”只可惜這次上的是一條不歸路。
秋風把落葉一片片的摘走,拋向空中,在風中飄動的還有女友母親的白發,剛經過了一個 夜晚,她的雙眼已如枯井,單薄的身體是那樣無助,仿佛一陣風就會把她吹走。
秋天是讓人傷感的季節,特別是在秋天里送人到另一個世界去,就更感悲涼之霧縈身。
堂哥自到這個城市治病,就是我聯系的醫院,并找好的外科醫生給他做的手術。只可惜胃 癌早以擴散,生命還是被死神拽走了。這是一個命運多桀的苦人,不到三十歲老婆就跟上一 個運煤的卡車司機跑了,給他留下一雙小兒女,兒子還是個啞巴。為了不讓他的兒女受委屈 ,他謝絕了多少媒婆,除了種一手好地,他還趕一手好氈。冬閑時,他走村串戶去趕氈。愣 是把兒女養大了,女兒出嫁了,兒子還是光棍一條。他的勁一刻也沒有松,入院前,還在清 涼山修復古寺,大把地吞著止痛片,掙那每天四十元的工錢。
在他生命走過的六十個春秋里,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刻不停地旋轉著,曾經充滿 活力的生命,被消耗成一具空殼。如果你看到一個生命是怎樣一步步飄離的,你還能對生命 無動于衷嗎?那維持最低的生命體征,是那么頑強地堅持著,久久地在病房縈繞,那一刻, 我覺得人是有靈魂的,靈魂是在做著死亡前的儀式。
焚燒爐在這里公平地對待每一個投向它懷抱的人,不管他是富有的、貧窮的、高貴的、低 賤的,生命的莊嚴在這里得到了尊重和平衡。
堂哥的女兒執意要給他在這個城市買一塊墓穴,說是他勞累了一輩子住的還是那兩間上房 。
這個城市一塊最好的墓地是一個文化人搞的,他原先是一位省報記者,是屬于最早下海的 文化人,是那種下海后沒嗆水而逐步發達起來的極少數人。他是先開發房產起家,又逐步涉 獵餐飲,后來又開發了墓園,隨之又把這個城市的火化場接管了過來。用他一句話說:就是 我們給活人蓋完房子又給死人蓋。真正做到了一條龍服務。
說實話,墓園很美,綠草如蔭,花果飄香,分高、中、低檔墓區,所有的墓碑都被松柏環 繞。墓區的西邊是上百畝果園,北面是動物園,有孔雀和山約在高大的鐵網里散步,兩只肥 碩的棕熊在陽光下笨拙的挪著步子。墓園正北和東西兩面是人工堆的土山,高高地俯視著這 一大片墓園。
秋天的墓園是暖色的,果樹的葉子黃的耀眼紅的鮮艷,連陽光都是軟的甜膩。自踏入墓園 的第一步起,那低緩的哀樂就通過地下線路隨我們到達墓園的每一個角落,仿佛和我們一樣 在安慰亡者的靈魂。能在這里安息,該是活著的人的一個安慰。死亡在這里被定格成一塊塊 墓碑,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淡化成一種形式。
我的腳步倘佯在碑群中,目光所到之處,有滿含蒼桑的老者,在活力四射的青壯年,也有 那像花一樣嬌嫩的笑臉。如果靈魂有知,他們是否滿意這個陌生的家?
這個秋天我對落葉格外敏感,一枚不經意的飄落,也會使我的目光馬上蒙上一絲憂怨,也 可能有什么正恰和我的心情,這個秋天里我的心情有點糟,所到之處看到的也是一團糟。我 為了能在這個秋天里看到紀小嵐的故居、他親手植的那棵紫藤、那有愛情記憶中的白海棠, 一大早就趕到北京,看表時光還早,正是吃早點的時候,就順便拐進小胡同,來到一家南方 人開的小吃部,要了一屜包子,一碗小米粥吃了起來。臨桌是一對母女,看來女兒已吃完, 正坐等,母親吃的很慢,過了一會兒,女兒突然站起身走了,把還在咀嚼的母親晾在桌邊。 母親對著那南方小老板說:我對她主這幾天上火,想喝碗粥,她抬腿就走,還吃的我的退休 金。那小老板送過一碗小米粥,那母親喝了,拄著拐棍站起來說是等明天再給拿錢下來,就 一步一顫地走了。我望著老人微弓的背影,又想起她女兒那冷漠的面孔和青春健壯的身體, 是什么讓親情如此冷漠?
我打了輛出租直奔珠市口大街,大街正拓寬,紀昀故居院里的紫藤正暴露在街上,花和葉 子上已是厚厚的塵土,面目全非的老藤獨立于周圍的大廈下,顯得那樣不堪一擊。再向里走 ,正房被改造成一個大餐廳,幾十張桌面上,食客如云。這里經營山西各種面食,想來是經 營者借紀昀之名,把鈔票盡收囊中。
我在正房前被隔開的小天井里,找到了紀昀親手栽的那顆海棠樹,樹被擠在這小天地里, 是他的主人所沒有想到的。海棠樹長勢還算旺盛,葉子毛綠,海棠正紅著半邊身子,樹身有 頭號土碗那么粗,只是樹四周的墻上掛著好幾只空調的室外機,炒菜的油煙也向這方小天地 飄散,就這么長年累月的熏陶,也不知這海棠樹能抵御多少載風霜雨雪?
古都博大、深厚、具有帝王之尊,它寬厚似海,可容納百川。可它又有一種自傲時時在心 底沉渣泛起,藐視別的存在。
這個季節里,是古都最美的時候,連街上的落葉都別樣豐富,可我分明感到了生命中的另 一種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