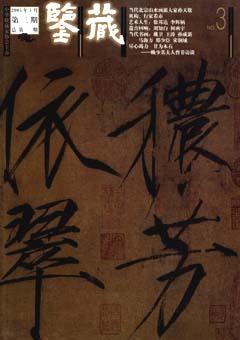大器晚成 厚積薄發
青 萍

邢少臣,字掃塵,1955年生,北京人。現為中國畫研究院專業畫家,中國美協會員。擅長畫大寫意花鳥畫,也常畫人物小品,風格高古清新,構圖絕妙。筆墨深邃有內涵,是當今國內大寫意花鳥畫領域頗具實力與影響力的畫家之一。
問: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藝術創作的道路?是受家庭的影響,還是出于天性?
答:我走上藝術創作道路是緣于偶然。我的母親是個農民,父親是個普通工人,我是跟著奶奶長大的,我既有農民寬厚忍讓的品質,又有工人堅毅果敢的性格。家里也沒有人從事繪畫、藝術創作。小時候,我沒有想過當一名畫家,做一名解放軍是我那個時候的最大夢想,但是我特別喜歡畫畫。最早我還是用鋼筆畫,照著小人書畫,比如《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等;畫秦瓊、畫張飛,看什么畫什么。
問:對于您從事藝術創作,您的父母、家人持一種什么態度?
答:我父母對我的態度很寬松,我前面說到,我是跟著奶奶長大的。奶奶對我特別疼愛,她常說:“你呀,我看了,一定能畫出來的,只可惜我看不到了。”這句話對我的觸動非常大,它成了我繪畫的動力,我就是這么認認真真地走過來的。(說到這里時,邢少臣的眼圈有些紅了)
問:我聽說您很小的時候說過,您的畫也能在美術館展覽,是嗎?
答:是的,大概在上世紀60年代,有一屆全國美展在美術館舉辦。上美術課時,老師帶我們去美術館看展覽。剛走進去,我就萌生出一個想法:“他們的畫能掛在這兒展出,將來有一天我的畫也能掛在這兒。”我這樣想了,也不經意這樣說了,直到今天我的有些同學還記得我當時所說的這句話。那時我確實產生了畫好、要好好畫的念頭,我想,我踏上藝術創作的道路就是緣于那個時刻吧。從那以后,我更是天天畫畫,慢慢地我就認識了什么是國畫,什么是油畫等等。

我上過師范,讀過美術專科,別人畫畫是畫面,而我動手就是線;我對中國畫有一種很自然的興趣。后來跟著盧老學畫,對中國畫的認識逐漸深刻起來,知道了什么是中國畫,也對線更執著了。
問:您認識了不少大師級的老先生吧?
答:我比較幸運,在20世紀70年代陸續認識了任先生、盧先生、齊先生,以及今天被譽為大師的崔子范老先生和董壽平等老先生,并得到了他們的教導與指點。
問:您跟崔子范先生學了多久畫?
答:我跟著老師學畫,最長的是崔老:從開始學到1988年調入中國畫研究院,大概有十年的時間。之后也從未間斷,一直跟著他學習。從他那里,我學到很多東西——他的觀念、他對筆墨的感覺,以及他對中國畫的特殊貢獻,都使我受益匪淺。所以說,我學畫的根是從齊白石算起,后來逐漸受崔老影響。那時候,我也去苦禪先生那兒看他畫畫,因為先生的很多學生和我都是好朋友,大家互相之間都有交往。
問:您對筆墨是怎樣理解的?
答:我對中國畫有一定認識后,就對傳統的中國繪畫進行了長期的、多層次、多方面的探討和研究。從兩宋到明清到近現代,幾十年間從未中斷過,也從中領悟了很多東西。我感覺大寫意就是筆墨兩個字。筆墨看似簡單,其實包容卻很多、很大。筆墨是無聲的,沒有語言,但是通過筆墨能夠看到畫家的文化、學識、修養、閱歷和社會積累。初學者看筆墨,感覺筆墨好像是很難撼動大山一樣,很難學,很難掌握:而中年人對筆墨已經很純熟了,怎樣去發揮自己的特長,怎樣使作品更美、更具內涵,怎樣才能發揚民族文化,這是一個中年畫家考慮的問題;而作為八九十歲的老畫家,他們留在紙上的就是幾十年的文化積累、人生積累和對藝術的認識,初學者是達不到的。
筆墨是一種文化,我們不能單純地看這兩個字。比如有些人,他們的筆墨表現得比較張揚、跋扈、霸道;有些人的筆墨表現出一種飄浮、怪亂、滑軟;而真正的中國畫的筆墨講究的是內涵。這種內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佛家的出世思想,道家的現實思想,儒家的中庸精神。具有這種文化精神的筆墨,絕不是飄浮的、亂怪的、張揚的、霸道的,而是綿里藏針、外柔內剛、充滿厚度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強調內涵和沉淀,期望能夠達到不溫不火,不急不躁的完美的筆墨意境。

問:您常常談到厚積薄發,而現在很多的中青年畫家追求的是“快”和“出新”,對此您是怎樣理解的?
答:齊白石先生60多歲時還默默無聞,吳昌碩先生40多歲才開始學畫,但是他們對藝術的追求從未間斷過。當幾十年的磨練、生活積累,以及個人修養積累得非常豐厚時,才有后來的厚積薄發。而現在的中青年畫家,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急于求成,畫了幾年就想成名。雖然短時間里,他們也名噪一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也就銷聲匿跡了。還有的年青人名氣大了,就滿足于自己取得的成績,這樣是不容易進步的;一種風格形成了,也不容易改變。雖然所有的畫家都想成為藝術大師,但大師不是爭、搶、奪、封來的,它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有的人在世時可能名不見經傳,但日后亦可能大放異彩。
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從中汲取營養,才能水到渠成,才能有所創新,否則只會是空中樓閣。我每天練畫,中國的大寫意畫,在60歲以前是不容易畫好的,因為真正的大寫意是需要積累、沉淀和錘煉的。我現在只有50多歲,我還要練,我始終認為,沒有積累就達不到真正的大寫意境界。放慢腳步,一步一個腳印,不追求名利,這是我所追求的。
問:您當時調到中國畫研究院時還很年青,您對自己取得的成績是怎么看的?
答:我是1988年調到中國畫研究院的,當是我33歲,很年青,這在當時也算是一個奇跡吧。我沒有經過專門的美術院校的學習,只是通過傳統的學習方式,研究歷史和古人,自己加以領悟和體會,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從一個業余的畫家成為一個專業的畫家,在這一點上我很感自豪。我個人認為學院里培養的寫意花鳥畫家,很少有畫得出類拔萃的。我主張臨摹大師的畫,比如齊白石老師的畫,就是從“八大”演變來的。我認為只有學到根本,再從根本上演變過來變成自己的東西,具有自己的風格,這樣筆墨才完美。

中國有句諺語叫“春捂秋凍”。在藝術上,我一直遵循著這句古老的養生道理,以不變應萬變,抱著堅定的態度畫傳統。幾十年來,我一直未放棄對傳統的熱愛,我始終認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把傳統學到根本,筆墨才更有韻味;只有自然,才能出新。現在很多的中青年畫家,他們的作品看起來很新,可讀起來很乏味,所以我一直是堅持這個觀點——踏踏實實地學。“出新”是自然而然的;“變”也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你的作品不中不西、不倫不類,那么國內國外也不把它當回事了。所以,我一直在講,對藝術要執著,不被任何理論、任何風格所左右。
問:您說畫大寫意與性格有關,畫大寫意一定要心胸開闊嗎?
答:是的,大寫意畫家一定要心胸開闊,要有豪氣。但是這種豪氣并不是蠻橫,是有內涵而不張揚。有的人文化修養不夠,其畫就張揚有余而內斂不足,很浮躁,不能使看畫的人身心寧靜,這樣的畫不能算是大寫意。真正的大寫意用筆雖然很簡單,但其意義卻很深遠,富有哲理、文化、民族精神和禪意;一幅好的大寫意作品一定是有韻味,有厚度,有可琢磨的地方。
問:您的學識和修養是通過讀書,還是通過跟老師的交流來提升的?
答:我喜歡讀書,但大本的理論著作我只是找其中的精華的句子來讀,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是老師教的。我特別喜愛下圍棋,下圍棋對我的繪畫有很大的幫助,從圍棋中我悟出了很多畫的道理,也從畫中悟出了很多棋的道理。棋中分高下,棋子是一個都不能輸的。很多棋中高手,往往在對方很迷茫的時候下一著妙招而險中求勝;而有時呢,也因一招不慎而導致滿盤皆輸。因此,下圍棋需要有一種拼搏感和敏銳的觀察力。另外,圍棋的黑白、方圓和圍棋的點線面都和中國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我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真的是包羅萬象。
再有,就是我掌握的國內外的信息比較多。國內每一個畫家近期的作品,其風格特點,以及他們最近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研究什么,我都非常清楚。只有了解別人在做什么,我才能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問:有人認為大寫意畫家作畫太容易了,寥寥幾筆即為一幅畫作,您對此是怎么理解的?
答:大寫意畫家確實能夠在兩三分鐘內作一幅畫,甚者可以在一分鐘內作一幅畫。但是,大寫意畫背后是畫家幾十年來對社會、對人生、對自然的理解,是幾十年的筆墨磨練。畫面的快慢是根據作品的需要來決定的,有時需要快,有時需要慢,有時需要粗,有時需要細,也有抑揚頓挫,輕重緩急。因此,看大寫意畫不能從表面上去看,而是要從大寫意以外去了解。
問:聽說外國友人來參觀時,看到大寫意畫家幾分鐘就完成了畫作,認為大寫意畫“物非所值”,您是怎樣看的?

答:中國大寫意畫是一種文化,不能以快慢來衡量其價值。在一個外行眼中,作一幅大寫意畫確實很快,認為作大寫意畫很簡單,這是走入了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另外,作為一個大寫意畫家,雖然處在商品社會,也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作畫不是做表演,不能為了眼前的利益放棄作畫的分寸和作品的好壞。
問:有人說中國畫是需要“養”的,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認為這個“養”其實是修養。中國畫與西方繪畫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中國畫的筆墨是一種文化,很深邃;而西方繪畫的筆觸雖然很美,但它只是一種技巧。從畫中看到文化,非中國畫莫屬。
問:對于石濤講的“筆墨當隨時代”,您是怎么看的?
答:任何一個時代的畫家,他的筆墨都是跟著時代的節拍的,不會有悖于這個時代,因為他所接觸的、所感受到的都是時代賦于的。雖然我們中國畫講究學習傳統,但每個畫家的作品都潛移默化地受當時的文化、政治背景所影響,決不會脫離本時代。
問:對于“搜盡奇峰打草稿”,您是怎么看的?
答:畫家肯定是要游歷名川,陶冶性情的。而我從上完師范大學后就不寫生了,這是我和其他畫家最大的區別。小時候上動物園寫生,我也喜歡帶著宣紙和筆墨直接畫,我覺得鋼筆表達不出我的情感。我習慣于先看,對自然有了感悟后也就裝在腦子里了,然后把它直接變成筆墨;其實中國的筆墨就是意象派,它比西方要早得多。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方式,每個人追求的目標不同,發展的方向也不同,只要不偏離自己的軌跡就可以了。
問:迄今為止,在藝術上您經歷過大的變革嗎?
答:經歷過兩次。第一次大概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時我二十五六歲,我的寫意花鳥畫在北京畫界已小有名氣。北京美協收藏的我的一幅《秋酣圖》,構圖簡單,用筆老辣,很有立意,那時我的繪畫上了一個新臺階。
1988調入中國畫研究院以后,我也有一般人的想法,要創新、要出新。那時興起了一種“點彩”派的畫法,因此我就把傳統放下了,這樣嘗試著畫了近兩年。畫這樣的一張畫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我很快就意識到這種畫法和我自己的性格相背離,于是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還是堅持從傳統中把握自己,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而且研究院的工作使我的眼界更開闊了;眼界打開了,思想也就活了,對我畫中國畫幫助更大了,這使我的創作又走上了一個臺階。
問:對于一個畫家來說,刻苦和悟性哪個更重要?
答:一個畫家如果沒有悟性,再怎么刻苦其作品也總是平庸的;但是,如果一個畫家只有悟性而不刻苦,就不會有作品出現。所以,刻苦和悟性對于一個畫家來說,是同等重要的。悟性有來自天賦的,也有通過后天培養使其提高的。
我觀察生活的方法和一般畫家有所不同,我有一種更深層、更細的觀察。在上世紀80年代我畫的幾張大寫意畫中,有一幅《年夜》畫的是一簸箕餃子和一壺酒,還有一幅《息》畫的是一把梯子和兩只小雞。這些畫的構圖雖然很簡單,但生活氣息很濃,立意也很高,當時的美術雜志和美術文化報都發表了這幅作品。而這幾年精彩的畫作并不多,我覺得作為一個畫家,只有善于挖掘生活,善于抓住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耐人尋味,才能打動觀眾。
此外,在墨色上我也打破了前人墨色變化的復雜性,追求簡單的墨色,敢于用重墨、濃墨,以增強視覺的沖擊力。我偏重黑色,努力使黑而不僵,聚而不散。
問:您覺得自己的畫容易仿嗎?
答:可以,但是只畫了三五年畫的人要模仿是不容易的。仿畫,最重要的是了解畫家本人,否則只會是“形似而神不似”。
問:您是不是廢了很多畫?
答:是的,李可染說“廢畫三千”,我撕的畫何止3000啊!一個好的畫家只有敢于否定自己的作品,經常對自己的作品持否定態度,才能不斷進步。此外,還要對自己的好作品進行不斷總結,只有具備了精晰的分辨能力,自己才能得到提高。
問:崔老對您的畫是怎樣評價的?

答:崔老對我的畫評價很高。大概在我22歲時,我畫了一張畫,崔老看了以后,題款是“少臣同學畫,章法新穎,筆墨蒼潤,格調高超,順此前進,定能自成一家。”前年在美術館聯展時,崔老對在場的很多畫家說:“少臣是我最得意的學生,也是我最重要的學生。”如此高的評價,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很感激老師對我的培養與評價。
問:齊白石先生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崔老先生介意您的畫與他相似嗎?
答:崔老的筆墨對我的影響很大,特別是他的用筆。但是我還是覺得我的風格跟他有很大不同。我二十多歲時,劉院長到我家去,看到我畫的一幅畫——畫面是一只睡著的鴨子,很喜歡,于是向我要去掛在自己家里。高先生當時是美院教授,已七十多歲,在他家看到這幅畫時,也大加贊賞。那時,我對中國畫已悟得很深了,經過這么多年的積累、沉淀,我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這點上我還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問:“尋門而入,破門而出”,你覺得自己現在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
答:我覺得自己現在在“出”與“入”之間。我的作品是很傳統的,表現的都是生活中的細節,很自然也很具有新意,這跟自己的觀察方法和悟性是分不開的。
問:您最早臨的是誰的畫?是每個時期都臨嗎?
答:我最早臨的是齊白石的畫,后來臨的是“八大”、吳昌碩。我臨畫主要是臨畫的精神,我知道怎么去看,怎樣起筆,怎樣收筆,臨“八大”幾乎可以亂真。臨的時間很長,實在是太喜愛了,覺得他們是用心在畫畫,從畫中可以讀到畫家的內心,這是中國畫的最高境界。我們學習傳統,要注意去粗取精,去其糟粕,留其精華。而有些人不具有分析能力,現在很多地方的宣傳誤導又太多,很多作品不倫不類的,對這樣的作品進行標榜、臨仿,是不會受益的。
問:您是在有靈感時作畫,還是把它當作每日必做的功課?
答:靈感是不定期出現的,在平常中也能感到新的東西,所以我并不拘于一格。“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一個好的寫意畫家,只有多練才能有好作品,因此作畫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課。
問:現在有些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流失感到擔憂,您是怎么看的?
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些東西的流失是必然的。但是它的根,它的精神并沒有流失,對這一點并不需要過分擔憂。中國畫是一種藝術,并不是一顆小草,它有很雄厚的根基和廣大的文化背景,我堅信我們及后人一定會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一代一代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