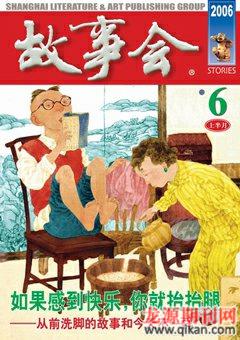難忘一面之交
閆金城

若非我遇見了,我難相信有這樣的一面之交;若非我相信了,我難理解有這樣的赤誠之人。一枚金燦燦的紀念章、一個破碎的筆筒,靜靜地告訴了我:他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救過局長
同事老宋請我吃飯,席間一位彌勒佛似的老頭問我在哪兒工作,我告訴他:“以前在鄉下學校,最近調到縣教育局了。”老頭立即興奮地說道:“教育局我有個熟人!還是多年的好朋友呢,叫李立,小李子,就是你們的李局長。”
“別聽他的!”東道主老宋拍拍我的肩膀,帶著幾分醉意說,“他呀,誰都認識,就是不認識自己!來,喝酒,喝酒。”
“哎,小宋,你可別這么說!”他漲紅著臉爭辯道,“小李子和我稱得上是患難之交,十年前,他出了車禍,是我及時把他背到醫院的。那時我把小李子送到急救室,一直照顧到他蘇醒過來,我偷偷給小李子輸過300毫升血,還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雞宰了給他補身體……后來小李子到教育局上班……”
這與我在機關里聽到有關李局長與群眾水乳交融的傳聞十分吻合,我完全相信了他所說的一切,忙舉杯問道:“咱別喝糊涂酒,請問您老貴姓?”
“哈哈……叫我老陳頭吧,小伙子,我們有緣啊!”他大笑后,小聲對我說道,“以前我也在教育局工作,剛才你說你老婆想要吃高粱米干飯、喝玉米兒粥,這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正好要去農村看孫子,在兒子家順便給你弄幾斤,再讓老宋給你捎去!”
誰動了我的自行車
散席時,我發現那輛放在樓下的自行車氣門芯被人拔掉了!為了不給大家添麻煩,我沒聲張,自己悄悄推上車子走了出來,剛拐出胡同口,老陳頭騎車搖搖晃晃地從后面攆上來了。
“小閆,騎上走呵!”
“您先走吧,我車的氣門芯叫人給拔了。”
“啊?誰這么缺德?”他的車子圍著我轉了一圈,“我給你回去找找。”
我急忙攔住他,說:“準是淘氣小子干的,沒法找啦!”
“那……”他下了車,醉眼蒙地瞧了瞧我,忽然拍了一下車座,“有了!把我的拔去,我家不遠!”
不等我阻止,“嗤兒”他已經給自己的車放了氣,擰下氣門芯就往我的車上安。 我哭笑不得地說:“嗨!你擰下來也沒用,黑燈瞎火的,我到哪兒去打氣?”
老陳頭一聽,也傻眼了。這下可好,兩輛自行車都推著走吧!就這樣,他到了我家門口,我確實過意不去,請他進屋坐坐,喝杯茶再走。

妻子還沒睡,見我領回來個客人,便忙著點煙、沏茶。
老陳頭看見我桌頭擺著許多稿件,他笑瞇瞇地問:“作家?”
妻子在一旁插嘴道:“可不坐家咋的,就知道在家坐著,外面事一點也不行。這不,到局里工作快半年了,人事關系還擱在學校里,也不知找領導催催!”
糟糕!她把我最不愿為人所知的一樁事情給抖出來了,我到教育局工作,當初談的是先借后調,可是,試用將近半年了,仍不見有調的動靜。
老陳頭正色問道:“怎么,你的關系還沒轉到局里?”
“還沒……不過,快了,快了。”
老陳頭拍著大腿說:“嗨,你咋不早說呢?這事兒你找我嘛!”
妻子的眼睛頓時一亮:“大叔,你能給說上話?”
“太能了!我和他們的局長很熟哩!”大概怕我妻子不相信,老陳頭又鄭重地向我們夫妻敘述了一遍他與李局長結識的過程。
“哎喲,大叔,以前就少了你這么個接洽人哪!”妻子喜出望外,還把家里唯一的5000元存折交給了老陳頭。
“還用這個?這事交給我就行了。”老陳頭連連擺手,滿口應承道,“別說咱爺倆兒還有一面之交,即使素不相識,這個忙也應該幫!我明天就去找小李子,爭取早點把關系轉過來。”
拿走玉瓷筆筒
妻子死活要讓老陳頭把存折帶上,在他們相互拉扯中碰倒了桌上的筆筒,老陳頭扶起筆筒驚奇地問:“你從哪弄來的?”
這個玉瓷筆筒并不值錢,我見老陳頭如此喜歡,便笑著說:“如果你喜歡就拿去吧!”
老陳頭喃喃地說:“你不懂,這是文物,我在小李子家看到一個……可小李子說它原先是一對,好像叫什么‘鴛鴦來著……這回,你的事情就不用愁了!”說著他小心地把它揣在懷里。

第二天下班剛進家,看見妻子高興的樣子,我以為是工作調轉的事有了著落,忙問:“是不是老陳頭把事辦成了?”妻子卻責怪我說:“你也太心急了,昨天答應你的今天就給辦成?是老陳頭給咱送來10斤高粱米和10斤玉米兒,說他今天到鄉下看孫子捎來的,我給他錢說什么也不要,說自家種的不要什么錢!”
我一聽,嘿!這老陳頭還真能辦事,看來,我調轉的事老陳頭準能辦成。等辦成后,我一定要登門好好感謝他。
一個多月后,教育局以“不適宜在教育局工作”為由,通知我“即日交待工作,返回原學校報到!”李局長找我談話,說:“小閆同志,當初我們考慮調你,主要是想加強基教處調研的力量。當然嘍,這都怪我們事先沒細致地了解情況,最近才聽說你搞文學創作,發表不少作品,這……固然很好……可這是教育局而不是文化局啊!”
我這才意識到,老陳頭呵老陳頭,你是怎么替我吹的喲!懊惱之下,我去找老宋,老宋聽后搖搖頭,說:“老陳頭,他哪兒是辦事的人喲!這個人是什么人都認識,可又什么事也辦不成。”
“那,他是干什么的?”
“原來是教育局燒鍋爐的臨時工,后來人老了自己就不干了,他成天蹬三輪給人家拉貨……那次我搬家,他前后忙了半個月,我給他300元錢表示謝意,可他說什么也不要,上次請客就把他捎上了。人是好人,就是有點破車好攬載……”
我說:“老陳頭辦事還行,上次喝酒時我隨便說一句我家那位想吃高粱米干飯、喝玉米兒粥,沒想到第二天他就從農村兒子家給我送去了!”
“行啥呀!”老宋苦著臉一笑,搖著頭說,“他就一個兒子在縣酒廠上班,農村哪還有兒子!他讓老伴也給我送了,無意中他老伴說漏了嘴——原來那是老陳頭到農村花高價買的。”
打開這個手帕包
我離開教育局回到了鄉下學校,一天,老宋帶著一個年輕人來到我家,說:“這位是老陳頭的兒子,來找你的。”
我看著那個左胳臂上套著黑紗的年輕人,好奇地問道:“你找我有事?”
那個年輕人悲傷地說:“我爸昨天歸天了,他臨走前讓我把這個交給你!”說著將一個手帕包遞給我,我接過來左一層右一層地打開,眼睛頓時直了:里面是一枚金光閃閃的抗美援朝紀念章,下面是一個破碎的筆筒。

我不解地問:“這……這……為什么送給我?”
那個年輕人說道:“那天你家大嫂非讓我爸拿錢去辦事,爸以為這是信不過他呀,當看到桌上的筆筒就隨口編出那些話,他是想事成之后再把筆筒還給你,哪承想事情讓他給辦砸了,爸幾次想把筆筒給你送去,可一走到你家樓下,就覺得沒臉進去,最后那次鼓起勇氣敲開你家門后,卻聽說你搬到鄉下去了,爸一陣內疚,筆筒掉在地上碎了。”
我擺擺手,告訴年輕人,那個筆筒并不值錢。
年輕人抽泣著說:“我爸并不知道那東西值多少錢,他四處求人買也沒買到。家里為了給爸看病已經傾家蕩產了,最值錢的就算這個紀念章,他讓我把這個和筆筒一起帶來……我爸臨終前對我說,他一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了。”
老宋壓低聲音對我說:“在老陳頭病重時,我去看了幾次。每次老陳頭都拽著我的手一個勁地自責道:‘小閆的事……我給辦砸了……對不住他啊!”
望著手里這枚金燦燦的紀念章和那一堆破碎的筆筒,我突然理解了老陳頭所做的一切……
(題圖、插圖:安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