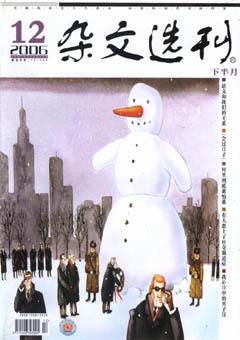報紙拼圖等
韓松落等
報紙拼圖
我還喜歡窺看一個人的命運。某個單位,某個人,在我在這城市的十三年里,始終給報紙寫新聞稿,開始,他剛從大學畢業,顯然是在新聞宣傳的崗位上,掛的是“通訊員”的名頭,三年后,成為“特約通訊員”。這段時間,總是有不同的人名字掛在他前頭,再過了三年,他成了“特約記者”,他名字前的那些名字都消失了。每年年底,報社都會邀請這些特約通訊員、記者寫寫感想和新年寄語,他一次不落,于是我知道他結婚了,愛人在哪里工作,有了兒子,在哪里上幼兒園,兒子后來又上了小學,那小學還邀請了他們單位的人去做安全教育講座,顯然也是由他撮合,這新聞也上了報紙,還是由他撰寫。我饒有興趣地在暗地里打量著他,而他一點也不知道,他的稿子所涉及的場合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高,篇幅越來越長,顯然他在不斷升遷,有段時間他的新聞都發生在小縣城,顯然他是去掛職鍛煉了,于是我再打電話到他們單位去找他,得到的答復和我的猜測完全一致。再回到城里,他的新聞稿,是他的名字署在最前面,一些陌生的名字掛在后面,我于是在街上打公用電話到他辦公室,祝賀他當上局長,“你是誰?”他警覺地問,“一個老朋友,”我回答。放下電話,我把手插進風衣口袋里,感覺自己像是漢尼拔,剛給斯苔琳打了電話。
白天黑夜,我是謙卑的小職員,活在剃刀邊緣,而在沉默地翻看著報紙的那瞬間,在探究那些冰冷的新聞故事后面的細節時,在將這些故事以我的方式重新書寫評說時,我似乎掌握了這個城市最隱秘的鑰匙,我驕傲地,笑出了聲。
漫長旅程
我們這個城市,在八月里,又一次舉世聞名。
公交公司放出風來,因為他們嚴重虧損,將擇定吉日,限量發放十萬張公交IC卡的預約單,在發放那天,有一萬多人去排隊。公交公司的柵欄被擠變形,人們向著施恩的人伸出如林的手臂,有人攀爬到兩米高的柵欄上,人群散去后,滿地都是鞋跟和鞋底。
這張卡具有什么魅力?每張可以享受25%的優惠,就是說,每次坐公交車,使用這張卡,可以節省兩毛五分錢,如果一天乘坐兩次公交車,就可以省下五毛錢,一個月就將省下十五塊,如果一天乘坐四次公交車,就可以省下一塊錢,一個月就將省下三十塊。就是這樣,就是為了這十五塊、三十塊,這個城市,有一萬個人去排隊,去領取預約單。
我媽媽如果在世,一定會去排隊領取預約單,她會在大清早就拿上她的花布袋子,在埋怨我們的動作不夠麻利中出發,她將頭發凌亂地回到家里,并且抱怨說,她應該也像別人一樣,凌晨四點就去現場排隊,一個月省下三十塊,一年就是將近四百塊呀!她總是這樣心思敏捷而痛心疾首地計算著,而我們總是臉色緊張地望著她,不知道她還將計算出什么驚人的結果。
我大姨也一定會去排隊。她曾經是紡織女工,在紡織廠倒閉之后,憑借她是熟練工,找到一家制作毛刷的廠子,往木板上扎毛,在生了病以后,聽憑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的那些江湖騙子,把手里的錢騙了個精光;我的姨夫曾經是機械廠的工程師,在機械廠倒閉以后,憑借他是工程師,去廣東找工作,誰會要五十五歲的人來做工呢?試用期一滿,他們就不要他了。他總是寫密密麻麻的信回來,計算著,這個月又有一個暖水瓶沒有從做工的工廠宿舍拿出來,又不得不交了五百塊錢押金。
我大舅三舅也一定會去排隊。他們有穩定的工作,讓人羨慕的收入,只是,自從他們不聽勸阻,一定要往股市里投錢以后,不過兩年,他們都成了赤貧階層,他們不聽我的勸阻,繼續購買股票,繼續生孩子,繼續走夜路。
我的遠房姨也一定會去排隊。在我少年的時候,她就擁有了一千度近視,她出身還算不錯,可是,因為這一千度,她從沒找到一份可以久做的工作,從沒找到一個耐心地陪在她身邊的男人,她也一定會去排隊,一定會被人把眼鏡擠掉在地上踩個粉碎。
而我已經逃離,從他們中間逃離,再也不想回頭望上一眼。而他們還停留在那里,等待排隊,等待股票上漲,或者等待一張一年以后才會發揮效用的公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