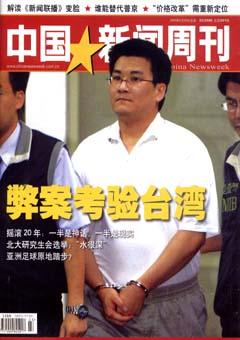稅收增長與經濟可持續發展
稅收超速增長背后的故事
高培勇:1994年以后,中國稅收呈現一條“魔方”式持續高速增長軌跡。世界稅收史上,收入跳躍式增長往往是稅制變革的結果,而中國持續12年的稅收高速增長是在稅制基本未作任何大調整的背景下發生的。我認為,當前稅收高速增長是整體經濟增長、物價上漲、稅源結構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均衡、加強稅收征管和進出口不平衡等六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真正有點特殊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地方是在加強稅收征管、拓展增收空間上。中國現行稅制誕生之時,中國政府在1993年亟待解決的矛盾主要有二:一要應對嚴峻的通貨膨脹,二要扭轉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滑勢頭,因此“增收”成了稅制設計時的一個重要著眼點。考慮到當時稅收實際征收率只有50%,在“寬打窄用”的理念下自然預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間。2003年實際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10年間提升了20個百分點,稅收收入肯定也要呈現相當的增長。正是出于這樣一個原因,關于中國稅收的故事才特別耐人尋味。
賈康:中國財政收入90%以上是稅收收入,稅收增長離不開經濟基本面形勢,要看整個經濟的成長和效益能否支持這樣一個發展趨勢。改革開放前十多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下滑的,最低點在1995年,然后比重一路上升,現在已經上升到調整后GDP的20%左右。從經濟基本面來說,改革開放要經歷痛苦的調整就必然有一個放權讓利、放水養魚的過程。改革十多年后,90年代中期的中國經濟運行規范性提高了,機制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點發育,加上市場經濟各種因素相互間的激蕩,開始進入了效益收獲期。這幾年,所得稅的增長非常強勁,內外資企業都是快速增長,以前稅源主要靠沿海,現在西部地區稅收增長已經超過沿海。改革開放20多年,前期的很多因素對現在稅收增長肯定有貢獻,正是宏觀經濟基本面多種因素集合在一起支撐了稅收全面增長,這樣一個大的趨勢,總體而言是正常的。
彭龍運:稅收這么快的增長,能不能持續,能持續多長時間?許多人認為是不可持續。但是事實上一分析會發現這個速度的確可以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經濟風險因素可以看到,經濟基本面是支持這種高速增長的,估計十年內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不會有改變。從經濟結構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的高速發展階段,特征是資本投資的高速增長和非農產業的比重快速提升,而中國稅制安排恰好是對這些非農產業采取高稅率,經濟結構變化也是有利于稅收增長的。綜合判斷,如果這些因素同時起作用的話,只要經濟基本面不改變,預計稅收增長再持續十年是沒有問題的。
袁鋼明:稅收是資金集聚,或者是一種分配方式,財政資金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資源集中速度過快,經濟理論上從來沒說稅收快速增長一定是件好事。政府的考慮與企業微觀的考慮,或者國家與居民個人的考慮,角度都是不同的,政府拿走的資源過多,可能會打擊人們的積極性。到底是激發個體的生產積極性重要,還是集中資金公共支出更有效,這時候需要找出一個平衡。現在世界上稅收和財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絕不可占到三分之二。我們國家掌握的公共資源部分已經上升到世界高位了,按照稅收計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較寬廣的定義大概占GDP 30%以上。現在稅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長,那么很快就進入世界上高稅收國家了。現在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增長,財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長只有6%,財政收入增長背后是居民的負擔和壓力在成長,而國內消費難以啟動。經濟能不能持續應該與人民收入和消費能不能承受有關系,如果財政增長過快,影響到消費需求,經濟必然受影響,這就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要及時調整稅收的增長。如果居民收入能同步甚至比財政更快地增長,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追求稅收過快增長不利經濟結構轉型
賈康: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長好的情況下,應該更加關注怎么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是最長遠、最關鍵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成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各地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粗放型的擴張,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不能滿足當前這種方式下的收入增長,現在的滿足會隱含一種危險:如果只看到財政情況好而沒有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今后一旦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瓶頸變成非常現實的因素,整體收入就可能要掉下來。那時候就會發現,前期做的很多工作要讓全社會去付出代價了。
袁鋼明:財政增長快了,是不是經濟就真的活躍了?現在政府的產業安排,各種各樣的目標設置,各種具體工作的執行,都以稅收收入增長為最終評價目標。很多地方的經濟就是以財政增長為主導,選擇產業第一個問題要看是否有利于地方財政增長。結果發展成為只有稅收增長了當地經濟才能增長,只有實現了稅收才會把錢投到那里去,社會大量資金集中配置到稅收高的產業,比如各地的房地產業。現在稅收增長高的地方獲得的外部資金比實現的稅還多,這種稅收背后有很多人為的安排。于是,欠發達地區跟發達地區完全是兩個世界,發達地區拿著大量資源去獲得一定的稅收,欠發達地區既沒有稅收又拿不到資源,財政金融體系不愿意改造投入多產少出的地區,更愿意把錢投到北京、上海、廣州,甚至投到香港去。因此,我們是在用稅收資金甚至稅收以外的資源在培植現在的稅收。這些年高投資、低消費、低物價、低收入、低福利的結構是一種低效益擴張,一種讓老百姓受損的歪曲。現在繼續追求財政收入增長,用擴大生產的形式拿走稅收,再把大量貸款投入到低效投資中去,這種高投入、高增長的模式難以持續。
減稅是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點
高培勇:福布斯雜志公布的所謂稅收痛苦指數,把中國排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國稅收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之所以會引起廣泛的關注,是因為它事關GDP在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分配格局,牽涉中國宏觀稅負的判斷,故而,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有重大影響。由稅收持續高增長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歸結為現行稅制能否適應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我們面對的所有的經濟制度中,稅收制度應該是與時俱進最強的那一類。換言之,稅收收入持續十幾年的高速增長,給我們一再傳遞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加快全面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所有問題都應在現行稅制的與時俱進中得到驗證,得以解決。
張曙光:持續這些年的稅收高增長,而且增長幅度那么大,確實是個問題,現在有必要研究一下減稅的實施辦法,以利于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減稅辦法里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領域,一個是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一個是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這兩項改革涉及到每家企業,既可以有效降低稅負,激發企業的活力,又利于塑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平衡國內外需求。現在應當在財政比較寬裕的條件下盡快推出。
經濟結構轉型強調擴大內需。內需和外需是緊密相關的,如果外需那么強勁,拉動增長的作用那么明顯,內需啟動就會很困難。現在出口增長那么快,引資那么多,同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密切相關。現行稅收政策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外資企業所得稅率15%,內資企業是33%。這樣的結果是外資進來了,出口增加了,外需在許多地方支撐著當地經濟增長,內需提升還有空間嗎?如果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到比如25%的標準,對國內企業是一種重要的激勵,對外資企業也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國民待遇。現在中國宏觀經濟循環潛藏著非常大的風險,出口大量貿易商品換回美元紙幣,然后投資美國的債權,美國拿這個錢到中國來買中國企業的股權。債權的收益是3%,股權的收益是10%,這樣一個循環,對中國相當不利,我們能夠從中間得到的貿易利益很少。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呢?部分原因是我們不恰當的免稅優惠政策造成的,對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了,今年政府財政收入已經3萬多億,把減稅政策推開是時候了。
安體富:現在的稅制結構本身就會帶來稅收高增長。原來為了保證財政收入因此名義稅率設計得比較高,稅收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稅基本稅率17%,折合成消費型稅率一般是23%,西方國家多數低于20%,而且我國的生產型增值稅是生產投資重復計稅,當然增長比較快。企業所得稅,我國是33%,歐洲國家多為29%左右,德國、澳大利亞經過這幾年的改革都低于30%。國外稅負扣除很多,有折舊、工資扣除等等,這個比稅率還重要,而我國所得稅中勞動工資、資本故障、風險故障、研發費用都不是足額扣除,這樣我們實際稅負比很多國家都重,經濟增量當中被稅收拿走比較多。以每年稅收增量對比GDP的增量,1994年這個比例低于10%,1999年就提高了,相當于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被稅收拿走了。現在創新型國家、增長方式轉變實行起來非常困難,也是因為企業沒有這個財力,沒有這個條件。要支持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趕快實現增值稅轉型,用合理的稅制去鼓勵創新和轉軌。財稅收入快速增長時,應當留出一定的空間去支持稅制的改革。
賈康:中央政府并沒有什么對稅收的偏好,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領導都呼吁要實現兩稅并軌,一致支持稅制改革。在財政收入增長比較快的時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進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和增值稅轉型兩個改革,因為這兩個改革都會減少稅收收入。現在的財政收入持續增長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條件,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這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