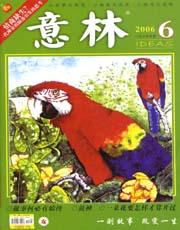我的父親愛迪生
查理斯·愛迪生
在美國新澤西州曼羅園他的實驗室里,我的父親愛迪生踱來踱去,一縷亂發覆蓋著前額,銳利的眼睛,皺了的衣服盡是污痕和被化學品燒破的洞,全不像一位改革家,他也不充什么派頭。有次一位要人來訪,問他是否曾獲得許多獎章獎狀,他答:“唔,有的,家里有兩瓶酒,是媽媽獎賞的。”“媽媽”是指他的太太,我的母親。
父親是個工作狂,他通常每天工作18小時以上。他認為:“睡眠有如藥物,一次服用太多,頭腦就不清醒。你會浪費時間,活力減少,錯過機會。”有些人問:“他從來沒有失敗過嗎?”當然失敗過。他時常碰到失敗。他的第一件專利品是電動投票記錄器,用以對低級鐵礦做磁性的分離。但是后來因為開發了蘊藏量豐富的高級鐵礦,這項設計便完全白費了。
但他從不會因恐懼失敗而趑趄不前。在從事一系列艱苦的實驗期間,他告訴一位氣餒的同事說:“我們并未失敗。我們現在已曉得有一千種方法是行不通的,有了這些經驗,便容易找到行得通的方法。”
他對于金錢得失的態度也是如此。他認為金錢是一種原料,跟金屬一樣,我們應該加以運用,而不要積聚。
有一天,父親在觀察一部礦石壓碎機的效能。他對那部機器的運轉情形很不滿意,吩咐操作工人說:“把速度提高。”“我不敢,”那工人回答:“再提高速度,機器會壞的。”
父親轉過頭去問工頭:“艾德,這部機器要多少錢?”“兩萬五。”“我們銀行存款有沒有這么多?有的吧?那么把速度再加快一級。”
操作工人把動力加大了,然后再度警告說:“機器響聲很大,如果爆炸,我們都會沒命了!”
“那沒關系,”父親大聲喊道:“盡量開動!”
響聲越來越大,大家開始往后退避。突然轟隆一聲,碎片四射。礦石壓碎機垮了。
“怎么樣,”工頭問父親:“從這項經驗又學到什么?”
父親微笑著說:“學到我們可以把制造者所定的動力極限提高40%——只要不超過最大極限就行。現在我可以再造一部機器,增加產量。”
我的父親從小就幾乎是個十足的聾子。他只能聽到最大的響聲和喊聲,但是他對這個缺陷并不在意。他說:“從12歲起,我就沒聽見過鳥叫。但是耳聾對我不但不是障礙,也許反而有益。”他認為耳聾使他提早讀書,還能夠專心,不必和人閑聊,省下許多時間。
有人問父親,為什么他不為自己發明助聽器,他總是回答說:“你在過去24小時聽到的聲音,有多少是非聽不可的?”然后他又補充說:“一個人如果必須大聲喊叫,絕對不會說謊。”
他喜歡音樂。旋律清楚的,他有辦法欣賞,用牙齒叼著鉛筆,把筆的另一端搭在留聲機的匣子上,借以“傾聽”。這樣他可以領略抑揚頓挫和節奏之美。在他所有的發明中,留聲機是他最滿意的。
父親從沒退休,也不怕老。在80高齡,他還開始研究一門以前未曾研究過的學科——植物學,想在當地植物中找出橡膠來源。他和助手們把1.7萬種植物加以試驗和分類之后,終于研究出從紫菀科植物中抽取大量膠汁的方法。
83歲時父親還拉母親去熱鬧的紐華克機場“看一個真正飛機場的實際情形”。他第一次看到直升飛機的時候,笑逐顏開地說:“我一向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于是他又開始設計,對于那架不大為世人所知的直升飛機,提出許多改進的意見。
到了84歲,父親因患尿毒癥危在旦夕。數十位新聞記者前來探訪他的病情,整日守候。醫生每小時向他們宣布一次消息:“燈火仍然在照耀著。”到1931年10月18日上午3點24分,噩耗終于傳來:“燈滅了。”
舉行葬禮之日,美國當局為了向他表示哀悼和敬意,本來預備把全國的電切斷一分鐘,但是考慮到那樣做所付代價太大,而且可能產生危險的后果,所以只把一部分燈光熄掉片刻。
進步之輪是片刻不停的。父親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也同意這樣做。
(王慧媛摘自《海外星云》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