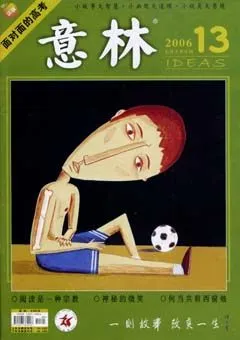樓梯上的扶手
愛德華·齊格勒
譯/任曉林
我的腿跛得厲害起來,上下樓梯拉扶手使的勁越來越大,走樓梯、跨臺階、去溪邊也越來越不利落。從我三歲那年得了病留下后遺癥后,我這兩條病弱的腿就成了我的伙伴。如今我四十五歲了。
我的兒子麥修具備所有我所缺乏的自信。他今年十七歲,有一頭金黃色的頭發,體格健壯。我不在場時他常常口若懸河地顯示他的口才,但我們在一起時,他卻有點像粗獷而口訥的運動員。他是個活躍的曲棍球運動員,還是個抓魚能手。
我們有過幾次不快,但除了火頭上的交鋒,我們之間相處得很好。
他一天天長大,而我卻一天天衰弱。看著晃晃蕩蕩的樓梯扶手,我的擔心與日俱增,修扶手已不能再等了。我去請過幾個木工,可誰也不想來干這點活。我走樓梯更小心謹慎了。
我雖然跛,不過在晴朗的夜晚我還能搬著我那老式的望遠鏡爬上松林邊的小山,把望遠鏡放在三角架上,尋找新的球狀星云和雙星。
麥特(麥修的愛稱)常來幫我架望遠鏡,有時他會留下來。也是在這樣一個夜晚,他又要我講他和天狼星——那顆天空中最亮的星之間的故事。
西瑞依斯(天狼星)是麥特的中間名字,是為紀念他出生在藍白的天狼星和壯觀的獵戶座星光下而起的。麥特就是在這座小山下面的小松林里出生的。
那天他母親沙莉是半夜以后醒過來的。因為是第二胎(當時兩歲的安德魯正睡在他的童床上),她很冷靜地按經驗估計新生命大約還得過幾個小時才會降生。
那時我還沒醒,對于將要在我身邊發生的戲劇性事件毫不知曉,是她用變了調的尖聲叫醒了我:“快起來,孩子就要降生了!”
那時我的腿比現在靈便,我跳起來穿上衣服,抓了車鑰匙就沖下樓去。沙莉已經給醫生打了電話,又叫了一個鄰居來照看安德魯。
等那鄰居來了以后,沙莉和我就去開車。我們那輛月白色的老福特停在50英尺外的松林旁邊。我坐在方向盤后面,“上車吧,沙莉,我們走。”我說。她還在猶豫。
“我……我不能坐了。”
“你怎么了?”
“嬰兒的頭就要生出來了……你最好還是過來接著吧!”
這時沙莉已經爬上了前座。
“你快過來呀!”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充滿了驚恐和緊張的聲音。
在這秋夜的星光下,我過去接住了嬰兒。這個小小的且有著體溫的小東西還沒有完全生出來,就發出響亮的哭聲。我右手托著他的腦袋,左手托著后背,驚奇地看著那個圓潤光滑的肚子一會兒就變成了一個能哭會喊的嬰兒。
我小心翼翼地提著嬰兒的腳后跟,托著嬰兒的頭,借著星光我看到小身體上那個小雀雀正對著我。“是個男孩!”我喊了起來,熱血涌遍了全身。
接著我把他遞給了他母親,給他們披上了大衣。一會兒救護車到了,醫護人員接替了我。忙亂之中我的汽車鑰匙丟了——失落在這個夜晚,這片松林,這腔興奮之中。
這就是嬰兒在洗禮時被命名為麥修·西瑞依斯的緣由——因為他降生到我的雙手中時,天狼星正在我的頭頂上照耀著。
麥特為他的中間名苦惱了好多年。當他長到能忍受別人的取笑時,他已經為他取了天上最亮的星星的名字而高興了。
有天晚上,我工作完后正準備攀扶著樓梯上樓去休息時,發現扶手不晃了。“沙莉,”我喊道,“你知道這扶手修好了嗎?”
“對,你去問問麥特。”
麥特回來后,說扶手是他修的。
“那我該為你做什么呢?”
“不用,你已經為我做過了。” “做過了,怎么會呢?”
“你知道,我降生在你的雙手里,使我沒落在地上。所以我想我該報答你。”
接著是一陣沉默。在沉默中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在我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雖然看不見又聽不見,但卻能被我的心,我的骨髓所知覺,所感動。
今天離這故事發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年。樓梯扶手依然牢固。天狼星也仍然在松林上升起——秋天里晚些,冬天里早些,春天里更早。而我每次看到它,心里就充滿謝意。
(野風摘自《黎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