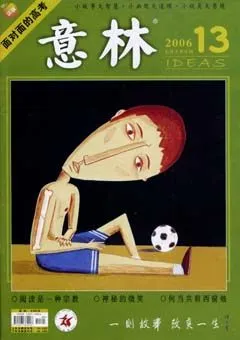佳作
J·A·湯姆
譯/鄒小良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個(gè)早春的上午——這天,慘白的陽(yáng)光照著剛吐綠芽的樹(shù)枝。年輕的我作為一名專(zhuān)門(mén)采訪治安消息的記者,正驅(qū)車(chē)駛向一處我不愿看見(jiàn)的地方去。警方廣播報(bào)告說(shuō):一名男子在家中的車(chē)道上倒車(chē)時(shí)意外地撞倒了小孫女,導(dǎo)致了一樁死亡事故。
我把車(chē)停在警車(chē)和電視采訪車(chē)之間,立刻看見(jiàn)一個(gè)身穿棉工作服的壯實(shí)的白發(fā)男子正站在一輛小型運(yùn)貨車(chē)旁。幾只照相機(jī)對(duì)準(zhǔn)著他,記者們把話筒伸到了他的面前。這位老人看來(lái)完全處于迷惑之中,正竭力回答記者的提問(wèn)。他幾乎只是在抖動(dòng)嘴唇、眨著眼睛,一句話也說(shuō)不出來(lái)。
不一會(huì),記者們放過(guò)了那位老人,跟隨警察擁進(jìn)了一間小白屋。在我想像中仍能見(jiàn)到那位備受精神折磨的老人正俯首注視著車(chē)道上曾站著孩子的那塊地方。屋旁是一個(gè)剛培土的花臺(tái),不遠(yuǎn)處有一堆黑油油的沃土。
“我當(dāng)時(shí)只想到那兒去撒那些肥土,”老人對(duì)我說(shuō)著,盡管我并沒(méi)有向他提問(wèn)什么,“我甚至不曉得她在門(mén)外。”他伸手指著花臺(tái),然后又讓手垂回腰際,重又陷入了思慮之中。而我正如一個(gè)合格的記者那樣踱進(jìn)屋去看有誰(shuí)能夠提供那蹣跚學(xué)步的孩子的近照。
幾分鐘后,我速寫(xiě)本上記滿了全部細(xì)節(jié),口袋中插著一張那天真無(wú)邪的女孩在照相館拍的3×5寸的照片,又朝警察說(shuō)的放尸體的廚房走去。
我隨身背著照相機(jī),是那種又大又笨的“斯比·古勞”牌的,這當(dāng)時(shí)就象征著新聞?dòng)浾叩纳矸荨V魅藗儭⒕臁⒂浾吆蛿z影師——所有人都已退回屋外去了。我跨進(jìn)廚房來(lái)到現(xiàn)場(chǎng)。
從拉著帶縐紗窗簾的窗口透出的陽(yáng)光照出,在一張塑面桌上躺著一個(gè)包在潔白被單中的纖小的身軀。那位祖父不知怎的總想避開(kāi)眾人,他正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側(cè)對(duì)著我,絲毫沒(méi)有意識(shí)到我的出現(xiàn),只是難以名狀地死死盯著裹住的尸體看。
屋里非常寧?kù)o,時(shí)鐘在“嗒嗒”地走動(dòng)。我看到,那老祖父慢慢向前傾下身軀,曲起雙臂猶如括號(hào)一般圍住了小身形的頭與足。然后他把頭抵在裹尸單上,久久地動(dòng)也不動(dòng)。
在這寂然無(wú)聲的時(shí)刻,我預(yù)感到將會(huì)產(chǎn)生一張有獲獎(jiǎng)希望的新聞?wù)掌N覝y(cè)定著光線,調(diào)好光圈和距離。在閃光燈上安好燈泡,舉起照相機(jī),從取景框中構(gòu)成畫(huà)面。
畫(huà)面中的每一組成部分都堪稱(chēng)完美無(wú)缺:身著樸素工作服的祖父;背襯著陽(yáng)光的白發(fā);包在被單中那孩子的小身形;窗邊墻頭上黑色鐵支架和“世界博覽會(huì)紀(jì)念盤(pán)”所烘托出的這間陋屋中的氣氛。外面,可以看見(jiàn)警察正在檢查運(yùn)貨車(chē)那致命的后輪,而孩子的父母親則依在相互的臂膀上。
我不知道在那兒站了多久,仍不能按下快門(mén)。我強(qiáng)烈地意識(shí)到即將攝成的照片必定具有驚人的新聞效果和價(jià)值。我那職業(yè)責(zé)任感催促我將它攝下來(lái),但我無(wú)法讓手點(diǎn)燃閃光燈,那無(wú)疑會(huì)打擾可憐老人那痛苦的內(nèi)心世界。
我最后放下了照相機(jī),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我萬(wàn)分震驚地對(duì)自己是否適應(yīng)新聞職業(yè)產(chǎn)生了懷疑。當(dāng)然,對(duì)于這次失去獲得新聞?wù)掌炎鳈C(jī)會(huì)之事,我沒(méi)有告訴城里的編輯和同行們。
每天在新聞廣播或報(bào)紙上我都能看到處于極度痛苦和失望中的人們。人類(lèi)的苦難已經(jīng)成為一項(xiàng)可供觀賞的運(yùn)動(dòng)了。當(dāng)我有時(shí)在看新聞電影時(shí),就不免想起那么一天。
對(duì)我當(dāng)時(shí)的所作所為,我至今不悔。
(尹手摘自《小小說(shu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