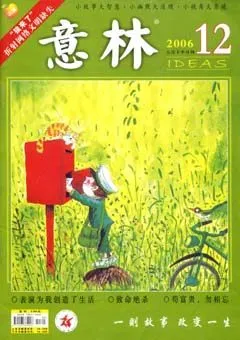人生中的“借貸平衡”
平鑫濤
遠去的初戀
大學(xué)時同班的女同學(xué)們,大都是富家千金,正值青春年華,個個爭奇斗艷,但也有一小群大概三五位,服裝比較樸實,也不濃妝艷抹。對我而言,很有親和力。當(dāng)她們要求我為她們溫習(xí)課業(yè)時,我自然欣然應(yīng)命。其中有一位文靜寡言、面目姣好,年輕的我,難免心動。似乎她也對我印象不惡,兩人漸漸由集體溫課,發(fā)展為個別研討。她家正好在我回家的中途,每天放學(xué)后她主動陪我步行回家。經(jīng)過黃昏時的公園,常會留連忘返。我們很少約會,不論喝杯咖啡,看場電影,對我而言都是囊中羞澀。我也不愿意由她請客,雖然我們每天幾乎都有一二小時獨處,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
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溫課,發(fā)現(xiàn)她家竟然十分豪華。白色的精致洋房,庭園深深,穿著制服的仆傭,送茶、送點心。沒想到她外表樸素平實,卻生長在這樣一個豪富之家。自卑與自尊的交織,使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們的感情不可能有美好的發(fā)展,于是心底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墻,從來不讓一絲一毫情意溢出墻外。我想她當(dāng)然知道我的家境清寒,所以從不要求到我家以免讓我感到尷尬,只是默默地接受我們這種純純的交往。
畢業(yè)聚餐那天,同學(xué)們嬉笑著向我們祝福:“向新郎新娘舉杯。”她都大方地接納,似乎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卻有些不知所措,內(nèi)心百味雜陳。畢業(yè)以后,前途茫茫,尤其在這樣戰(zhàn)亂的時候,我能給她什么愿景?更何況我們的生長環(huán)境,如此懸殊,我不以為有“終成眷屬”的可能。
聚餐后的第三天,突來的機緣,決定去臺灣。我滿懷離愁地去她家話別。聽完了我結(jié)結(jié)巴巴的述說,她卻出奇地平靜,不像小說或電影里的男女主角那樣愁腸寸斷,難舍難分。她臉上沒有笑容,只是冷冷問我:去臺灣有必要嗎?留在上海一定不好嗎?去臺灣一定更好嗎?
我無言以對,最后,我拙拙地說真希望有她同行。她還是那么平靜。說:“你只有一個艙位,我哪能去?再說我憑什么身份跟你去呢?”是啊,我從未給她任何信諾,何況,即使再有辦法的人,都不可能再弄到任何艙位,即使她真的可以到臺灣,我又能給她什么?我自己什么也沒有。
就這樣,我“失去”了——或者應(yīng)該說結(jié)束了這一段淡淡的、純純的,甚至不算初戀的“初戀”。
一年后,我收到她的來信,從香港轉(zhuǎn)來。信上說:“……現(xiàn)在,即使我有此心愿,也似乎更不可能了。”從此,我再也沒有接到她任何訊息。
離開上海四十年后,我和瓊瑤回到上海,在我下榻的飯店歡迎我的老同學(xué)們,居然來了二十多位,彼此相見,恍如隔世。瓊瑤表示她很希望見到我的“初戀情人”,但她,沒有來!并且沒有一位同學(xué)知道她的下落。
我想,如果不是貧富懸殊,我又不那么自卑(或說是自尊),也許我們之間的感情會有較正常的發(fā)展,那么,我也許會舍不得離開上海,或者她會強烈地不讓我離開上海……
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失去”!
永別了母親
離開上海,當(dāng)然最使我舍不得的,是這個家,雖然這個家又小又破,但這個家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每一件破舊家具,每一道斑駁的油漆,都記錄了歲月的痕跡,那么熟悉,那么親切。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尤其掛心的是體弱多病,對我呵護備至的母親。
當(dāng)我們討論要不要搭船到臺灣時,母親蒼白干枯的臉上,卻是毫不猶豫地堅定。她把二兩黃金,密密地縫在我一件外衣的墊肩里,又細心地為我整理行裝,她說:“真可惜你不能把收音機帶去!”父親則把他用了一輩子的手表和鋼筆給了我。
臨別時,我熱淚盈眶,不能自已,希望母親改變初衷要我留下。真的,我一直在想,我有必要非去臺灣不可嗎?
母親非但沒有流淚,反而容光煥發(fā)地、含笑地說:“等日子平靜了,就可以回來啊。等事業(yè)有成了,可以接我們過去啊。”好像我只是去郊游,她很高興地祝我玩得盡興。
當(dāng)時,我也覺得也許二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去。但沒有想到這是永別。
如果當(dāng)年我沒有離開上海,不知道會有怎樣的人生?總之我的命運會改變,我周圍的人也會因我而改變命運。
如果當(dāng)年我沒有來到臺灣,絕不可能有《皇冠》這本雜志,也絕不可能因《皇冠》的存在而影響一些人與事。當(dāng)然,也不可能與瓊瑤有這份相知相惜、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情緣。
不管你喜不喜歡,愿不愿意,人生有數(shù)不清的“得”和“失”,你也可能必須一次次地面對這些“得失”,作一抉擇。不同的選擇,就會有不同的后果。可能影響你的一生,也可能影響你周遭的一切。會計學(xué)上有個最最基本的定律:“有借必有貸,有貸必有借,借貸平衡。”如果用淺顯一點的說法,所謂“借”,是收入,是得到,是正面,是資產(chǎn);所謂“貸”,是失去,是付出,是負面,是負債。把這定律應(yīng)用到人生上:你失去了一個機緣,因此而得到另一個機緣。你得到了一筆財富,可能換來了享樂,也可能帶來災(zāi)難;你結(jié)束了一個不順的婚姻,可能換來另一個美滿的婚姻;你做了一件義行,可能得到了一份福報……
所以——因為“失去”,所以“得到”。也可以說沒有“失去”,哪能“得到”?
(任長秀摘自《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