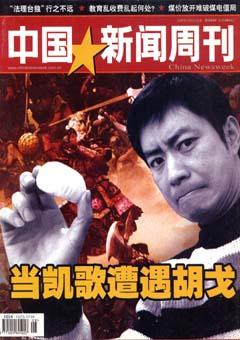煤電角力 積年沉疴
于 石
據資料顯示,煤炭訂貨會從1965年就開始了,這在當時也是全國最大的物資分配訂貨會議之一。
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計劃經濟下的訂貨狀況一直持續到2005年秦皇島“訂貨會”。當時國家發改委為了擺脫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將“煤炭訂貨會更名為“煤炭產運需銜接會”。但是,即使如此,人們依然將2006年的“煤炭產運需銜接會”稱為“煤炭訂貨會”。在煤電雙方看來,這種更名只是用簡單的方法來化解煤電矛盾。
多年的煤炭訂貨會就是多年的煤電角力。
1990年代的矛盾
從歷史上來看,煤電利益矛盾真正開始在現實中顯現始自1992年,而其中“計劃煤”與“市場煤”的雙重價格則是核心。
1992年以前,尤其是計劃經濟年代,煤炭與糧食、棉花始終被視作戰略物資。當時的煤炭企業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生產單位”,并不參與到銷售等環節。“低價格”的煤炭很容易形成煤炭企業虧損的狀況。
1992年煤炭方面匯報的需要補貼數額是60億元,1993年這個數額達到80億元,“這也就是說國家要對絕大部分的煤炭企業進行補貼。”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濮洪九說。
因此,放開煤價,用漲價來彌補煤炭企業的虧損便成為了一個選擇。
在放開大部分煤價的同時,政府還留存了2億8000萬噸電煤,在價格上施行“政府指導價”。就此也形成了“政府指導價”(即計劃價)和“市場價”。隨后電煤略有上漲,電力部門也力求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1993年后,國家采取了“順價”政策,即根據煤炭的漲價,電價也可以漲一定幅度。其實,這和目前提及的“煤電聯動”并無實質性差異。但是到了1994年,農村電價瘋漲,考慮到農電涉及到更大范圍的影響,“順價”最終被當時的國家計委“勒緊”。
此后,電煤價格和供應依然是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但是,在煤炭企業不景氣的90年代,電力企業往往是不會將計劃合同煤的數量訂滿,而更愿意從市場上采購煤炭。在煤炭企業來看,“這是不扶煤炭兄弟一把!”
于是,這種無法理順的半市場、半計劃的煤電之間的關系,變成一種“煤電矛盾”開始延續。而每年的煤炭訂貨會一度被政府認為是解決矛盾的一種不二法門。
2000年后加劇的角逐
2003年以后,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運轉,煤炭市場開始回暖,煤炭等資源性價格的漲價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選擇。2004年10月底,記者在美國太平洋頂峰經營的誠峰熱電廠采訪,其管理者一直在抱怨著煤價的上漲——2003年煤價100多元,2004年已經達到300元。太平洋頂峰(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安德森則向記者抱怨,大的發電廠依舊有拿到統配煤的特權,而且在運力方面可以得到保證。
而反映在煤炭訂貨會上,煤電雙方進入一種白熱化的角力。
2003年長沙煤炭訂貨會上,在煤炭價格普遍上漲的局面下,電力企業始終堅持電煤價格不能改變、合同條款不能改變、訂貨基數不能改變。2004年年底,國家發改委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試圖解決“煤電頂牛”的局面。內容規定,“原則上以不少于6個月為一個煤電價格聯動周期。若周期內平均煤價比前一周期變化幅度達到或超過5%,相應調整電價;如變化幅度不到5%,則下一周期累計計算,直到累計變化幅度達到或超過5%,進行電價調整。”2004年福州煤炭訂貨會上,國家發改委推出了首次煤電價格聯動——允許發電用煤價格每噸上漲不超過12元,同時允許發電廠上網電價每千瓦時上漲7厘。也正是這種政策,促使煤電雙方簽下90%的合同。
但是,即使如此,最終合同的履約率卻相當低。“很多電力企業的老總都在招待煤炭企業的酒席上給抬下來,就是為了能夠簽下一些價格不錯的煤炭!當時我看了很傷心。”中國電力報的一位記者說。
考慮到電價上漲的滯后性,電力企業的虧損在預料之中。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1140家火電企業中有440家虧損,總虧損額78億元。
到了2005年,國家發改委將“煤炭訂貨會”更名為“煤炭產運需銜接會”。當然,為了避免市場大幅波動,發改委最終還是定出了8%的煤炭價格上漲幅度,但是結果卻大出政府的預測——土漲幅度甚至超過15%以上。2005年春節后,華能、大唐、華電、國電和中電投五大電力集團聯合向國家發改委上交報告,認為發改委在訂貨會上的確定的煤炭漲幅受到了煤炭企業的一致干預。
2005年年5月,全國平均電價每千瓦時上漲0.02元,約消化掉7%至8%的電煤價格上漲因素。但是,截至2005年11月,發電企業仍有噸煤13元的價格漲幅沒有被消化。
而煤炭企業也在叫屈,華東煤炭銷售聯合體秘書長鄭勇曾向記者分析,2005年,安徽省內重點電煤和市場電煤之間的價格差超過100元/噸,比真正的市場煤炭價格則低200元/噸。僅此一項,該省四大煤炭企業即減少銷售收入26.8億元。
2006年,發改委表示,以后將不存在重點合同電煤的說法。隨后引來的重點合同電煤漲價雖然在各方的預料之中,但是發改委決沒有預料到,2006年的合同簽署會如此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