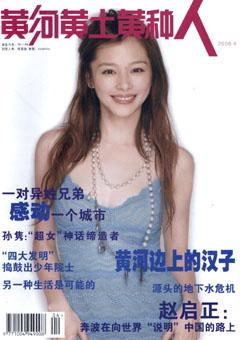源頭的地下水危機
王銀剛
今年的世界水日前夕,我與內蒙古烏梁蘇汰河西營子的劉福存通了個電話,知道村里那幾天正忙著抽水澆地。剛抽了兩天,住在村中間的小學校長陳益民家那口壓水井又斷水了。交談中了解到,今年澆了半個月地,村里的壓水井只干了百分之七八十,說是全仗著去年秋天的雨水好。而去年春天澆地時,全村沒水的井占了九成以上,并且過了很久才恢復。我知道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了好幾年,自從使用了那兩眼機井,情況越來越嚴重。雨水多寡,井中立顯,說明地下系統已經十分敏感,也十分脆弱了。
河西營子是一個有近60戶人家的小村莊,位于克什克騰旗境內嘎拉德斯汰山的烏梁蘇汰溝中下段。原先溝里山高林密,云過雨過,小氣候十分宜人。那時幾乎溝溝汊汊都淌水,進山不用背壺帶水,到處都有甘洌的“撅茶”解渴。每年春暖,淹冰融化滋潤了溝膛,泉眼一開,流水蜿蜒曲折匯成小溪,嘩嘩地繞過村莊,奔向嘎拉德斯汰河。這時,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婦便會來到溪邊拆洗蓋了一冬的被褥。他們將洗凈的被單展覆在河邊的草灘上晾曬,猶如一畦畦開滿鮮花的美麗花圃,迷惑了飛過的小鳥,成了初夏的一道風景。即便暴雨過后洪水下來,第二天溪水便又清澈,偶爾仍能看到水中石塊間游動的泥鰍。
當年我下鄉在此時,溝膛的地下水十分充沛,也很穩定。我曾參與策劃和組織過挖井、截潛工程,對地下水的情形有過直觀的了解。尤其是那個截潛工程,在河西營子下幾十米的地方,橫向剖開了大半個溝膛,地質構造一目了然。
截潛工程,就是利用落差將潛在地下的流水截引上地面,用以澆灌和飲畜。老百姓戲稱是“扳倒井”、“自流井”。為了出水口靠近地頭,也為了不影響村頭的水井,河西截潛的開挖深度只達七八米,沒有接觸到基巖,挖出的都是大大小小的礫石、砂石和少量黏土。在30多米寬的立面,不計滲滴,明顯流淌的泉眼就有20多個。從此,牲畜飲水無論冬夏全年靠這股長流水解決,冬天滿溝膛的淹冰成了下游春匯地的水源。直到后來在它的上游打了兩眼機井,開機抽水時才發生斷流,并因此流量逐年減小。
和潛流同時發生斷水的還有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壓水井。真是越忙時節越添亂,原先的水井因為水位下降無人使用,更為安全考慮已被封閉,大伙只得東鄰西舍找水喝。幾年來村民們已經習以為常,怨只怨自己的壓水井打得太淺,總相信只要機井不抽便會來水。
人們還沒意識到這是地下水危機發出的預警信號。
與烏梁蘇汰一山之隔的克侖沐汰,溝里的溪水也已經斷流。1977年,我曾經在這道溝的二地營子上面完成了截潛工程。為了這個工程,犧牲了一個隊長,還有一個大連知青九死一生。可自從近幾年在工程的上方打了一口深井,潛流水便全年干涸,廢了。為機井配套修了梯田,筑了防滲灌渠,卻因為受地形位置和農時限制,澆地也只能在百十畝左右。既耗能源,還需維護。每當開機澆地,營子里不少水井便壓不出水,牛羊飲水又成了費勁事。老百姓都說得不償失,倘若水井因此也廢了,人畜用水都靠深井將會極不經濟,還難料水質如何。
為了利用地面上的一點水,人們忙于疏堵;地下水看不見摸不著,卻似有恃無恐。機井打出水來,便歡呼勝利,慶賀成功。打得越深、越多,便能耐越大,政績越高。機井一開,高強度地索取,打破了源頭水循環這個極重要的生態支撐條件與環境要素的平衡。危機也許就是這樣由人促成的,大自然不追究責任,卻不會放棄報復。
河西營子歲數大一點的人都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一場連陰雨,下了足足一個半月,山坡到處見涌泉,有的人家連灶坑都淌水。但是這里既沒發生山體滑坡,也沒有出現泥石流,洪水過后溝里也看不到因此倒伏的樹木。
保持林相原始面貌的森林是一座隨山起伏的水庫,動植物資源的欣欣向榮與雨水頻頻互為因果,呈現一種良性循環。無需引證專家們的實驗結果:一株大樹每天從地下吸收25~70升水,一畝闊葉林一個夏天能蒸騰160噸水,能使空氣濕度大增,從而增加大氣降水的機會。
這里的人們絕對相信老祖宗認定的真理:山多高,水多高。確實,我們在很多風景區的山頂寺廟旁見過水井,轆轤上的井繩并不長。至于為什么與“水往低處流”相矛盾,人們常用雨水多、石頭底不透水等等來想當然,其實稍作調查便不難發現,除了地質構造的因素,主要還在于地表植被的水土保持起了決定性作用。活的大山猶如一棵健康的大樹,樹多高,地下的根就會把水輸送到多高。
因為人口的增長,砍柴的車已經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往溝里推進;打回的棒柴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短了,直到無柴可砍。人們開始褪樹杈,于是一年比一年褪得高,褪回的樹杈一天比一天細……當我還在夢中津津樂道嘎拉德斯汰是個生命樂園的時候,這里已經悄悄地不知不覺改變了。
我們這代人親眼目睹了嘎拉德斯汰山上的清泉逐漸干涸,山楊、白樺正在逐漸甚至成片枯死,動植物物種正急劇減少,生態條件退化使環境狀況進入惡性循環。在這里高強度開采地下水,無疑是雪上加霜。
大自然的回應絕不是今天上山砍了樹,明天就山洪暴發,后天便泥石流吞沒村莊。嚴重的問題是人們往往對潛移默化熟視無睹。有些變化是不可逆轉的,即便有一線可能,也將是十分困難、漫長的。只要想想我們喊了這么多年的植樹造林,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綠化荒山至今收效不大,步履依舊艱難,那么已經進入惡性循環的生態的修復會是一個怎樣的過程,該是不言而喻的了。
為了抗御干旱,近年來,這里也廣泛使用了塑料地膜,使節水保墑促全苗成為可能,并且減小了除草松土的勞動強度,不失為增加作物收成、提高農民收入的好辦法。可隨之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已經成為這里的環保難題。
當我們砍樹毀林,當機井反復、強烈地干擾地下水文環境,就有可能陷入無水窘境,人們不得不重覓家園,那時便無以面對擇水而居創立家業祈求子孫興旺的先祖,枉費自己一世辛勞,愧對兒孫后輩。聯合國環境計劃署、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合會制定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用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話:“我們并沒有從父輩那里繼承地球,只是從后輩那里借用了它。”
今年的春節我曾在烏梁蘇汰度過,用一個多月時間結束了初步調查。喝完了河西營子孫隊長端給我的奶茶,三步一回頭地告別鄉親們,心情是沉重的。這里的山水曾經養育過我,中國人的報恩美德促使我志愿為她的繁榮出力。
回程一路走來,過熱水到經棚,經赤峰到大連,在酒店盥洗間我看到了“節約用水”的標貼,此刻更因其精美而讓人動容。我用相機做了記錄,準備寄給烏梁已當了父母官的老朋友。
昨天接到老朋友的電話,告訴我森警大隊正在大規模擴編招員,這道溝又增加了4個護林員,嚴格禁止牲畜上山進溝。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好消息!
為解決溫飽,我們曾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奔小康,我們會將目光放得更遠,有能力有膽魄做出抉擇、學會節制,學會放棄。一種設施、一種方法,當人們嘗到了甜頭,自然不會輕易舍棄。告別輕車熟路,需要一種犧牲精神,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
為了讓孩子們在共和國的地圖上依然看到我們腳下的那條藍色曲線延綿不絕,看到母親河恢復水流潺潺的昔日容貌,我們還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但“亡羊補牢,未為遲也”。致力環保,持之以恒,一定會實現青山永駐、綠水長流、造福子孫。
作為生活在生命之源,生活在淡水源頭的人,應該以生命的名義,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滴水。保護山上的一草一木,爭取在現有大樹壽終正寢之前,恢復起接續的幼樹和灌木,恢復郁閉的植被。
愛惜水資源,保護水源地,化解水危機,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