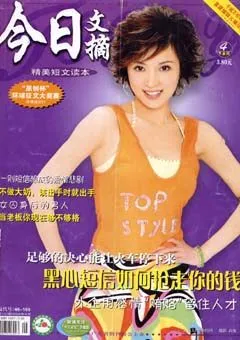八月,我淚流滿面
今年的八月,少有鳥的煽情、蟬的聒噪,多是風的嗚咽、雨的悲鳴。八月,我沉默不語;八月,我淚流滿面。
爺爺從發病到死亡前后不到3個小時,可我卻像是在地獄的隧道里艱難地穿行了無數個世紀。
當患有半身不遂的奶奶顫顫巍巍的拄著拐杖用她那吐字不清的舌頭向我說明爺爺摔倒在地上的時候,我渾身有一種雷擊般的驚悸。硬漢子爺爺摔倒在地上自己卻起不來了,我知道爺爺這一跤摔得肯定不輕。
連忙跑過去的我,看見爺爺頭朝南摔倒在廚房門前,手里拿著什么我已無從記得;我一邊費力地摟住爺爺癱軟無力的身體把他緊緊地抱住,一邊大聲喊著三弟趕快打電話找醫生。爺爺看出我的驚慌,說,“不要緊張,緊張個啥?”不曾想這竟成了爺爺生前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我不知道爺爺是否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知道,爺爺為何對自己的生死看得如此淡然;如果不知道,突然襲來的巨大痛苦為何沒有改變爺爺慣有的沉著?
所有的這些我都無從知道了。八月的電閃雷鳴讓淮河兩岸人們的臉色在水澇里漂得蒼白。爺爺離去那天惡毒的陽光則幾乎照得我毛發倒豎,七竅生煙。
八月,我沉默不語;八月,我淚流滿面。
在那間溽暑蒸騰的病房里,當我閉上眼睛把因過分緊張而攥得汗涔涔的手試探著放在爺爺的胸口時,我感到徹骨的冰涼——陰冷的涼氣剎那間傳遍全身,如酷暑之際墜入冰窖。
爺爺死了。抬手時我淚如雨下。看不見匆匆趕來的醫生那判官似的表情,聽不到周圍撕心裂肺的哭喊。我只是絕望到近乎麻木地意識到爺爺死了,在來不及思考,毫無預感的時候。
人都說生者死前會有回光返照和臨終遺言,可是爺爺什么也沒有留下就那么匆匆地走了,甚至沒睜開眼看一看自己的兒孫,沒有對這個他生活了七十余年的世界留一聲深情的眷戀。爺爺就這樣走了,一言不發,睡態安詳。
我沒有失聲痛哭,只是淚流滿面。世間許多事情人們都去尋求一個完美的結局,甚至死亡也不例外。似乎死者只有在回光返照中對病床前的滿堂子孫千叮嚀萬囑咐然后撒手人寰,駕鶴西去才算壽終正寢,活得風光,死得體面。
可是爺爺走得匆忙,來不及等他兩個遠在山東為養家糊口做小本生意的兒子,來不及等他那個在縣城為考大學而發奮苦讀的孫子,來不及聽一聲他已經上了大學的長孫喚一聲爺爺。
爺爺生前是村子里的忙人,風風雨雨中當了40余年的大隊書記,芝麻大的村官管著芝麻多的瑣事,直叫貧窮落后的村莊發生著芝麻開花般的變化。爺爺一生都在奔忙,生前不曾像別人家的爺爺那樣在有陽光的白天背著孫子四處串門,或是在有星星的夜晚摟著孫子講一些老掉牙卻又生趣盎然的故事。我沒有獲得這種別人幾乎都有的童年幸福,可爺爺不也失去了平凡歲月里的逗孫之樂嗎?
八月,我沉默不語;八月,我淚流滿面。
女友說,聽說爺爺生前根本不疼愛你,為何你想到他時總是淚流滿面。
我沒有作答。我只是想:爺爺有村子里百家的憂樂,也會有個人的一己悲歡。作為他的孫子,我不應該苛求什么。況且,即使他真的不疼愛我(事實上決不可能),爺爺也是我卑微生命的偉大根系里供我營養的粗壯一支,我明亮的臍帶連著母體,可我冰藍的血脈和爺爺永在一起。
其實,我寧愿相信爺爺是不辭而別的一次出游,獨自一人去消解一身的勞頓。如果爺爺是去了某個地方,那么他一定會在那兒耐心地等著我,我們祖孫之間還有一場遲到的重逢,可是理智告訴我,他不是去了某個地方,而是根本不存在了。
昨夜的夢里,潸然淚下中我又回到了八月,見到了爺爺——八月驕陽似火,爺爺睡態安詳。
八月,我沉默不語;八月,我淚流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