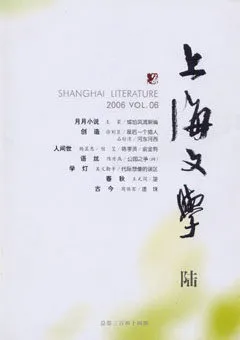滑稽戲·性別研究及其他
上海:羅婷婷來信
陳主編:
錢乃榮教授在《上海文學》上每發一篇文章都開辟了一個海派文化的研究領地,從方言到滬劇,這回又討論了滑稽戲。上海是移民城市,居民來自五湖四海,現在又有了大批的新上海人,語言是南腔北調,所以,沒有純粹的上海方言,也沒有純粹的上海風俗,而是由全國各地融匯在一起的生活風俗,才是真正的上海風俗。在這個意義上,讓人快樂的滑稽戲很有上海的地方性(大概沒有一個地方劇種可以做到那樣的包容性),就如過去傳統的《十三人打麻將》,典型地表現出上海的雜交文化特點。可惜現在電視里的滑稽情景劇只注意各地方言,不注意各地的風俗特點,文化的意義就縮小了。
希望錢教授能夠繼續關注上海文化的邊邊角角,與社會現象進行動態對話,為海派文化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有一點遺憾是,錢教授的這些宏論似乎沒有引起滬劇和滑稽戲的編劇和有關專家的關注,如果能引起更多的討論就好了。比如現在很流行蔡嘎亮的現象,好像只有傳媒的操作,卻沒有海派專家出來分析這些現象……
羅女士:
你的問題提得很好。《上海文學》是一家由上海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雜志,理當關注上海的文化現象。也希望能夠針對上海的文化建設進行比較學理化的討論。這方面我們應該主動去組織稿件。我也會把你的意見轉給錢教授,希望他能夠繼續為本刊撰寫海派文化的研究文章。關于蔡嘎亮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現象。如果我們考察地方戲曲的發展過程,大約現在人們所推崇的老一輩藝術表演家們,都有過類似蔡嘎亮的草根演出的經歷,記得王安憶在長篇小說《富萍》里描寫過一個地方戲的草臺班與上海群眾娛樂的場景,寫得非常精彩。地方戲曲本來就屬于群眾的娛樂,就是應該在社會的底層里掙扎,與貧窮而快樂的普通民眾在一起,在他們的笑聲、哭聲、哄聲里慢慢壯大起來。如果是敬業的民間藝術家就可能為群眾所歡迎,藝術的流派,唱腔的變革,也是在群眾的選擇中慢慢形成。但是后來,群眾的娛樂被抬入了高貴的意識形態的殿堂,被國家供養著,結果連流派也慢慢枯萎,喪失了生氣勃勃的民間活力。所以我覺得蔡嘎亮的現象,最好的態度是不要去驚動他們,讓這種草根文化在民眾的歡樂和選擇中自生自滅,漸漸會形成當代民間藝術的風氣。格調庸俗一點怕什么?環境骯臟一點怕什么?素質差一點也沒有關系。如果我們一定要像某些媒體那樣去大肆吹捧哄抬,或者給以過多的規范和批評,企圖去引導它,反而是人為地把草根與土壤割裂開來,結果也喪失了民間的包容性和自在性。不過我這樣說不是拒絕討論蔡嘎亮的意思,如果有從文化角度來分析的好文章,我還是需要的。
謝謝你的來信。
陳思和敬上
2月5日
上海:陳惠芬來信
陳思和:
《上海文學》現在越辦越好了,像第三期劉慧英這樣的文章,一般綜合性的文學刊物不會考慮,現在出現在貴刊上,體現了刊物的包容度,很有“五四”時代男性辦刊人的氣度——回望起來,那時的男性精英與女性刊物、女性問題都有千絲成萬縷的密切聯系,而劉慧英的研究文章本身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中肯而有見地,與時下一些似激烈而浮泛的女性主義大不同。
祝《上海文學》越辦越好!
陳惠芬
陳惠芬:你好。
《上海文學》剛發了一點與婦女問題有關的文章就獲得你的鼓勵,真讓我高興,當然剩下的意思是,希望上海研究女性文學的專家也出場可以呼應。《上海文學》目前正在討論關于60年代作家的長篇小說的問題,好像不同意見非常多,眾說紛紜,連續兩期都有一些評論家在發言,連大隱隱于市的程德培也按捺不住,拍馬舞刀了,我突然想,他們討論的和關注的幾乎都是男性作家的作品,6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呢?有沒有值得一說的空間?本期特發表金理對遲子建最近的長篇小說的評論,我期待女性批評家的你也來發表看法。
并祝
身體健康
陳思和敬拜
4月20日
上海:羅錚來信
陳老師:
繼續讀《上海文學》,每一期都有吸引我的小說,讓我產生有話要說的感覺。這回我想對白樺的“邊地傳奇系列”發表一些讀后感想。
在城市生活高速運轉的當下,人們都希冀借假期逃離工作,在回歸大自然中尋找著那一份本真,而不少人的首選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部落。但這些地方是否真的純潔無瑕?讀過白樺的《一朵潔白的罌粟花》后,答案似乎有點痛心疾首。
《一朵潔白的罌粟花》里,一個美麗的邊地姑娘出現了,她的名字叫依嬌。開頭依然是一段美妙的描寫,依然有一個與“我”感情交流的角色,這個已經進入“現代神話”的緝毒大隊長是眾人仰目的英雄,怎么會突然間被抓進了自己一方的看守所?
緝毒英雄夏曉明憑借豐富的經驗逮住了毒販子班丁,本是大功一件,但就是出于對純潔美女依嬌的好奇心,讓他丟失了大好的機會。如果說,這年頭,像依嬌那樣,連見了槍都笑得異常自如,那么只有兩種可能,也正是作者給出的兩種畫面:潔白如玉與陰險狡詐。夏曉明相信了前一種,而且一直都堅信著,這是不是太笨拙?不是,他曾抓住過班丁。是太貪婪?也不是,他拒絕了班丁巨額資產的誘惑。作家的理由是:依嬌太美了,夏曉明無法抗拒的是對美的依戀,明知觸犯法律,也豁出去。“這是命!”
我驚詫于聾子大爹的“復聰”,驚詫于依嬌高超的演技,更驚詫于作者的用詞。后文對前文敘述的顛覆使我有些迷惑,可一旦翻回前面的文本,才發現之前沒有細細注意的詞語,聾子大爹的耳聾、依嬌的行跡、他倆之間的關系,前面無一例外加上了“據說”、“有人說”、“聽說”之類的非確定性語詞作為前提,原先總以為事實即是如此,可正是因為他們深居簡出,便在介紹時已經埋下了一處重重的伏筆。再加上依嬌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撿槍速度,完全有理由看出一些端倪。“曼錦寨是最后一小塊沒有受到這兩種粉塵污染的凈土,依嬌父女是最后一對沒有受到污染的人。”這兩個“最后”一直珍藏在夏曉明的心里,可是恰恰是它們深刻諷刺了現代文明對于少數民族部落的侵蝕。作者有創作談中說“面對堅固的封閉,古樸的習俗,金錢大放異彩。”正因為單純、原始,才更容易被利益腐蝕,或許這是走向現代化的陣痛吧。
夏曉明的走麥城,簡單而又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依嬌面對熟睡的夏曉明沒有下殺手;原因也很輕松:她確實是在見到夏曉明第一眼的時候,動了心。設想如果二人沒有這層復雜的感情交流,這里就不會發生“一個艷麗的愛情故事”。可是這樣一朵讓人欲丟還取的“潔白的罌粟花”,作者最終選擇的還是把它丟掉,因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此完美的花。
當傳奇過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群看客,一群高速生活著、希冀借假期逃離工作的人,作者就給他們提供了幾個上佳的去處。
羅錚同學:
你的讀后感,我還是刊登在《大白》上,你的分析,我不想加以發揮。我只想告訴你的是,白樺先生的邊地傳奇系列還在繼續創作,讓我們一起等待他的新的“傳奇”。
祝好
陳思和
5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