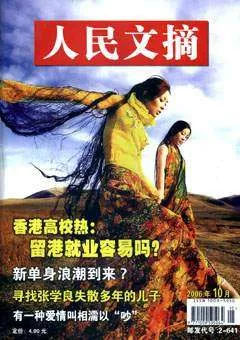一個私立高中部引來家長“陪讀村”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機場路的鴻德國際學校周邊,近幾年來形成一個一百多戶的家長“陪讀村”。生活在這里的孩子大都來自內蒙古自治區各地的旗縣農村,他們被鴻德學校景宏高中部的優秀師資和高升學率所吸引,而陪讀的家長則是為了照顧他們的生活。
在城市孩子“擇校熱”的同時,大批縣城、農村的孩子涌入城市,希望在城市學校占領一張課桌,形成一股“擇城”教育的風潮。
一個“陪讀村”的形成
72歲的蔣秀蘭老人一天的生活是這樣度過的:早上5點半起床,給外孫做早飯;8點買菜,11點做午飯;下午看會兒電視,下午5點做晚飯;晚上有可能在附近轉一轉,然后繼續看電視,或者看著外孫做作業,在外孫12點睡之前她也很難入睡。
蔣秀蘭來自距離呼和浩特市幾十里外的武川縣農村,今年3月,蔣秀蘭的女兒、女婿將他們的孩子送到了呼和浩特市鴻德國際學校讀書,為了照顧孩子,騰不出時間的家長只好請老人出馬,陪著孩子一起來到了呼市。
最遠追溯到三年前,在呼和浩特鴻德國際學校周圍,開始逐漸出現蔣秀蘭老人這樣的“陪讀家庭”,最終形成了100多戶的“陪讀村”。
“陪讀村”中,每個人的生活和蔣秀蘭老人大同小異,沒有娛樂,單調乏味,讓人不時地產生思鄉之痛或忍受夫妻兩地分居之苦,經濟上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孫女士是烏蘭察布市右旗人,兩年前她辭掉工作,專門陪女兒來到呼市,做起了全職“陪讀”媽媽。她算賬說,每月的房租、水、電、其他日常開銷,一月沒有500元是不夠的。加上交學校的4700元的學費,一年至少需要1萬元。這筆錢不是每個家庭都可以輕松拿出的。
陪讀村居民的聚散只取決于一個結果:孩子是否考上了大學。他們來此的目的也很單純:城市學校的教育質量要高于縣城和農村,甚至兩個市之間的教學質量也有很大差別。為此他們付出很大代價,不辭辛苦地從縣城、鄉村來到城市,為的就是追求一個好的學校,給下一代爭取一張更有把握的“大學入場券”。
擇城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事實上,呼和浩特市“陪讀村”現象并不是一個特例。近幾年,在全國許多城市,同樣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陪讀家庭”。為了使他們的孩子接受更優質的教育,許多縣城和農村的家長想盡辦法,克服困難,走上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擇城”教育之路。
每天下午4點10分,康英花準時來到小學門前,接她的兩個孫子回剛剛租來不久的住所。今年春季開學之前,王剴和王苗還在呼和浩特市郊區一所農村小學上學,他們的父親通過熟人,將兩個孩子轉入市區的一所小學,王剴上四年級,王苗上二年級。奶奶康英花便跟了過來,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套房,負責接送孫子上下學,做飯等所有雜事。
康英花說,在市區小學和農村小學上學區別很大,最明顯的是支出驟然上升,房租一月450元,三個人的生活開銷一月最少300元,但所有這些都是值得的,因為市區小學的質量很高:英語課、語音課、電腦課都已開設,校風也好,老師也負責,這些都是農村小學所缺乏的。
城鄉教育“博弈”
“擇城”現象的興起,反映出農民對農村現有教育的一種放棄。對許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來說,農村學校的種種問題,導致了整體教學質量低下,已不足以實現他們的孩子“跳龍門”的夢想與希望。而大批心懷理想的學pIOL02IpP3rgC/k3ospbPVPLWnevVqbgNFa5f3xfl6s=生“跳槽”,反過來又給予了農村學校致命的一擊。
師資流失是農村學校難以抹去的陰影。張家口市尚義一中是尚義縣惟一一所高中,從2003年到2005年,該校三年共流走教師28名,其中僅2004年就走了14名。康保縣一中去年有5名高三任課教師被私立學校聘走,其中一位是康保縣高中年級惟一一位特級教師。2002年成立的涿鹿縣私立學校北晨中學,招聘的10多位初中教師中,幾乎清一色地來自基層公立學校。
教師是學校的靈魂,一所學校的質量好壞,很大程度取決于是否有一批優秀、敬業的教師。大批教師的流失,導致了當地家長對學校信心喪失。
學校師資力量削弱,會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反過來,教學質量的下降,會失去更多的優秀學生。
“一所學校,沒有了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一夜之間就會淪為末流學校。”呼和浩特郊區一所中學的負責人說,現在許多農村中學中,很多是對升學不感興趣或不抱希望的學生,大多數的成績較好的學生,都進了城。農村學校已經陷入了一個泥沼難以自拔:教學質量差—吸引不到好學生—沒有好生源—教學質量更差。
歸根結底,擇城熱的形成是由于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和教育資源不均衡導致的,城鄉教育存在巨大的鴻溝,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可以填平的。吸引生源方面,尤其是優秀生源,城市學校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這場城鄉“博弈”中,輸家毫無懸念屬于農村。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進城讀書,眾多農民選擇這條路時投入了太多的希望,誰也沒有理由指責他們。但是,城市學校畢竟不可能容納太多的學生,絕大多數的農村孩子必須“留守”在農村學校。隨著學生大批出走,教師的毅然離去,農村孩子的大多數將受到傷害,整個教育體系將受到傷害。從這個角度講,擇城熱背后的城鄉“博弈”沒有贏家,只有輸家。
(陳 曉摘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