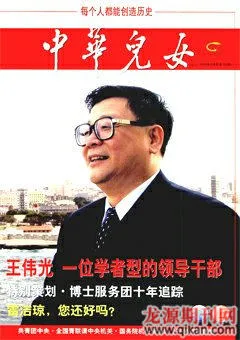歌聲尖銳的人是可靠的
我們這期的封面故事《你的醫(yī)生,不在國內》是關于“境外旅游醫(yī)療”的,我認為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報道。其實,它并不是最近才出現,但是它進入了一個加速期。越來越多的旅行社開始推銷境外體檢業(yè)務,越來越多的中介機構開始鼓動高端人士境外醫(yī)療。
在全球化時代,人們不僅會追逐商品貿易的“比較優(yōu)勢”,也會追逐服務貿易的“比較優(yōu)勢”。醫(yī)療一直被認為是local的,但是,這是一個錯覺。過去人們受制于出國不方便、語言交流不通暢、對別國醫(yī)療情況的不了解??現在呢,這些信息不對稱往往被填充了。中國人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境外游市場,很多中產富裕人群已經有“充分全球化”的能力,英語被更多的國人嫻熟地使用,互聯(lián)網和社交網絡降低了資訊隔閡,于是,“全球化配置你的醫(yī)療”堅定地發(fā)生了,而且不斷“壯大”。
有的人追逐的是價廉物美,有的人追逐的是科技先進,有的人追逐的是產業(yè)成熟。所以,有的人會跑到臺灣做整容,有的人會去美國看疑難絕癥,有的人去日本癌癥篩查。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無法忽略的重要趨勢,而且隱蔽著極其重要的老齡化下的醫(yī)療含義,并將這種含義添加了全球化的維度。
就像我們衡量未來中國的醫(yī)uqHXyeGfYSTUz2EIc5BJSw==療資源壓力的時候,它總是靜態(tài)的、假設所有在內部發(fā)生的,忽視了“國外部門”的存在。就像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消費的看法一樣,他們集體犯錯了,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富人的消費是放在國外的——富人們不會在國內買奢侈品,而是在法國的老佛爺百貨里面血拼。對于他們來說,也許未來他們會忘掉中國的醫(yī)患關系,“全球化”尋找醫(yī)療資源。
與此同時,我們也關注另外一個趨勢性的玩意——現實增強技術(AR)。在幾年前,流行的是Second Life代表的VR,它被認為是未來的方向。林登實驗室搗鼓出來的林登幣最后是一錢不值,無人問津。原因還是很簡單,人們需要的不是自己在虛擬世界里面的投射,而是在現實世界里面的添加。現實增強能夠有助于讓人們更好地掌握現實,而這才是人類的方向。所以,我們認為AR技術是改變世界的動力,谷歌眼鏡索尼頭盔都是重要的催化劑。我們用一篇較長篇幅的報道來慶祝必然發(fā)生的尖叫,顯示我們對它的熱愛。
在秋天,歌聲尖銳的人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