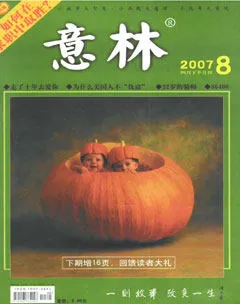哈佛首位女校長
劉 宜
“父母希望她成為貴婦人,她卻成了世界上最杰出大學的校長。”———福斯特的朋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伊麗莎白·沃倫。
得知自己將被正式任命為哈佛大學校長時,身為該校拉德克利夫研究院院長的福斯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她領導的研究院是哈佛最小的一個學院,而且遴選委員會為了尋找到最合適的校長人選已經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
任命宣布后,福斯特因為其女性身份立即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有趣的是,她的前任拉里·薩默斯正是由于公開貶低女性,稱“女性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先天遜于男性”的歧視性言論受到輿論的巨大壓力,被迫在去年2月辭職。
哈佛大學校長的職位大概是高等教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職位,其言論能在整個學術圈中引起震動,而且手中掌握著巨大的資源。要成為哈佛的校長,能力、才華、聲望缺一不可。哈佛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曾坦言“如果能找到這樣一個人———能夠團結眾人達成一致,并把任務完成,我們立刻就會讓他成為校長。”言下之意,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可遇而不可求。
不過福斯特很清楚,在人們的好奇過后,要真正成為一位出色的哈佛校長應該展現給世人的是自己的成就而不僅僅是女性身份。所以她強調:“我不是哈佛的女校長。我是哈佛的校長。”
對于未來,福斯特信心十足地表示:“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我用很多時間思考過去的事情以及它們如何影響著未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讓哈佛的未來比過去更加輝煌,這意味著要堅持我們的優勢,同時認識到不足,不能自滿,直到做得更好。”
在就職發言中,福斯特感慨地說:“我希望我的任命能成為一個機會均等的象征,這對于上一代人還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雖然成長在美國南部一個性別和種族的傳統觀念不容置疑的傳統家庭,但福斯特一直是個反叛的孩子。9歲時一次與家中黑人保姆和司機的交談,曾促使她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寫信,要求廢止種族歧視。之后她又開始質疑美國南部僵化的習俗———為什么女孩就應該穿得很差,白人的孩子就能對黑人成人直呼其名?
福斯特經常與母親辯論,因為母親總是對她念叨:“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孩子,越早明白這個道理,你過得會越好。”
“在我童年的世界里,社會對于性別的安排和認知是被認為理所當然而且亙古不變的。孩子的任務是去學會接受和運用這些安排,而不是去質疑它們。”她曾經在哈佛雜志上發表文章寫道:“待人接物的每一方面幾乎都有范例和模式可循,比如用餐完畢之后怎么放刀叉、讓誰先進門、介紹人的次序、你該和誰握手而不該和誰握手、誰該在餐廳用餐而誰又該在廚房吃飯、怎么稱呼人———黑人只要直呼其名就可以了,對于白人,則要加上‘先生或‘太太的稱謂。”
福斯特確實曾按照父母的意愿做了一些事,比如養奶牛、參加舞蹈課等,但她最終還是成了一個“叛逆的女兒”,參加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爭取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游行。此后,她又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著書疾呼,或許正是這種與生俱來的對平等、權利的追求,促使她成為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并最終戴上哈佛大學校長的桂冠。
當被問及對她的任命是否意味著哈佛性別間不平等待遇的結束,福斯特答道:“當然不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在理工科方面。”
(岳建軍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