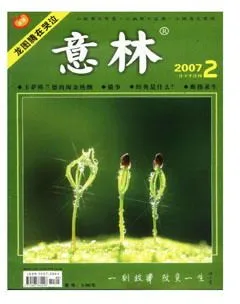為戰亡的士兵父母畫像
陳丹青
1979年,中越開戰。3月底,我與班上兩位同學隨鐵道兵文工團南下廣西勞軍,演員表演,我們給軍人畫像。其時戰事已近尾聲,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軍車給南國的春雨紅土濺得滿車泥漿,不見絲毫戰爭的慘狀。那天吃過午飯,我們所在的營盤有小兵領進一對自稱從長沙趕來的中年夫婦,領到連長面前,那母親,也就是天下所有母親的樣子吧,父親的模樣是在地方干部與廠礦職工之間。兩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現在兵營,十分注目,他們環顧眾人,羞慚惶惑,然而涎臉笑著,輪番解釋來意,說是孩子一個多月沒給家寫信了,不放心,特地趕來問問看。
我想在場的人誰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嘗不明白,只是人對死的消息總不肯當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漸漸圍攏,顯然他們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戰友;勤務兵端茶遞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對夫婦。連長到底歲數大些,又是領導,他給那父親遞過煙,點上,挺自然地強笑著,用一種混雜部隊官腔和地方家常話的語調寒暄著。
其時我正給戰士畫像。待我歇手,周圍一片靜默。那父親看著地面,沉吟著,抖著腿,很有姿勢地舉著煙,相當鎮定。不知他真是位于部呢,還是職工,中國的職工的舉止,常在模仿干部,很像干部的。
終于,我第一次當場聽到——而不是在電影里看到——有位真的軍人真的說出我們從小聽熟的詞句。和電影里不同的是,連長并沒有緊握對方的手,做出無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繃著臉,低眉瞥視手上的煙,緩緩地,撣一下煙灰,說一段句子:
事情是這樣子,你們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經光榮犧牲了。
原句似乎還長一點,夾著“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這場自衛反擊戰中”等等修飾詞。接著是交代陣亡的時間、地點、戰役,解釋為什么沒有及時通知的原,因。但我盯著那對夫婦,沒在意聽。
母親埋下頭去,哽噎嗚咽:沒有大哭,更沒放聲嚎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飲泣”的那種哭法,一個女人隨便為了什么事都會哭得比她那會兒更劇烈,更傷痛。
我清楚記得的是那位父親的側面;他停止抖腿,專心傾聽。聽到“犧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沒有出現異狀,繼續專注傾聽,既像是一名下屬聽取上級報告,又像百姓面對首長時的那么一種恭敬而凜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陣亡,他不會有機會坐在這里被接見,由一位部隊首長親口對他說出“光榮”與“犧牲”這幾個字:這聆聽親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榮啊。
他就這么聽著,神情鄭重、通達,像一位干部在個別接見中傾聽內部機要傳達時那樣,在每一逗號句號處穩重地點頭,目不轉睛看著連長。可我發現他其實沒在聽。一個人不是常會極專注地傾聽,凝視對方,又完全不在聽么。在聽到兒子的姓名和“光榮犧牲”之后,大約半分鐘,他照,樣將煙卷湊到嘴上吸,甚至安詳地吐出煙來。僅有一剎那,猛地,他的顏面頸脖漲得通紅,頃刻泛紫,淚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陽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臉盤即刻就會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傾聽的身安居然完好保持著,只是腿又開始抖動,速度加快。
就像小說上寫的那樣,我的心“緊縮起來”:悲慟要發作了!我想——只見他使勁眨眼,同時,如內地的男人們在重要場合關鍵時刻將要表態的一瞬,用力咳嗆,像是真的在清喉嚨,喉結猛烈地吞咽,總之,他迅速恢復了革命鎮定,紫漲、淚光、要爆炸的血管,漸次消退,腿的抖動轉成徐緩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支煙,又被換了一杯添上熱水的茶。
我就開始畫速寫。
孩子十八歲,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為家里做了一百多個煤餅。這是后來別的士兵告訴我們的,他們在連長宣布死亡后團團圍攏那對夫婦,有位清秀的小兵說他也是長沙人,他竟伸手撫摸母親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話反反復復念著我們從小在電影里聽熟的話,鄭重而誠懇,但也沒有電影角色那套標準的悲痛相,倒很像喃喃地朗誦臺詞,不善做戲的群眾演員:別難過,媽媽,你就把我當成你的親兒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經排練的合唱與重唱,有點錯落,有點整齊,別的士兵用各種嗓音和方言依次應聲:我們都是你的兒子!我們都是你的兒子!
入夜,操場上播放老電影《劉三姐》。軍人整隊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時的當地村民赤著腳蜂擁進場,在混亂中,我一眼看見那對夫婦,他倆被另一群更高層、更穩重,而且個個粗壯發胖的老首長前后簇擁著,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親,顯然剛吃過晚飯,顯然頭一次被這么多高級首長奉為主賓,他笑得那么懇切,興奮,激昂,搶著掏自己的煙,和左右兩位首長用手臂來回推擋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親夾在當中,不搭話,呆著,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渙散。電影開映了,劉三姐,眉目飛揚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場軍民浪濤般一波波跟著唱,叫喊,鼓掌,嘩笑。我幾次扭頭望過去,那母親的眼睛仍然無焦距地向前直視,根本不在看電影。散場后,我們分頭上車。強烈的車燈光照亮路邊已經發動引擎的首長的吉普,我又看見那對夫婦,丈夫在車門口同諸位首長握手又握手,奮力點頭,后腦勺上下晃蕩,妻子先已坐進前車座位,依然直視著,在電影放映前后近兩個小時里我幾次斜看:她始終維持著她的無焦距的直視。
(趙雪蓮摘自《文學故事報》
圖/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