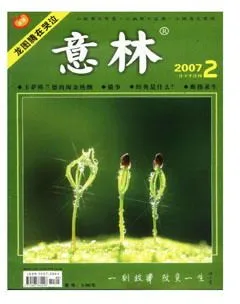第一次受打擊
2007-05-14 08:17:44季羨林
意林 2007年2期
季羨林
1936年,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師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第四個學期念完,我開始慢慢寫論文。我想,應當在之前寫上一篇有分量的長的緒論。我覺得,只有這樣,論文才顯得有氣派。我一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做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做卡片同時并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于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費了一番心血,自我感覺良好。我把緒論送給了教授。
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沒有說話。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兒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劃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個字后面劃上了一個后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這真是“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掉了。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根本沒有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復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
(風鈴摘自《另一種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