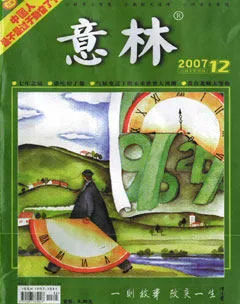我割斷了兒子與相聲的緣分
馬 季
回顧我從事相聲的經歷,酸甜苦辣都有,但是苦的、酸的占一多半,其中的磨難、磨礪啊,真夠我受的。因此,我的兒子馬東,我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轍,走我這條路。我說過一句話:我太喜歡相聲了,但是我太討厭這支隊伍了。這是我的心里話,我說出來了,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還是要說。我可以克服相聲界的一些壞習氣,但我擔心我的兒子隨波逐流。
馬東從小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十分喜愛相聲、快板書等曲藝節目,四歲半時他就能背出整段的快板書《奇襲白虎團》(近20分鐘的節目),當時把我嚇了一跳,我問他是跟誰學的,他說是收音機。他對相聲也有一定的理解和看法。我曾經創作了一個段子《地名學》。這段子也膾炙人口,是我在西單劇場從青年曲藝隊那兒聽來的一個墊話:“您這腦袋上盡是地名,您整個一個地圖哇,您讓大伙看看,您前面這個‘門頭溝。”“我這個‘門頭溝哇?”就是這么兩三句,我聽了以后受到啟發,覺得很有意思,就決定寫一個這樣的段子,叫《地名學》。我興致勃勃。很快就把結構寫出來了,寫完之后,我叫馬東,說你聽聽這段子。他當時十幾歲了,我夫人也在旁邊,我就開始念,念完了。我夫人搖頭:我兒子呢,我拿他當孩子,不懂事,結果他說:“思想性不強。”他走了之后。我思索這個東西,“思想性不強”是什么呢?好像這段子沒有內容,只是利用“字音”上的巧合,產生了一些笑話。因此,我堅持下去。再改得巧一點,使它趣味性更強一點。改完之后。我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全國青年聯合會,在中直禮堂。中間休息的時候,有人喊:“讓馬季上來給大家表演表演!”一個人表演什么呢?正好構思完這段,我上臺一說,觀眾非常喜歡!馬東的一句話使我對相聲的認識變得更成熟了。
寫《舞臺風雷》的時候,五天沒出門,馬東放假在家,看著我整天就在那兒寫。我寫的時候,我一遍一遍老要說,怎么上口怎么寫,代表甲和乙兩個人,就跟對詞一樣。馬東特喜歡這個,我哄他進屋去玩兒,他坐在那兒偷著聽。我寫完了,差不多他就能背下來了,小孩腦子快。寫完之后,我把趙炎找來了:“今天下午4點出發,清華大學演出。”“馬老師,我行嗎?”我說:“行,你一定行!”我們就排練,排練的時候趙炎忘詞,這時候馬東憋不住了,從里頭出來,一探頭,幫他把臺詞接上,完了對趙炎說:“連我都記住了。”
馬東很喜歡相聲,經常偷偷地翻看我創作的本子。他那時正上學,我催促他早點睡覺,明天早上好上課呀。但聽到他在房間里“哈哈哈”地笑,我說你笑什么呢?原來他在看《四大本》,相聲小段。看到精彩處便忍不住大笑。笑完了,他也都掌握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跟老師們一再聲明。您可千萬別引導他,一引導他就過去了,他就把精力從學習上轉移了,現在讓他好好學習,至于說不說相聲,等他長大了再說。
之后,他留學國外。學成回國后投身電視行業,最初主持的節目是“有話好說”。看了這個節目,我感到他做了很多努力,有很大的進步,我很為他驕傲。我曾經想讓他幫我總結我的藝術經驗,寫回憶錄。因為他最了解我,我跟他深談過這些,他的一些想法,使我也很受感動。我覺得孩子成熟了,他很多看法,對我來講是一種教育。比如說,我跟朋友、師徒之間的關系,他是局外人看得很清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東西。我覺得他的分析有一種時代感。有時候,我鉆到一些問題當中去,他給我講,我覺得挺好。但是我提出來讓他給我寫回憶錄時,他說:“我完不成。我和您是父子關系,中間必有一種親情,使我們看問題具有局限性。”我認為他說得對。
我十分慶幸我割斷了他和相聲的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