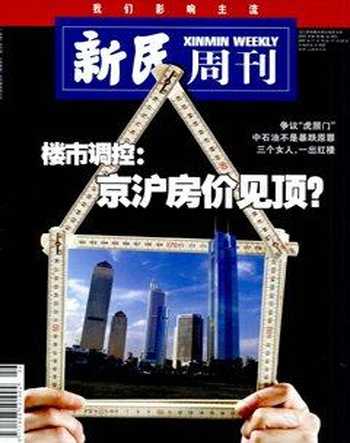2003-2007:調控與房價的博弈
汪 偉

調控與房價的博弈似乎已經周期化,并且,每個回合的勝者總是不斷躥升的房價?
調控與房價周期化博弈
中央政府對房市的調控始于央行2003年6月的“121號文件”,此后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3年到2004年,以央行的“121號文件”和國土資源部?監察部的“71號令”為標志,第二階段是開始于2005年的“國八條”;到了2006年,溫家寶主持國務會議,提出“國六條”,房地產調控進入了第三階段?
三個階段都重復著相同的故事?調控前房價飛升,新政策出臺,房價上漲的勢頭為之一挫,在隨后的相持階段,交易量萎縮,房價略有回調或保持不動,等到市場力量將調控政策的效應消化殆盡,新一輪的房價上漲又重新開演……調控與房價的博弈似乎已經周期化,并且,每個回合的勝者總是不斷躥升的房價?
除了專業人士,人們似乎已經很難想起2003年的“121文件”這一調控“開場白”了?“121文件”全名為《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申請銀行貸款,其自有資金應不低于開發項目總投資的30%;土地儲備貸款額度不得超過所收購土地評估價值的70%,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2年,且不得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用于繳交土地出讓金的貸款?
“121號文件”是2003年大范圍的宏觀調控的一部分?調控的目標并非特別指向房地產業,包括重工業和資源性產業在內的多個國民經濟基礎行業,都被央行收緊了信貸口子?中央政府認為這些行業投資增長過快?規模過大,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寬松的信貸政策被認為是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成了調控的主要環節?
隨著SARS疫情漸漸平復,2003年年底,各大城市的房價幾乎都擺脫了疫情陰影而重新起飛?盡管只過去了區區4年時間,現今已經很難想象“121文件”剛出臺時造成的震動?這份文件表明由城市房改肇始的房地產市場進入了賣方市場,由此導致財富飛速向這一行業集中,其速度遠超出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心理預期,也超過了社會財富增長的平均水平?
調控政策一開始就緊盯著金融與土地兩個政策杠桿?房產開發基于土地,同時需要大量資金,收緊土地與信貸口,可以減少供應,防止過熱——這原本是針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行為的一般思路?
繼“121文件”之后,2003年8月,國土資源部等5部委對31個省市自治區的用地情況展開了調查?2004年3月,國土資源部?監察部下發了被稱作“71號令”的《關于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提出當年8月31日為辦理協議出讓土地的最后期限?城市建設用地的供應全面市場化,土地供應的口子開始收緊,同時提高了房地產開發的資金門檻?
但這種調控思路很快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第一個考驗來自于銀行和地方政府?央行難以遏制各大商業銀行向房地產業放貸的熱情,而國務院也不能真正節制地方政府賣地的沖動?
到2005年,房價急速和持續的上升勢頭,已經變成了普通市民經濟生活中最受矚目的事件?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針對房地產業的調控變得越發頻繁,也更有針對性?
到第二階段(2005年)和第三階段(2006年),調控開始敲打對執行宏調不力的各大銀行和地方政府?2005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是為“國八條”?2006年5月17日,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六點意見》,也即“國六條”;“國八條”和“國六條”都有嚴厲措辭,要求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中央的調控政策,為房產市場降溫?“國六條”明確提出要調整住宅供應結構,90平方米以下的小戶型將占到市場供應總量的70%;這次疾風驟雨式的調控還第一次明確了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對房價負有行政責任?
至此,房地產業內的宏觀調控,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政策體系?一方面,通過土地?信貸?稅收等種種手段,限制房地產商的投資熱情;一方面,通過開征土地增值稅和提高營業稅,加重交易成本,減少交易次數;此外,還從政治上要求地方政府對房價負責,政府開始整治開發商囤地囤房現象,以維持市場秩序?
流動性過剩催生樓市泡沫
進入2006年,隨著“流動性過剩”一詞的不脛而走,樓市的火熱似乎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錢多房少,價格上漲:各方忽然驚奇地發現,所有關于樓市的判斷,都在向這個經濟學常識靠攏,因為在流動性過剩的市場環境下,資金不再是開發商的瓶頸,即使國內銀行收縮貸款,開發商也很容易得到外資的支持?
而針對交易環節進行的調控,尤其是提高交易稅,在賣方市場里,最終要由購房者承擔?高額交易稅對減少交易次數縱然有效,卻也加重了“自住型”和“改善型”購房者的負擔,因此受到抱怨?
調控的思路正是在這種批評和反思中開始發生變化?漸漸地,收緊土地和信貸不再是調控的重頭戲?而吸收流動性?首先是限制外資炒房,被認為是調控樓市的治本之策?

2006年7月11日,建設部聯合其他五部委下發被稱為“外資限炒令”的171號文件,加強對外資投資企業房地產經營或購房的管理?2007年3月?6月?7月,商務部和外匯管理局又接連三次發文(25號文?50號文和130號文),限制外資投資房地產?同時,不斷地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和發行巨額央行票據,都顯示了中央政府吸收流動性的決心?
新政需要時間表
盡管調控艱難重重,對政府而言,坐視房價上升卻意味著風險積聚?總結4年來的調控經驗,發展新的調控思路,成了當務之急?
2007年,中央開始強調政府在住房問題中的責任,要求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市場份額?此后不久,中共十七大上又提出,要增加國民的財產性收入,所謂“財產性收入”,居民在房地產市場上的投資所得也在其中?
觀察人士認為,這可能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房地產思路已經發生變化?這個新的思路中,政府保障性住房將成為大多數居民住所的來源,房地產業的份額將變小,轉而經營高端房產?而關于“財產性收入”的闡述則被分析為中央對投資性購房的態度已經轉變?
這種判斷是否準確,還有待繼續觀察?但在房地產調控問題上,基于4年來的經驗教訓,政府和業界應該已經形成了幾個共識?
首先,中國城市化的歷史進程方興未艾,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城市房地產業在未來仍有擴張空間,社會資本也仍將繼續向這個行業聚集?未來一段時期內,房地產商人仍將繼續以密集態勢在富豪榜上出現?
但房地產業的歷史空間不等于現實中的土地空間?大中城市中心區域的土地開發將陸續宣告結束,開發重點將從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從市中心轉向郊區?“小產權房”將是未來房地產業發展中不可忽視的變量?在這種農村土地所有者自發城市化的倒逼之下,極有可能蘊藏著未來的土地制度變革?
同時,房地產業的歷史合理性不能證明現實中的房價合理?盡管房價是否有泡沫還有爭議,但爭議正在變小?從王石這樣商人到諸多經濟學人士,都開始警惕房價持續高企可能造成的危機?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危機的抓手很可能在產業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這取決于宏觀經濟能否創造更多的投資渠道,將負利率下紛紛出逃的銀行存款吸掉,同時配合以央行的金融政策(加息和提高準備金率),進一步縮減流動性,當然,這還取決于人民幣的匯率問題的發展,能否將熱錢阻擋于國門之外?
加息和提高準備金率空間有限?面向出口的制造業盡管是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但事關中國數以千萬計缺乏技能的人口的就業,某種程度上,這一產業結構將會繼續維持下去?股市對資金的吸收此時顯得至關重要?不幸的是,包括巴菲特在內的投資者面對價值不斷重估的中國股票,已經產生了高處不勝寒的緊張——誰指望能以股市的泡沫來消弭樓市的泡沫呢?
許多評論人士都在期待政府保障性住房計劃能夠盡快進入實際運作階段?這被看作解決中國房地產困境最現實的出路?但迄今為止,地方政府并沒有真正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