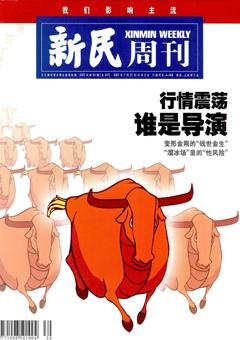工薪上漲:白兔還是烏龜?
李澤旭

人們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結果的不平等而是機會的不平等,這被稱為隧道效應。
日前,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論壇出現一條消息: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扣除物價因素平均年增長12%,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
消息一出,網上網下一片嘩然。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為此通過題客網就此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這項有1604人參與的調查顯示,85.4%的人自稱工資漲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稱4年來工資"不漲反跌"。
從歷史說起
隨著1985年和1993年兩次較大范圍的工資及相關制度改革,幾十年不變的工資體制僵局終被打破,并成為這之后工薪普遍、快速上漲的基石。
1985年,我國將國有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脫鉤,使國有企業的工資分配逐步與市場機制相銜接。同時,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使得企業能夠按照利潤留成政策保留一部分利潤,并可以用于集體福利和職工獎勵。1993年的工資制度改革重新設定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實行政事分開。同時,隨著非公經濟和外資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工資形成與調控機制也逐步完善,基本形成了市場機制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的工資分配制度。與之相適應的是,1993-1994年啟動實施的財稅改革,決定將國有企業所得應該上繳國家的部分采取稅的形式,并按照統一的稅率征收,剩余的部分全部歸企業支配使用。
"我國工資體制改革最大的一次是1993年的工資套改。工資套改后,工資多與少在很大程度上轉向與學歷、受教育程度等掛鉤。這個變化是比較大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權衡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市場化改革后,原來的工資決定機制或者說形成機制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企業工資,基本上是以市場化來完成的。工資規模和公司效益掛鉤,企業效益越高工資越高。與此同時,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也開始同步上漲。
是否數字游戲
4年間,職工工資平均上漲12%。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數字游戲。
對此,2007年7月17日下午3時,勞動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在中國政府網就"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問題"與網民進行在線交流時解釋說,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們國家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分別超過了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十五"時期是工資增長最快的時期。這種增長不管是在哪一類企業,在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都有增長。
造成部分人們對工資增長的感覺與統計結果存在差距的原因,邱小平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是一個統計的概念。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并不意味著廣大職工的工資都能夠按照同樣的水平增長。現在在職工工資總體增長的情況下,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不同企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資快速增長會直接拉高對全部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增長的統計數字,從而有可能掩蓋低收入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甚至有的職工工資水平相對下降的實際情況。
第二,隨著近年來我們國家住房、醫療、教育等消費價格的上漲,增加了職工家庭的消費支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資增長的效果,有可能造成低收入職工對工資增長的感覺不太明顯,也許工資漲了,但是相應消費支出也增長了。
第三,我們國家現行的工資統計范圍只是城鎮國有、集體單位以及其他規模以上的企業,沒有包括工資水平一般偏低、增長較慢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現在主要的問題還不是工資體制本身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怎樣看工資增長和可支配收入增長包括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權衡認為,理論上講經濟快速增長,收入也應高速增長。但是從偏離度角度來看,我國近幾年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并不是朝同一個方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偏離。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6年的1175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價因素以后,民眾的收入平均年增長6.7%。但是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高速增長相比,這個速度無疑顯得有些緩慢。
權衡認為,目前我國勞動工資總額和GDP總量比較,這個比例與國外主要國家相比,我們是非常低的。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多,按照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分配,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勞動所得就應該多,相應占GDP比重就應當高。但是我們并沒有體現出來。這從根本上反映出了宏觀分配方面的問題。整個國家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當中,占大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未占優勢。政府拿了多少,企業留了多少,個人拿了多少?企業的變化很小,政府這些年拿得越來越多,普通老百姓相對增加量較小。在國際比較中,工業化到了中后期階段,往往是國家拿的份額越來越少,例如在10元當中,可能國家只拿1元,個人拿六七元,剩下的企業拿。而我國政府拿的份額很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1993年稅制改革。當時,一個是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例偏低,一個是財政收入在GDP當中的比例偏低。為解決這兩個偏低,我們實行了分稅制,這是分稅制實行的出發點之一;但是問題在于財權集中的同時,事權并沒有劃分清楚。
不患寡而患不均
邱小平稱,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資快速增長會直接拉高對全部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增長的統計數字。
那么這一部分,到底是哪部分?
權衡將其解釋為四個字---壟斷行業。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05年,"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工資漲幅為15%,航空運輸業為24.1%,金融業為19.4%,與此相對應,當年農業漲幅為9.3%,建筑安裝業為7.7%。行業間的工資漲幅差距明顯。
"這種壟斷的背后是行政性壟斷,電信、電力、銀行、鐵路包括行政部門的工資收入主要不是市場機制的配置,還是行政權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權衡認為。
權衡分析,人們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結果的不平等而是機會的不平等,這被稱為隧道效應。我們知道上海穿過黃浦江的延安路隧道時常擁堵,如果向同一個方向的兩個車道都堵住了,這時大家都沒意見。一旦左邊車道上的車開始動了,這時相對差距拉開了。但是,距離拉開了并不是壞事情,至少右邊車道上開車的人看到,左邊的車動了,我差不多也該動了,這時是積極的效應。但如果左邊的車一直在動,右邊一直不動,時間一長,就由原來的有希望變成沒希望,右邊的車就有可能去往左邊車道插隊,爭取獲得一個通過的機會。中國的收入差距引發的問題原因應該主要在這個方面,我們要克服的就是在機會層面上的許多不平等的現象。